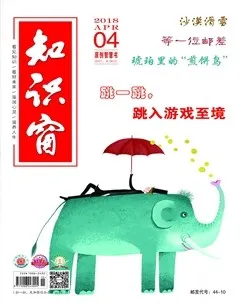語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思宇
梅破知春近,此時節(jié),遼遼曙光中,正值朵朵寒梅,悄然開遍向南的枝頭時。
一樁老梅,一端蠟蓓,一段段開在雪里、散在風(fēng)里的往事故舊。歲歲冰中,有枝一夜清香發(fā)散;年年雪里,有人長插梅花為醉。
唐人崔道融,穿過千年的時光向我們說出所見:數(shù)端臘萼,初初含風(fēng)帶雪,香中有韻,清極不寒,是孤標而難以復(fù)刻的畫本。自是極美,然而他又說橫笛和愁聽,說斜枝倚病看,說朔風(fēng)如解意,說容易莫摧殘,一句一句,讀得悲而復(fù)去,傷而復(fù)來。
宋人黃庭堅,在宜州見梅時,和雪吟誦“玉臺弄粉花應(yīng)妒,飄到眉心住。平生個里愿杯深”。詩里的故事,群芳妒恨也好,平生里愿也罷,一束清梅下,縱然天涯也有江南魚信,一首《虞美人》,堪堪老盡了這位去國十年夫子的少年心。梅景再美,也讀得人心涼。
這樣的故事很多。梅花一弄處,斷人腸;梅花二弄處,費思量;梅花三弄處,風(fēng)波起,云煙深處,水茫茫。這樣的梅花像是在寒冬的冷水里浸過一般,悄愴幽邃,凄寒傷骨。讀著這樣的詩詞,有時候我會想,它們不該只是晨光里高懸著的蠟蓓,不該只是暮色中掛遍了金鐘,應(yīng)該是有梅漫侵月影,是有朵展上窗紗。梅花,本該就是天賜的胭脂、一抹的腮,何必故作姿態(tài),強加許多,這種想法也慢慢地固執(zhí)起來。
“君自故鄉(xiāng)來,應(yīng)知故鄉(xiāng)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語出唐人王維的《雜詩》,我很是喜歡這首詩,詩句很質(zhì)樸,質(zhì)樸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但質(zhì)樸往往是最容易打動人的。
“君自故鄉(xiāng)來,應(yīng)知故鄉(xiāng)事”。關(guān)于每個人的“故鄉(xiāng)事”,無論古今,都是可以開一張長長的清單的。初唐的王績寫過一篇《在京思故園見鄉(xiāng)人問》,從朋舊童孩、宗族弟侄、舊園新樹、茅齋寬窄、柳行疏密一直問到院果林花,結(jié)尾處仍是“羈心只欲問”的意猶未盡。故鄉(xiāng)之于每個人,每個人之于故鄉(xiāng)的懷念,是親朋故舊,是山川景物,是風(fēng)土人情,它們往往平常,往往細小,卻蘊含著當年故土生活時親切有趣的情事,這些點點滴滴連著每個人的記憶,拼出故鄉(xiāng)的模樣。詩人獨問寒梅,平淡質(zhì)樸得如敘家常,一株寒梅,勾連起那些寒冷歲月里的溫馨瑣碎。
這樣的梅平淡得多,熟悉得多,也親切得多。
梅花,高潔而風(fēng)骨,很多人從小就知道,梅花是一種冬天開花、特別耐寒的植物。我的故鄉(xiāng)是冬天足夠寒冷的山東,但小時候我從未見過梅花,這并不妨礙我對《雜詩》里梅花由心而生的親近與喜愛。我總會問大人:“為什么咱家這里的冬天,我看不到梅花呢?為什么梅花和水仙同樣耐寒,卻很少會像梅花一樣頌贊水仙吶?”大人們總是在笑,卻不回答。后來,我第一次看到真真正正的梅花是在南京的梅花節(jié)。在大片大片的梅花中,我想明白了小時候的問題,梅花能耐江南的寒,水仙能耐嶺南的寒。所以,應(yīng)該還是梅花更耐寒一點。
我的童年里是沒有梅花的,但我的血脈中有梅花的基因。在南京的梅花節(jié)上,記憶中大片的梅花種種,與眼前的梅花模樣,撞了個滿懷。
隨著年齡漸長,眼界和閱歷逐漸開闊,我和所有的同齡人一起同世界固執(zhí)、同世界和解。當我們真正經(jīng)歷過一顆悲傷的心,能夠和歡樂的心同唱,會慢慢體會這樣一份至高無上的高貴,會慢慢壘砌成內(nèi)心的高壁。然后,我漸漸地讀懂,陸游詩中“一樹梅花一放翁”所蘊含和沉淀千年的中國式智慧與風(fēng)骨;漸漸相信,少年時幼稚的懷疑、反叛,同樣會在時間里被打磨、解釋。所有的一切,都匯成一種力量,引領(lǐng)自己,更或者能被時光留駐,去引領(lǐng)他人。
同一株老梅樹上承接的少年心事一樣,人生路上,或許就是固執(zhí)與和解的相互博弈與扶持,這種說法也許很矛盾,但即使寒冬臘月中,也會奇妙般地開出一簇簇香中有韻的梅。它們是如此博大而遼闊,如此凌厲而和解。
對于梅,前人已然說出了太多我們想到或者從未想到的話,它們風(fēng)情萬種,默默地向人世間寄出方寸情衷。疏影橫斜、暗香浮動的梅,神清骨秀、幽獨超逸的梅,每個時代,每個人兒,許是都有著自己對它的氣質(zhì)風(fēng)姿的見解,也該是有著自己對它氣質(zhì)風(fēng)姿的見解。兩者之中,前者也好,后者也罷,都是一樣的。
梅花,本就是天賜的胭脂、一抹的腮。
梅破時,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模樣。梅花和著冰雪謝盡。一點微酸已經(jīng)著枝時,古人寫過這樣幾句詩詞——“立春枝頭東風(fēng)化,生從此出生,笑去無牽掛,攜得燕子語,解得無憂花”。許是綺窗前的梅花,早將芳條指向東,也許這春風(fēng)就是從梅樹枝頭上化出來的,從今兒以后,所過之處都姹紫嫣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