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從前,也有個人等你下課,愛你很久
2018-05-03 16:29:44胡識
意林
2018年7期
胡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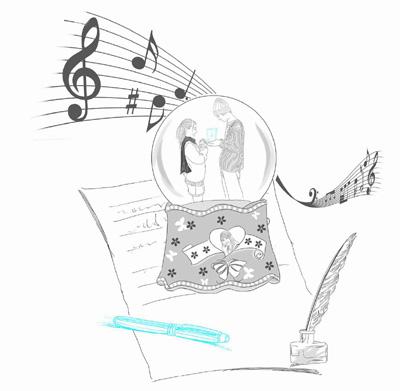
我一直珍藏著一封情書,印花信紙,淺藍色的筆跡。有時候坐在藍天白云下把情書攤在石凳上,在春光的撫摸下端詳,情書折射出一道道七彩光芒,宛如一個晶瑩的夢,在夢里住著一個粉紅色的故事。
那年我考上了縣里的一所私立高中,遇到很多陌生面孔。
那時候我特別喜歡寫詩,常常趴在課桌上把想到的詩句寫在便箋簿上。雖然現在讀起來有些言不及義,空洞無力,但那時候卻博得很多同學的喜歡,他們都不叫我的名字,都以“大詩人”稱呼我。
我幾乎每天都要寫一首詩,等到下課后便用透明膠貼在教室的黑板報上,大家見狀就會圍在一起看我的詩。倘若歌頌的是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們就會叫阿狗蹲在桌子上朗誦。
阿狗自詡有一副像狗一樣的金嗓子,故藝名喚作阿狗。他撕下黑板報上的詩歌,“嗖”一聲躍上桌子,收腹提臀,半跪著,頭微微昂起,他的一對大眼珠子在眼眶里快速地轉動,他在掃視便箋簿上的詩句。他清了清嗓子,開始朗誦起來。
我寫詩歌不喜歡用“啊”或是“吧”字去表達自己的情感。但阿狗每念完一句總要聲嘶力竭地“啊”上一聲,他總以為拖長音能夠顯得忘我,聲情并茂。可每每這時同學們都會笑得前仰后合,我自然也被他氣得七竅生煙,為此,我好幾次都和阿狗廝打起來。
班主任拿我們實在沒法,就罰我沒日沒夜抄課文,罰阿狗背書。我氣不過,在便箋簿上又多寫了一首罵狗的詩。
我把詩歌傳給女同桌陶子妹,想她一定會捧腹大笑并指著我的大鼻子說:“阿識詩人,你作詩罵狗的本事真可謂出神入化啊!……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