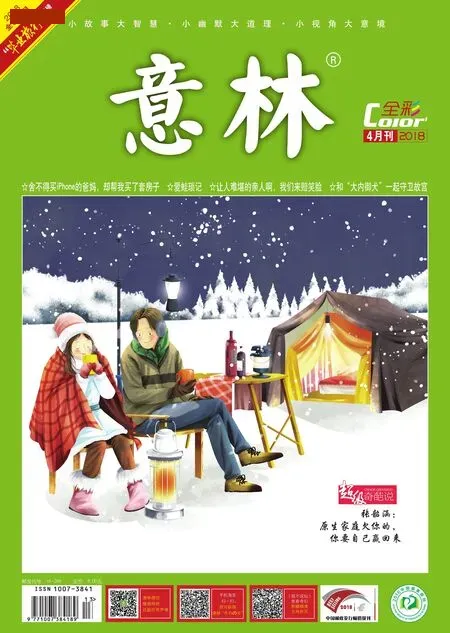讓人難堪的親人啊,我們來賠笑臉
□ 南在南方

看程紹國寫的《林斤瀾說》,有一章寫林先生和汪曾祺先生的莫逆之交。
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作者提起游鷗海時,一個年輕姑娘挽著汪曾祺,走在后面的汪的妻子施松卿對作者說:“老汪這個人啊,就是喜歡女孩子。你看你看……不過,我不嫉妒,真的沒有嫉妒,哈哈哈……”2000年,在北京林斤瀾家附近的建國門客棧,我說起這件事,林斤瀾感慨地說:“老施腦血栓,癱倒在床上,還疑心曾祺和保姆有關系。有一天,保姆問她晚飯吃什么,老施竟說:‘吃逼!’(原文如此,抱歉)曾祺對我說的時候直搖頭,說:‘你換一個詞也可以嘛,比如說:吃屁。’”
忽然眼熱,不說施松卿當年是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的美人,也不說汪曾祺喜歡女孩子,而是病中汪夫人說的那兩個字,這兩個字無疑令人難堪,可若說這話的是我們的親人呢?
比如我在《我媽》里寫道:我媽笑起來像灰兔子,灰白的頭發(fā),露出僅剩的兩顆門牙!不過兔子不流口水,我媽有時要流口水,可誰也攔不住她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笑完之后要說一句:“要是有啥藥,把我的笑給治了就好了。”我說:“你只管笑,比哭好!”我媽自從中風之后,就愛笑。我說:“媽,你笑啥咧?”我媽說:“想著有一回下雪咱屋一只雞摔了一跤,爬起來,一拐一拐地跑了……”話音未落,又笑起來。
很多時候,我媽管不住自己的笑,家里有客正說話,我媽忽然笑了,常常讓人莫名其妙,自然,我們得解釋一番,這樣客人才釋然。因為,我媽坐在那兒,看上去好好的,正常人一樣嘛。
生活里頭,親人讓人難堪的事總是免不了。
有一年夏天,我坐公交車,一個中年男人和一個小伙子坐一起,小伙子明顯不對勁,腦袋擰著瞅后座一個女子,這個男人就扳他的身子,扳他的腦袋,他明顯地掙扎,還要擰過腦袋,呆呆地瞅著那個姑娘。中年男子跟女子輕輕說:“對不住啊……”小伙子第三次轉身,伸手指著女子的胸說:“爸爸,好大奶!”
那女子忽地站起來,指著小伙子,惱怒的嘴唇顫抖著……
中年男人再一次道歉,臉上絳紅著,好像有點輕微的抖動:“對不起,娃有病啊。”那女子余怒未消說:“有病,你領著他出來瞎轉?”中年男人誠懇地說:“不是瞎轉,去看病……”
周遭的人就勸姑娘息怒,那男人將小伙子的腦袋摟在懷里,這時,小伙子不掙扎了,只是安靜地靠在他爸懷里。
他沒有責怪兒子一句,或許責怪并沒有意義。
我們無法知道自己將會有怎樣的父母,就來到世上了。父母也不知道將會有怎樣的兒女,就養(yǎng)育了我們,就算是一塊石頭,他們也要焐熱我們,有時候,我們讓他們難堪。
父母曾經(jīng)是龐然大物,只是后來,總有令人難堪的時候。我們能做的,只是由著他們讓人難堪,我們來賠笑臉。因為這樣的時日,也許不會太多。
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里說:你和死亡好像隔著什么在看,沒有什么感受,你的父母擋在你們中間,等到你的父母過世了,你才會直面這些東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你不知道。親戚,朋友,鄰居,隔代,他們?nèi)ナ缹δ愕膲毫Σ皇悄敲粗苯樱改甘歉粼谀愫退劳鲋g的一道簾子,把你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