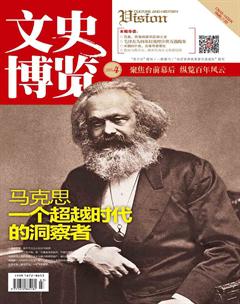曾國藩“以貌取人”有一套
譚凱仕
1856年,湖南攸縣鳳嶺鄉(xiāng)鳳塔村的譚丙榆在新寧縣擔任教諭時,年已五十,然才貌仍佳,時人評其氣質(zhì)長相曰:“氣吐長虹,振珊珊之鶴骨;貌留古雪,美郁郁之虬髯。”說他風度翩翩,是個美男子。 當時的名臣曾國藩對譚丙榆也有一個斷語:“目不妄動,鼻子挺,堅實可靠。”并與譚丙榆的朋友譚鐘麟說,此人忠厚勤勉又有才,但他的手掌肉體薄,一生坎坷多磨,很難大富大貴,且日后將死于任上。
曾國藩有著“古今完人”之譽,他的識貌評人可不是隨意說說。他識人的口訣可概述為:“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他將初識之人分為三種:聞可、見可、聞否。前兩種是能用或可用;“聞否”則是“庸而無用”“貪而無恥”或愛“離間內(nèi)斗”者之類,不能用。曾國藩認為:人貴忠誠而有才。所以譚丙榆的面相雖不算太好,但屬“見可”,因此進入了他的網(wǎng)羅之圈。
譚丙榆出身于教育世家,從小詩書熏陶。他的宗師、當時的理學大儒邵丹畦、龔春溪等,認為他“具龍文之偉質(zhì)”,日后必定是“湘中琳瑯,楚南杞梓”。青少年時,譚丙榆在各學堂的聯(lián)考中屢奪高標,兩次府試冠軍。但參加鄉(xiāng)試科考卻總不如愿,“明珠屢遺海底”。一直到37歲時,參加清道光癸卯科科考,才由優(yōu)廩生中式考取第一名副舉。副舉第一名,即僅僅以一個名次之差,未能名列正舉。
考中舉人即能授職授官,但副舉即算是第一名也不能。出榜之后,譚丙榆只好選擇回鄉(xiāng)繼續(xù)“授徒”,在攸縣的黃甲、東山兩書院執(zhí)教過相當長一段時間,二十來歲始,至45歲才離開。教學之余,譚丙榆仍刻苦研讀,“心苦熬波,志堅破浪”。
1851年,譚丙榆45歲終于開始“轉(zhuǎn)運”。朝廷通知他以副貢的身份入當時的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學習。三年之后,被點為職貢進士,并授新寧縣教諭。譚丙榆在負責全縣教育的同時,也熱心政事,撰文痛陳國家必須改革。他的文章受到曾國藩的關注, 1856年,曾國藩與譚丙榆開始了正式的面對面的接觸。
曾國藩既然“相”中了某人,一有機會就會設法提攜。1860年,立志改革舊制的咸豐皇帝正急需寫作人才,曾國藩便適時向咸豐帝舉薦,讓譚丙榆入中書省試任內(nèi)閣中書。他說,據(jù)臣下觀察,這人生性忠誠,又具有改革頭腦;且文筆穩(wěn)健,小楷極佳,可當此任!
曾國藩看人首要是品德,第二是才能。他將德才兼?zhèn)涞娜艘暈橹海谑且簿陀辛嗽鴩c譚丙榆的“麓山蘭譜聯(lián)盟”(互相交換帖子,義結(jié)金蘭)之事。
時任浙江杭州府事前提督譚鐘麟(湖南茶陵縣人,后官至浙江巡撫、兩廣總督)撰寫的《恭祝筠農(nóng)先生宗兄大人六秩壽亭》一文中,曾寫到了譚丙榆“登蓬苑,步木天”,以及與“曾滌帥麓山蘭譜聯(lián)盟”等事。文題中的“筠農(nóng)”是譚丙榆的別名。“苑”,指皇帝的花園,“步木天”即在“翰林院”任職之意,譚丙榆當時所任“內(nèi)閣中書”即是與此差不多的一個職務,但因為“編制”的原因,他還同時兼著新寧縣教諭的職位。內(nèi)閣中書的主要職責是根據(jù)皇帝的意見撰寫文件,官位等級不高,但權(quán)力大,有時能左右高層領導人的意見。但譚丙榆潔身自好,時人評價他“光明磊落,不受人私,難能可貴”。擔任內(nèi)閣中書期間,他獨立思考,勤于筆耕,頗得皇上、王公及權(quán)臣贊許,“寵錫龍章,沐到九乾雨露”。
1869年陰歷八月的一天,譚丙榆寫完一篇文稿,剛站起身,突覺一陣眩暈,又坐下靜休,一小時后竟與世長辭,終年64歲。曾國藩親自為他主持了追悼會。
譚丙榆猝然而逝,可推斷是血壓驟然升高,以致腦溢血,而血壓驟然升高的原因又可能是操勞過度。上文提到的曾國藩斷人、預測之能,不過是曾國藩從譚丙榆“手掌肉體薄”推斷其體質(zhì)弱、不經(jīng)操勞,從他“忠厚勤勉”的性格認定他必然會為公事不懈操勞,更兼譚丙榆“有才”,所謂“能者多勞”,故此推斷他“日后將死于任上”,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