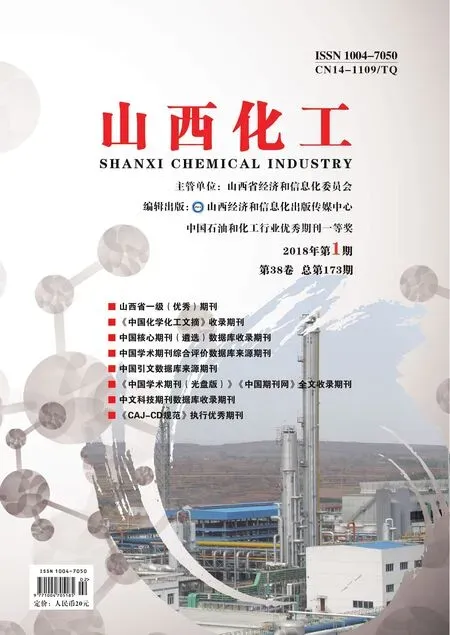固體加壓輸送泵在新型煤氣化技術中的應用
衛榮榮, 姚根有, 鄧 靖, 袁悅婷
(陽泉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化工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21)
我國煤炭資源豐富,石油資源相對短缺,大力發展新一代煤化工產業,以煤代油是我國技術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采取的一項措施[1]。新一代煤化工產業的主要特點就是煤的清潔利用。煤氣化技術是煤的清潔利用技術之一,在國際油價飆升、國內天然氣資源緊張、環保要求越來越高的背景下[2],一種新型的煤氣化技術應運而生。
該新型煤氣化技術借鑒航天領域對噴射器、氣體流場、高溫高壓材料的設計經驗,經過幾十年的研制開發,目前建有一套中試裝置,快速混合燒嘴使煤及氣化劑在爐內以柱塞流的形式進行氣化反應、耐高溫水冷壁內襯套(以渣抗渣)和固體加壓輸送泵超高壓密相粉煤輸送是其三大技術核心[3]。
本文重點介紹該新型煤氣化技術的固體加壓輸送泵超高壓密相粉煤輸送技術,將傳統氣流床氣化工藝[4-5]的進料系統同這種新型煤氣化技術的進料系統進行對比,突出該進料系統的先進性,以適應現代新型大規模煤氣化技術的需求。
1 新型煤氣化技術的進料方式
1.1 固體加壓輸送泵和超密相輸送系統
粉煤鎖斗系統氣力輸送技術的載氣一般為N2、CO2或合成氣[6]。N2作為載氣會對氣化爐產品產生不利影響,可增加后續合成氣系統惰性氣含量,降低有效氣成分含量及煤氣熱值。用合成氣代替N2,雖然可減少N2對合成氣的污染,但由于合成氣含有大量易燃易爆成分,危險性較大[7-8]。CO2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少工藝蒸汽的需求量,可作為理想的輸送載氣,且后續產品氣不會由于載氣為惰性氣體而降低產品氣的熱值及有效氣成分,同時還可改善產品氣的組成[9]。
與粉煤鎖斗加壓進料系統相比,濕式煤漿進料系統擁有升壓更高、無需使用惰性載氣、操作及控制計量簡便、進料連續等優點。缺點是水煤漿中僅有部分水是氣化需要的,多余的水分需要加熱到氣化溫度蒸發,氧氣消耗比干煤粉消耗要高,且冷煤氣效率低[10-11]。此外,水煤漿濃度、黏度、粒度分布特性變化較大,給水煤漿加壓輸送帶來了不穩定因素[12-14]。
該新型煤氣化技術摒棄上述2種進料系統的缺點,其進料系統采用固體加壓輸送泵和超密相輸送系統,氣化爐煤粉進料采用特殊的分流器對煤粉和氧氣進行均勻分配,保證氣化爐的流場為柱塞流,從而有效提高氣化爐的氣化效率。該設計為一種全新的設計,固體加壓輸送泵的示意圖見第100頁圖1。該新型煤氣化技術的固體加壓輸送泵可以取代傳統氣化系統中的鎖斗系統,上部連接低壓料斗,下部連接高壓料斗。該新型煤氣化技術的超密相輸送系統及分流器置于高壓料斗及氣化爐噴嘴之間,使得高壓料斗中的高壓煤粉勻速、均勻、穩定地送到氣化爐的噴嘴中。
1.2 固體加壓輸送泵主要設計特點
1)直線履帶概念(高效和可擴展);
2)商業組件的最大使用率;
3)可維護(快速零件更換);

圖1 固體加壓輸送泵示意圖
4)高壓能力(可達到8.3MPa)。
具體運行如下:干燥后的煤粉儲存在干燥煤粉收集過濾倉,煤粉通過重力作用進入固體加壓輸送泵的頂部,固體加壓輸送泵將煤粉加壓到5.3MPa,并儲存在高壓加料斗中。在高壓加料斗中,通過超高壓密相輸送系統將煤粉輸送到氣化爐的頂部分流器。
2 固體加壓輸送泵相較于傳統進料方式的優勢
1)固體加壓輸送泵流程簡單,無充卸壓操作,無需加壓輸送氣,程控閥門設置少,省去了流程復雜的鎖斗流程,運行上減少了輸送氣的消耗,操作更簡便。固體加壓輸送泵的電耗很低,故加煤系統投資成本更低,比煤鎖斗方案大約低20%~30%。
根據技術成熟的航天爐生產數據[15-16]和該新型煤氣化技術擁有公司提供的相關數據,對鎖斗流程和固體加壓輸送泵流程進行投資和運營成本比較,見表1。

表1 鎖斗流程和固體加壓輸送泵流程對比表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看出,固體加壓輸送泵流程比鎖斗流程投資節省853萬元,年運營費用節省5 120萬元。從投資和運營成本角度來看,固體加壓輸送泵進煤流程優于鎖斗流程。
2)煤鎖斗的程控閥故障率高,可靠性沒有固體加壓輸送泵高,固體加壓輸送泵的不間斷運行周期的設計期望值為1年。
3)固體加壓輸送泵更容易大型化。
4)固體加壓輸送泵的框架高度較傳統加煤鎖斗低。
3 結束語
粉煤鎖斗系統進料技術和濕式煤漿泵加壓進料技術在煤氣化技術中有廣泛應用。但在應用過程中,粉煤鎖斗系統進料技術存在輸送壓力不高、粗煤氣有效成分受載氣影響且帶來較高的后系統放空量、輸送系統密封及計量技術復雜等問題。濕式煤漿泵加壓進料因其輸送介質含水多、煤耗氧耗高而使有效氣含量和冷煤氣效率相對較低。固體加壓輸送泵超高壓密相粉煤輸送技術摒棄上述2種進料系統的缺點,其進料系統采用固體加壓輸送泵和超密相輸送結合,利用電機帶動履帶運動產生的摩擦力及擠壓力,將低壓煤粉送入高壓料斗中。固體加壓輸送泵目前所顯現出的經濟性及實用性等優勢奠定了其在未來煤氣化技術中將具有重要地位。
參考文獻:
[1] 陸小泉.我國煤炭清潔開發利用現狀及發展建議[J].煤炭工程,2016,48(3):8-10,14.
[2] 趙麥玲.煤氣化技術及各種氣化爐實際應用現狀綜述[J].化工設計通訊,2011,37(1):8-15.
[3] 曹正元.PWR煤氣化技術在中國市場的技術先進性及應用環境分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13.
[4] 霍錫臣,蔡文生.各類煤氣化爐的特點與適應性分析[J].煤化工,2009,144(5):12-16.
[5] 汪壽建.現代煤氣化技術發展趨勢及應用綜述[J].化工進展,2016,35(3):653-664.
[6] 潘響明,郭曉鐳,陸海峰,等.不同載氣供料對工業級豎直上升管粉煤氣力輸送的影響[J].化工學報,2016,67(4):1169-1178.
[7] 鄧曉陽,周少雷,謝京選,等.選煤廠機械設備安裝使用與維護[M].2版.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08.
[8] 張臘,米金英.干煤粉加壓氣化技術的現狀和進展[J].潔凈煤技術,2012,18(2):74-78.
[9] 夏支文,井云環.CO2作為密相輸送載氣在GSP氣化技術中的應用[J].潔凈煤技術,2012,18(5):49-51.
[10] 唐宏青.碳一化工新技術概論[M].成都:氮肥與甲醇編輯部,2006.
[11] 岑可法,姚強,曹欣玉,等.煤漿燃燒、流動、傳熱和氣化的理論與應用技術[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7.
[12] 邵迪,代正華,于廣鎖,等.固定床氣化與氣流床水煤漿氣化集成的能量與經濟分析[J].化工學報,2013,64(6):2186-2193.
[13] 崔意華.壓力、煤漿濃度、氧煤比對水煤漿氣化的影響[J].化肥設計,2010,48(5):23-26.
[14] 譚心舜,程樂斯,賈小平,等.德士古煤氣化工藝CO2排放分析[J].化工進展,2015,34(4):947-951.
[15] 管蕾.激冷式氣流床粉煤氣化爐模擬研究[D].上海:華東理工大學,2016.
[16] 唐佳.新型頂部多噴嘴氣流床氣化爐的數值模擬[D].杭州:浙江大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