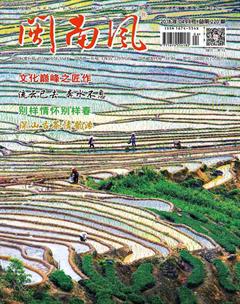記憶
莊國宜
前些日子,溫州的一位詩友發來材料,要我幫他尋找先人。他說,他的祖先是從南靖縣居仁里開花散葉遷居溫州的,始祖朱一輪是朱熹的第十七代孫裔,自明朝崇禎元年遷居荊谷三甲已有三百八十多年,溫州朱姓子孫也繁延昌盛,已有四千余人。
他還說, 水有源,樹有根,溫州族人渴望找到先祖,認祖歸宗,成全心愿。
詩友尋根誠心感動著我。我想到了縣文史研究員陳春梅女士,立刻把有關的信息發給她,以求得到她的支持。陳女士辦事干練、俠膽心腸,一會兒,她就發回了有關居仁里的資料。嘿,明末清初的居仁里幾乎涵蓋了今天的整個縣域,真要尋找,可要海底撈針了。
但她說,朱姓在南靖是小姓,船場、南坑有過朱姓記載,現在都不存在了。較大可能應該是靖城,那里有朱姓村子,龍海程溪也是范圍之內,而且明末、清朝南靖縣城就在靖城。
我立刻把有關信息轉發給詩友,就想成全他的心愿。
在儒家文化里,族親,族緣,族“根”屬于文化記憶,那是一種基因,有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只是我們有一段時間忽略了它的存在。
前年正月十五,我參加了奎洋莊氏大宗祠的祭典,廣東的,江西的,四川的,廈門的,以及縣內各村人馬,都是一隊隊。據說四川族人是第一次回鄉祭祀,顯得特別激動,其中有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還聽說有許多老人想來,后因組織者擔心路途遙遠,車船勞頓,為了安全起見進行限制,一些老人才取消行程。
奎洋莊氏族人是六百年前從廣東揭陽遷居過來的,綠水青山的滋養,族群不斷壯大,已達十五萬之多。這期間許多族親二次出征,遷廣東,遷江西,遷四川,遷臺灣以及海外。一種說法現在臺灣族親人口最多,有五萬余人。
這是美好的人文景觀,也是一種人文記憶。
2010年,我參加山西文藝采風,參觀晉祠時,一位王姓的隊友特意去珍藏館查族譜,也許他早就知道自己血脈來源。真找到根據,晉祠王姓族譜有南靖王族南遷的記載。我們玩笑地說,此行你收獲最大,找到了自己的“家”,他笑著,顯然是一種滿足。
前不久在閩南師范大學莊舍老師的“悅讀時光”里,遇到一位從臺灣來閩師大工作,且就要返臺的王博士。她自稱南靖人,說遷臺已有四、五代了,祖上只留下南靖的地名,具體不知在那兒。
她的述說,柔聲細語,顯然有點沮喪的情緒。是呀,南靖就在身邊,她卻找不到回家的門。
不管是王隊員晉祠尋根,還是王博士南靖人自居,都是“根”的情結,都是文化記憶基因,烙上飲水思源的記痕,也是心靈棲息地美好的記憶。
然而,歷史常常會誤筆的。有時間的原因,也有人為的破壞。像“文革”時期,講“階級情感”,不講親情、族情,家譜、族譜屬于反動的物證。沒收的,燒毀的,文化與歷史記憶出現了空檔,“根”的守望失去根基。就說臺灣吧,閩南人、客家人占的比例很大,他們的先人飄洋過海,為臺灣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而上世紀幾十年的兩岸互為封鎖,給族群聯系留下了遺憾。就像王博士那樣,只知道自己是南靖人,卻不知道“根”在南靖哪兒。
最近一段時間,我對家鄉奎坑村一個叫“雜姓樓巷”的地名產生了興趣。那是一條幾百米長的巷子,兩邊是土樓房。說“雜姓",從我記事起,這里除了一戶劉姓人家,其余都是莊姓。“雜”義跑到那里去了?
我請教了村里幾位老人,證實了村里確實有過毛氏,楊氏,章氏人家,后來他們遷走了。現在的張氏、莊氏、簡氏都是后來居上的住家。他們在村子里生活的時間,也只有三百多年。
更有趣的是,我還了解到,民國時,或許更早,張氏、莊氏雖同屬一個村子,卻被分治于兩個行政機構,張氏屬于曲江鄉管轄;莊氏屬于奎洋鄉管轄。村子中央一條水溝就是疆界分割線。
這是典型的族群紐帶轄治理念的見證,也是舊時鄉紳管理鄉村的例子說明。
當然,記憶也會殘缺的 ,在奎坑村幾處山腳,堆積著許多瓷器碎片。這是明清時期的窯址,有四、五百年了,也許更長。站在碎片前,我常陷入沉思:山村曾一度輝煌,窯工制瓷,師傅燒窯,挑工把一擔擔的瓷器,挑到山外,送到月港,銷到東亞、南亞、歐亞等地。
記憶是遺忘的對面,而我們許多不曾記憶,本應擁有的記痕卻空檔著。更可怕的是人為地塞入了許多虛假信息。似乎我們更習慣接受強調性的記憶和選擇性的記憶,這不能不說是人性的一種不良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