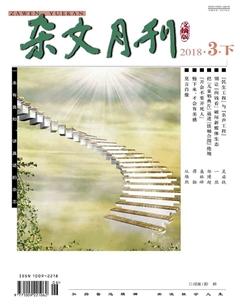醒與醉
趙威
筆者參觀過中國國家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幾家博物院館,觸目所及皆琳瑯珠玉,印象最深的是各類酒器:觥、觴、酌、卮、角、觶、觚、罌、蘨、缶、卣、尊……品種之多,令人咋舌,幾無法詳盡,足見國人尚酒風氣之源遠流長。
尤其文人自古與酒有不解之緣,時醉時醒,醒與醉之間如何把握火候,既是一門學問,也是為人處世之道。“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屈原醒過了頭,不能“哺其糟而歠其醨”,只好自沉汨羅江;“造飲輒盡”一醉方休的陶淵明,則醉過了頭,拋卻烏紗帽,作《乞食》一首,讓后世爭論不休。明人陳繼儒有《酒顛小序》一篇,言“太醉近昏,太醒近散”,大概就是以上兩類人,只有“非醉非醒”“胸中浩浩”的半醉半醒狀態,才能進入拋卻榮辱,甚至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
此外,醒與醉之間大致還有幾類狀態。
醒中求醉型,認為醉比醒好,但醉不失志。例如,唐·房玄齡等人編著的《晉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九》記載,魏晉名士借酒助興,崇尚玄學,抒發人生感悟、社會憂思、歷史慨嘆。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作《酒德頌》,嗜酒如命,任性放誕,縱酒脫衣,赤身裸體。他常乘車攜酒,讓人帶著鐵鍬跟在后面,囑托:“死便埋我。”一次,劉伶飲酒過度,害了一場大病。可他還是饞酒,于是開口向夫人要。劉夫人很生氣,把酒倒了,把裝酒的瓶子摔了,哭勸劉伶道:“夫君喝酒太多,不是養生之道,一定要戒掉啊!”劉伶說:“我自己戒不了,只有在神前禱告發誓才可以,請你準備酒肉吧!”夫人高興地說:“就按你的意思辦。”于是,她把酒肉放在神案上,請劉伶來禱告。劉伶跪在神案前,大聲說道:“老天生了我劉伶,因為愛酒才有大名聲,一次要喝一斛,五斗哪里夠用?婦道人家的話,可千萬不能聽!”說罷,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來,不一會兒便醉醺醺了。魯迅說:“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劉伶之醉是借助自己的放浪形骸,表達對舊禮教的強烈反抗精神。
自醉型,酒不醉人人自醉。醉翁歐陽修“飲少輒醉”,當屬此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樂,在與民同樂。歐陽修的醉是沉醉,是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在滁州這方小天地實現而陶醉,他的內心是清醒的,自詡“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而陶淵明在醉與醒之間就未能做到這一點,只好將他的夢寄托在了桃花源。
得糊涂型,以糊涂對糊涂。鄭板橋的名言“難得糊涂”,由清醒入糊涂難上加難。因此,若做到了,就是“得糊涂”。隋唐之際的王績嗜酒,能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以醉對醉,以糊涂對糊涂,“哺其糟而歠其醨”,屈大夫未做到的,王績做到了。貞觀初,太樂署史焦革善釀酒,王績自求任太樂丞。后因焦氏夫婦相繼去世,無人供應好酒,于是,他棄官還鄉。心中對現實的不滿,化作消極頹廢,這種人缺乏積極向上的理想。
裝醒型,看似清醒,實則糊涂。臺上大談廉潔,臺下大肆貪腐,貪官當屬此類。這些人平時大談廉政,看似很清醒,其實對黨紀國法、人民利益醉眼視之,醉態處之,難以清醒!
- 雜文月刊(選刊版)的其它文章
- 倘若齊白石去當官
- 感念祖先
- 別讓“向錢看”破壞新媒體生態
- 茶客留言
- 思露花語
- 做人,里子要講究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