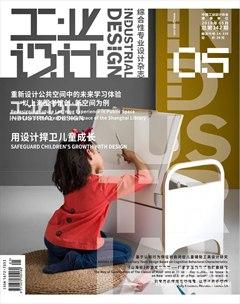現代漆立體創作的幽玄情結
林卿

摘要:日本民族將幽玄美學傳播至世界各地,然“幽玄”一詞實則師出中國,日本民族從中攝取并融合獨特的民族意識后提煉而成,繼而應用在生活、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對日本傳統工藝,尤其是漆藝也深有濡染。中國曾是漆器大國,卻在漫長的歲月流逝中走向衰弱,在工藝復興大潮下,漆藝從衰弱走向振興,但面臨著如何實現傳統材質與當代審美理念相平衡的問題。日本在現代化造型革新的同時保持民族色彩,重視傳統文化,將自身民族文化積淀融入漆藝創作中,成就了今天日本漆藝創作獨有的審美面貌,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周邊國家的漆藝創作。
關鍵詞:幽玄美學;漆藝創作
中圖分類號:TB4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碼:1672-7053(2018)05-0086-02
1 釋“幽玄”
幽,深也,微也,冥也,隱也,昏也。《說文》段注:幽,從山,猶隱從阜,取遮蔽之意。玄,黑也,天也,虛也,幽遠也。幽玄一詞取源于中國,其審美觀形成于日本中世,是日本美學觀里的一個重要的審美意識。在藝術美學上首推大西克禮的幽玄論,他認為“幽玄”的核心是余情,講究境生象外,意在言外,追求一種以神似的精約之美,引發欣賞對象的聯想和想象,傳達出豐富的思想感情內容。具體闡述為:
1) 隱藏不露,籠之于內。
2) 與露骨、直接、尖銳的感情表現相反,具有優美、安詳、柔和性。
3) 帶有與隱微蔭翳相伴的寂靜。
4) 深遠,特別是之精神上的東西,如深奧難解的思想。
5) 具有內在的充實性,其中凝集著不可言傳的意蘊。
6) 有一種神秘性和超自然性,雖關乎宗教、哲學的觀念,但仍可感受到其中的“美的意識”。
7) 以一種非合理的、不可言喻的、微妙的意味為主。
2 漆立體概念
喬十光對漆塑的解釋是,漆塑是漆藝的立體造型,是漆藝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漆立體的產生是現代藝術思潮影響下,日韓藝術家們對漆器創作的創新之舉。立體形式的漆藝術,擺脫了因依附器物實用性而造成的器物裝飾功能的局限性,而且使漆藝術的造型空間急劇擴大,人們可以在悅意的狀態中完成各自的藝術審美行為和藝術造型行為。它的特征在于打破了不同樣式之間的隔閡與局限,呈現出多元化創作特征,著眼于不同藝術形式的吸收融合,在漆藝創作方面出現了抽象立體的造型形式,它既拋棄了原有漆器的使用目的,失色于傳統意義上的器,又不是客觀實際存在著的具象事物,而是純粹抽象的、獨立的、完整的審美對象。
3 幽玄美學與漆藝之契合
露骨、直接、尖銳一類,在幽玄審美中向來不被待見,幽玄美學偏愛深遠、含蓄、微妙。而漆藝材質所傳達出的那種靜謐、溫潤的意境,折射出靜觀內省、溫柔淳厚的氣質,與幽玄所推崇的深邃悠遠等屬性不謀而合,不論是幽玄美學還是漆藝作品,它所呈現的都是一種內斂和沉寂的審美體驗。
4 當代漆立體創作的幽玄情結
4.1 從材料角度上窺探幽玄
當代漆立體的幽玄情結首先體現在色彩上,天然大漆渾厚蘊藉,包容性強,又具有深邃靜謐的色彩體現,能夠恰如其分的表現幽玄的意境。而在漆立體創作中中,通常使用單色素髹或者異色髹漆。單色素髹就是通體髹涂一種色漆,通常是黑漆、朱漆,金漆等,追求材料質地美感。在漆畫中,我們能夠看到許多充滿暄鬧氣息的作品,但在器物中,幾乎是清一色的素髹。偶爾蹭幾縷單薄的金銀色,在可控范圍內,不暄賓奪主,一撮點綴。“巨大的單色畫布占據了整個視野,但卻提供了形式的不充足的結合,來掩飾視覺的辨認,它促進了一種被稱為純感覺的狀態。在一個堅持將注意力集中在上述各點之上的觀賞者心目中,它們可以產生一種與東方式沉思冥想相似的狀態。”
在談漆立體的色彩時,必然少不得談“黑”。吳冠中說,素白的宣紙與墨黑的漆,都極美,樸素大方之美,是經考驗了幾千年而不被淘汰之美,是我國傳統藝術棲止的溫床。中國畫的空白給人以想象的中間,大漆藝術中的漆黑也給人以想象的空間。黑色也是最接近大漆的藝術本質,最能體現其魅力的一個顏色。黑色代表著沉著,內斂與含蓄,經過推光之后呈現出來的瑩瑩光澤和半透明效果,它有助于讓觀者的心平靜下來,進而進入自省的狀態,與東方人獨有的幽玄情結較為貼合。
南泉說道不屬知亦不屬不知,屬于意識的美才是滿足之美,真正的美是有意無意的。雙色素髹中,因其人畫一半,天畫一半的漆變之美,常常出現變幻莫測的畫面,虛虛實實,有意無意。漆打磨的不確定性,讓微妙的的變幻昭然體上,在痕跡的邊緣實現溫柔的過渡,使之目光悠然滑行于畫面,造訪每一個微小的起伏變化,每一個似有似無的行蹤,不必跳躍呼嘯,只一葉落地便鏘然驚魂,正如佛理禪教所謂白馬入蘆花,塊然一片,卻真耐尋索。
4.2 從造型角度上把握幽玄
當代漆立體創作造型多是抽象的,正所謂大象無形,最好的繪畫是沒有具體形態的,無限的抽象就具有無限的可能性,越接近具象的形,表達出的僅是那一點點淺薄的東西,其他的所有東西、那個廣闊無垠的世界就不復存在于其中,被斥離在表現范圍之外。
抽象形象往往是意味的或神秘的,它通過博觀取象,舍棄具象形把握抽象的神,摒棄繁雜和瑣碎,提煉簡約的造型,多運用造型形成對比,簡單大方,力求將優美發揮到極致,創造典雅的形象,在一種簡潔的秩序中保持韻律。同時,造型的單純化簡約化以接近事物的本質,是獲得空靈感最好的方法,其中蘊含的深邃清悠的美,廣闊深遠、無限又朦朧的印象,能帶給我們更高層面的意識啟發,促進人的聯想、體味和補充,于意猶未盡的意境中體會超然物外的審美感受。
當代漆立體創作大多遵循去繁為簡的理念,以日本漆藝家田中信行為例,他的《流動系列》作品造型簡練,線條干凈利落,且多用素髹,強調大漆的自然與不事雕琢,無多余裝飾,曲線多而轉折少,極盡簡約之能事,含而不露,平淡質樸,凝練的造型,勻稱的比例,溫潤的質感折射出雋永的美感。雖無繁復的色彩與花紋,卻展示出很強的現代設計理念和東方美的內涵,表達出一種簡潔的、獨特的、極富靈感的、具有生命特質的視覺形式美感,并且注重空間關系的處理,使得造型周圍的場在視覺上不斷括展。形體的起伏與轉折,流動的曲線都飽含藝術家的靈感與創意,而光在作品上產生流動的幽深感,更喻示了生命的流動。
4.3 從跡象角度上追溯幽玄
跡是一物作用于另一物產生的痕跡,在漆立體中就是大漆附麗于立體造型上的痕跡,包括肌理、質感、色彩、也包括麻布、瓦灰等一系列綜合材料在內的跡理因素。象是物的形狀和體量。在一幅作品中,一個完整的象必定有相應的跡來充實,跡也必定產生相應的象。落筆成跡,因跡生象,漆立體創作就是一個做跡留痕的過程。用無微不至的實有之跡,造成一無所有的虛無之象,卻又臨近極點的充實。通過堆疊、做跡、產生余、厚、濃的視覺效果,或是用跡來分割形體,跡藏匿在鋪天蓋地的色域之中,實現微妙莫名的朦朧效果,實現視覺的豐富性、光與影的聯想、迷幻的神秘感。
如胡秀姝《圓之余》,器上張貼銀箔給視覺設置障礙,從跡的遲滯、模糊、缺損、溶解、隱退、剝蝕、延緩欣賞的過程,而不可名狀的跡,讓人聯想到清幽虛無,它以象外之象,不測之意描繪出一個極靜的空靈意蘊,透露出疏簡素淡,生拙含蓄的意味,從表面的視覺感知,深入到心靈的縱深疆域。再如李永清《循之路》,側面斑駁粗麻的肌理象征著滄桑,麻布的外露,伴隨著澀的量感與深度產生,澀將空之美凝結,給作品又增添了一份質樸的色調,與正面單純大度的黑色素髹形成互補。跡是殘跡,破損、模糊、象是靜象,對于整件作品而言,以素色黯淡為整體基調,表達深沉的緬懷之情,實現色彩與情緒的和諧共生。靜中寓動,似靜而實動,外靜而內動,面上沉靜如水,細水流長,實則空靈悠遠,傳達出清幽空寂的境懷。
5 結語
日本文化與我國古代文化淵源頗深,都擁有東方的含蓄美的特點。將幽玄之美作為切入點,探究幽玄美學與漆藝創作的共通之處,作為透視中國文化精神一隅的窗口。通過借助日本幽玄對藝術創作的影響啟發國內的現代漆立體的創作,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用以指導當代漆立體的創作,引發社會公眾關注漆藝的當代轉型并緬懷、回望東方的漆藝傳統,追循勾沉中國傳統中幽玄、虛靜、閑寂、枯澹、典雅等豐富的文化特質和深邃的精神資源,東方審美之思致始終存在于我們的意識當中,甚或遁入內心深處,當我們開始思考、書寫、設計之時,它便自然而然浮現出來,寄予我們文化之信心與創造之力量,從而在國際漆藝界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另一面,幽玄美學教給我們在藝術創作中保持一種寧靜、淡泊的心態,一種清靜空寂的意象,一種意猶未盡的形式美,希望能讓我們這個過份暄囂的世界多一分安寧、平和、靜謐的氣息和含蓄內斂能發人深思的色彩。
參考文獻
[1]大西克禮.幽玄·物哀·寂[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
[2]鐘孺乾.繪畫跡象論[M].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3]王向遠.釋“幽玄”——對日本古典文藝美學中的一個關鍵概念的解析[J].廣東社會科學,201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