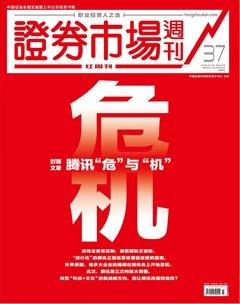注冊制改革不能刻意回避
黃湘源
新發審委又要換屆了。從時間上看,這一屆發審委換屆與被延遲的注冊制改革將重新提上議事日程應有更大的關系。自注冊制改革被再次延遲后,不知是由于某種刻意還是非刻意的“諱莫如深”,這件事似乎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線,就此而言,新發審委如果還是穿新鞋走老路,則換與不換又有什么太大區別呢?
問題要敢于正視、抓住并解決
劉士余主席上任初始曾說,“注冊制是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的制度基石”。并明確表示:“必須搞。”如果說“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制度”等確實反映了A股市場和成熟市場在歷史背景和法制環境方面的某些差異,一旦實行注冊制改革,在這些方面勢必也將有可能會遇到不小的困難,但這也并不可以作為不再聚焦注冊制的理由。注冊制改革被延遲多年,至今對于要不要推行和如何推行仍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問題無處不在,敢不敢正視問題、抓住問題并想辦法去解決問題,結果必然大不相同。但令人遺憾的是,恰恰在注冊制改革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資本市場似乎呈現了選擇性的人格分裂,講問題不依不饒,講改革深加隱諱,似乎除了繞道而行,沒有一條路可以通往注冊制。
不可否認,這些年A股資本市場在重視監管、加強監管等方面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績。監管層一方面堅持不懈地實行監管前移,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一查到底。甚至順藤摸瓜追查到海外,對一些信息披露不實的帶病IPO嚴格把關,弄虛作假欺詐上市者毫不留情地予以強制退市。另一方面,對于操縱市場,操縱價格,擾亂市場秩序,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更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重監管、嚴監管、強監管,不僅維護了市場秩序的穩定,更是旗幟鮮明地彰顯了市場的正義。
不過,在《證券法》尚未修法到位的前提下,新時代的投資者保護還是不可避免的遇到了新問題。上市公司違法造假欺詐仍有沒被退市的案例存在,一些受害的投資者索賠無據。如果投資者保護都可以被所謂的“投資者教育”替代,那么一句“股市有風險,投資須謹慎”,豈不也可以將投資者一切的虧損問題都打發給投資者去尋找自身的問題了嗎?這又哪里還有什么實質性的投資者保護可言呢。
問題不會因刻意或非刻意回避化有為無
歷來市場暴跌的一些深層次原因告訴我們,有些風險并不是投資者想回避就能回避得了的。2018年,正當一度沖上3587點的股市仿佛給人們帶來了重回牛市之幻覺的時候,A股突如其來地以提供特別通道的方式推出獨角獸IPO和CDR。如果不是小米請緩,BATJ等獨角獸巨頭圈錢的胃口一定不會比一開口就是數十億數百億融資規模的富士康們小多少。CDR雖然之后被暫停,但市場卻被一個比一個更為巨大的融資圈錢意圖嚇怕了,至今也未能恢復元氣。
獨角獸上市不僅有可能遇到“同股不同權”的問題,還有個高新技術企業盈利不盈利的問題。美國由于早就實行了注冊制,這些都不再是問題。但香港就不同了,因糾結于“同股不同權”而錯失了阿里巴巴之后,香港監管層主動發動了一場深入人心的大討論,才有了接受這一深刻制度性變革的思想準備和可行性行動計劃。至少,香港的發行制度通過這一次的改革和創新,或不無希望地向注冊制更靠近了一步。而我們卻搶在人家前頭搞引進獨角獸這種新鮮事物,快則快矣,不料卻除了快出急不可待的獨角獸大圈錢之外,不僅再次給市場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市場對于注冊制的恐懼無形之中似亦進一步有所加深。
市場一次又一次地因為政策變化的突如其來引發了重大的動蕩,且市場的動蕩又無不給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虧損,可政策面卻沒有以此為導向,對投資者保護采取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的對應措施。相反,就在股市一次又一次地暴跌甚至跌破“熔斷底”的時候,有關方面非但沒有引起應有的反思,反而借“入富”的名義更進一步擴大了引外資入市的比例。但這支被當成中國股市未來生力軍的外援,能否真的會成為救苦救難的“解放軍”結果還有待觀察。
問題是客觀的存在,不會因為任何刻意還是非刻意的回避而化有為無。相反,只有正視問題,才有可能更好地發現問題和有效地解決問題。只有找到客觀存在的問題,才談得上掌握解決問題的主動權,從而順利地將改革推向前進,并在前進的道路上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對此,我們應該喚起必要的理性認識和應有的責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