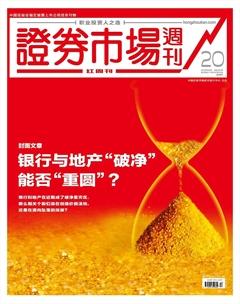云南能投14億并購關聯企業 “自己人”犯錯上市公司買單
王宗耀
5月底,云南能投發布公告稱,擬以合計超過14億元的價格購買新能源公司持有的馬龍公司100%股權、大姚公司100%股權、會澤公司100%股權和瀘西公司70%股權。這是云南能投自2016年由云南鹽化資產置換后的一次重大并購行動。
在完成資產置換的當年,云南能投2016年的業績表現似乎不錯,實現凈利潤2.6億元。然而好景不長,一年后的2017年,云南能投凈利潤便相比上年減少了1億元,只有1.6億元,降幅高達38.46%,如此突變似要再現2016年改組前的困境。或許正是在這種不利的背景下,云南能投積極展開了針對馬龍公司、大姚公司、會澤公司和瀘西公司的股權并購,希望能通過此次并購拉動自己的業績增長。
對于此次收購,《紅周刊》記者在梳理重組預案時發現,云南能投并購的四家公司均為“自己人”,而這些“自己人”身上還存在著不少的瑕疵,一不小心,很可能使得上市公司掉進自家人挖的“坑”里。
標的之一馬龍公司涉嫌無證生產
云南能投本次并購的4家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均為陸上風力發電的項目開發、建設及運營,主要產品為電力。根據《電力業務許可證管理規定》(電監會9號令)第四條要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電力業務,應當按照本規定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除電監會規定的特殊情況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不得從事電力業務。因此,本次云南能投并購的四家標的公司,都必須要有電力業務許可證方可運營。根據并購預案披露,云南能投本次并購的四家標的公司截至目前為止雖然都已經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但《紅周刊》記者還是注意到,這幾家公司在此前的經營中似乎存在無證經營的問題。
以本次并購標的之一的馬龍公司為例,該公司是由新能源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出資2500萬元成立的,2014年股東新增貨幣出資1.44億元;2017年股東新增貨幣出資2237.96萬元,變更后的公司注冊資本為1.91億元。從重組預案披露的財務報表數據來看,該公司2015年時就已經實現營業收入2850萬元,其中包括標準電費收入1588萬元,新能源補貼款1189萬元,接網補貼款72萬元。該組數據說明,公司既然存在標準電費收入,一定意味著公司至少從2015年開始就已經在經營電力業務了。
然而奇怪的是,預案中披露的馬龍公司的《電力業務許可證》(證書編號1063016-01026)的發證時間是2016年3月30日,有效期20年,有效期間為2016年3月24日至2036年3月23日。也就是說,該公司是從2016年3月24日開始才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的,在此之前,其并不具備電力經營的資質。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該公司其實已從2015年開始就已經從事電力業務了,否則無法解釋公司的2850萬元營業收入來源何處。

馬龍公司在2015年未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的情況之下,就開始經營電力業務,顯然是違反相關規定的。根據《電力業務許可證管理規定》第四十條,未依法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非法從事電力業務的,應當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以并處以違法所得5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也就是說,一旦查實馬龍公司存在違規經營的情況,那么不但其2015年的收入可能會被罰沒,而且還有可能面臨數千萬的罰款,甚至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
此外,馬龍公司在沒有取得相關許可證的情況下,不但已經取得了標準電費的收入,而且還取得了新能源補貼,那么這其中又是否存在違規申請補貼的情況呢?總之,無論是沒有許可證的經營,還是違規申請補貼,這對于本次并購來說都影響重大,很可能會影響到并購重組的進程。對此,云南能投還得小心自家人挖的“坑”。
遠超收入的異常應收賬款
并購預案披露,云南能投本次并購的四家標的公司提供的電力主要為風力發電,屬于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風電上網電價高于當地煤電標桿上網電價部分,享受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云南能投在其披露的預案中表示,公司所建設的風力發電場以及電網接入工程在項目投入正式運營、開始并網發電時,已經符合補貼的申請條件,具有收取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的權利,與該收入相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符合收入確認原則,因此公司電費補貼收入、線路補貼收入與公司標準電費收入同時確認。此外,預案還表示,四家標的公司所收取的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和接網補貼是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直接相關,而且根據《可再生能源法》及其他國家政策規定,是連續的、可預見的、經常性的收益,因此視為經常性損益進行財務核算。事實上,標的公司的營業收入也正是由標準電費收入、可再生能源補貼收入和接網補貼收入三部分組成。

以大姚公司為例,該公司是由新能源公司2013年6月4日成立的,從該公司的財務報表來看,該公司2016年才開始正常生產經營,當年實現的營業收入總計為1377萬元,其中包括245萬元標準電費(見表2)、1055萬元的新能源補貼和77萬元的接網補貼。由大姚公司營業收入構成來看,正如并購預案中所述那樣,該公司將新能源補貼和接網補貼當做了經常性收益,核算為營業收入,但值得奇怪的是,該公司應收賬款的數據是大于營收的。
根據大姚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數據,2016年形成的應收賬款金額高達4508萬元,其數值竟然遠遠超過了自己的1377萬元營業收入。我們知道,應收賬款是伴隨企業的銷售行為而產生的債權,如果該公司已連續經營數年,則應收賬款的累計金額遠遠超過當期營業收入尚可理解,但問題在于該公司只是自2016年才開始正常經營,在經營的當年,應收賬款就遠超營業收入的做法就有點讓人難以理解了,難道該公司應收賬款中有很大一部分金額沒有被確定為收入?
從該公司應收賬款的構成情況看,在2016年應收賬款中,有4192萬元為尚未收回的新能源補貼,有316萬元為尚未收回的接網補貼。然而從該公司營業收入的構成情況看,當年這兩項補貼形成的收入金額卻分別僅為1055萬元和77萬元,遠遠小于了應收賬款的金額。
既然該公司將新能源補貼和接網補貼確認為營業收入,那么當年形成的兩項補貼均應該確認為營業收入,而這兩項補貼中沒有以現金或票據收到的部分是需要形成應收賬款的。由于這兩項補貼在報告期內并未收到,因此新能源補貼和接網補貼形成的應收賬款在理論上應與相應的營收數據相等才對,然而在該公司的報表中,這兩項形成應收賬款卻遠超相應的營業收入,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在2017年大姚公司的期末應收賬款中,新能源補貼應收金額和接網補貼的應收金額分別為9420萬元和688萬元。由于該公司這兩項補貼在2016年和2017年中一分都沒有收到,因此扣除這兩項的期初金額,大姚公司2017年新確認的新能源補貼應收金額和接網補貼的應收金額應該分別為5228萬元和372萬元。然而從收入明細來看,該公司當年確認的新能源補貼收入和接網補貼收入卻分別為4353萬元和318萬元。公司2017年確認的收入遠低于應收賬款金額的現實讓人費解,該公司的新能源補貼收入和接網補貼收入到底是按照什么依據來確定收入的呢?
除了大姚公司外,本次并購標的之一的馬龍公司也存在類似讓人費解的情況。正如我們上文所分析,2015年馬龍公司并沒有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因此其新能源補貼和接網補貼本身就存在可疑,雖然在該公司的審計報告中,并未披露2015年應收賬款明細,但就算其2015年開始經營,其應收賬款總額超過營業收入總額的合理性也是讓人懷疑的。此外,2017年期末的新能源補貼和接網補貼的應收賬款余額分別高達1.34億元和499萬元(見表3),而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三年中新能源補貼合計實現的營業收入與接網補貼合計實現的營業收入卻分別僅有1.08億元和426萬元,竟然也低于相應的期末應收賬款余額。

相較上述兩家公司的應收賬款數據的異常,本次收購的另兩家標的公司滬西公司和會澤公司卻不存在這種奇怪的現象,這兩家公司以上兩項補貼形成的應收賬款金額均遠低于相應的營業收入。
《紅周刊》記者認為,對于本次收購標的所形成的應收賬款遠超營業收入的奇怪現象,上市公司應該在并購預案中給出詳細、合理的說明才對,可遺憾的是,《紅周刊》記者并未從預案中找到合理的解釋。
蹊蹺的零壞賬準備
正如上文所分析,報告期內大姚公司和馬龍公司因補貼款形成的應收賬款金額遠超相應的收入金額,這導致這兩家公司的應收賬款金額異常巨大。其中,大姚公司2016年和2017的應收賬款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分別高達327.31%和134.92%(見表4),而馬龍公司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形成的應收賬款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則分別高達101.40%、90.34%和179.86%。其他兩家標的公司會澤公司和滬西公司應收賬款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則相對上述兩家公司較低。除此之外,令人更吃驚的是,以上四家標的公司的應收賬款在整個報告期內計提壞賬準備竟然全部顯示為0。
對此現象,并購預案雖然給出解釋,即四家標的公司的壞賬政策按照“單項金額重大并單獨計提壞賬準備的應收款項”和“按信用風險特征組合計提壞賬準備的應收款項”兩個標準執行,均認為“公司風力發電銷售形成的應收電網公司標準電費、可再生能源補貼及接網補貼,經個別認定,不會出現壞賬風險,不歸類到賬齡組合計提壞賬準備,作為‘無回收風險組合不計提壞賬準備。”而這幾家公司的收入均來自他們認為的“無回收風險組合”,就導致這幾家公司所有的應收賬款壞賬全部為0計提。可問題在于,這種解釋真的合理嗎?

實際上,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分析,以馬龍公司為例,該公司2015年并無電力業務許可證,而其卻存在電力經營的情況,這可能導致該公司當年營業收入被罰沒,其新能源補貼和接網補貼本身也存在風險,而并非是其認定的“不會出現壞賬風險”,因此,應該按照比例計提壞賬準備才合理的。
另外,本次并購的四家標的公司應收賬款的欠款方雖然均為地方電網公司,但這并不意味著公司就不存在回收的風險,0計提壞賬準備顯然是不夠謹慎的。以同為電力企業的上市公司國電電力做對比,該公司應收賬款也多為各地方的電力公司,但從其2017年年報來看,國電電力還是按照比例對自己的應收賬款進行了相應計提,其2017年應收賬款壞賬準備金額合計計提了1.76億元,綜合計提比例為2.95%。

如果馬龍公司也能對其應收賬款進行壞賬準備計提,即使參照國電電力1年內6%的比例計提,其報告期內合計需要計提的壞賬準備就超過了千萬元,而考慮到其2017年凈利潤也不過1200多萬元,如此看來,馬龍公司不計提壞賬準備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果其他幾家標的公司也均合理計提壞賬準備,那么這幾家標的公司的凈利潤恐怕也是慘不忍睹,而這種結果很可能會影響到標的公司未來幾年的業績預測,進而對本次并購的交易價格帶來一定的影響。
云南能投本次并購的四家標的公司均為公司控股股東能投集團旗下的新能源公司控制的企業,因此這四家公司也算是上市公司的“自家人”,本次交易是屬于關聯交易的。在此背景下,如果采用激進的應收賬款計提政策,則會粉飾標的公司利潤,進而做高了交易價格,此舉的目的難免讓本次并購有了瓜田李下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