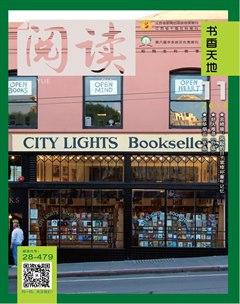宮崎駿:風起的日子里修補童年記憶
梁爽
創作一部動畫也就是創造一個虛擬的世界,這個世界慰藉著那些失去勇氣的、與殘忍現實搏斗的靈魂。
——宮崎駿
宮崎駿,日本著名動畫導演、動畫師及漫畫家,出生于東京,1963年進入東映動畫公司,1985年創立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動漫電影在世界動漫界獨樹一幟,迪士尼稱他為“動畫界的黑澤明”,《時代周刊》評價他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2014年11月9日,宮崎駿獲頒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人生被一部
動畫片改變
宮崎駿出生于1941年的東京都文京區,在四個兄弟中排行第二。宮崎家族經營一個飛機工廠,屬于軍工企業,所以在戰爭后期物質匱乏時也能溫飽,宮崎駿因此度過了相當自由的幼年生活。然而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宮崎駿卻意外地對家族的特權產生了懷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因戰時疏散,舉家遷往外地。
由于身體不好,宮崎駿少年時不擅長運動,但是對靜態的繪畫很有天分,特別是對于飛機尤感興趣。他后來許多作品當中都反復出現飛行的概念。宮崎駿小時候就擅長繪畫,非常喜歡手塚治蟲和浦茂的漫畫作品。
1958年,日本最大的動畫制作公司“東映動畫”,拍攝了時長75分鐘的動畫電影——日本第一部彩色動畫片《白蛇傳》。當時尚在準備高考的宮崎駿,在一家廉價影院看了《白蛇傳》,他的一生被改變了。
“與他們的執著比起來,我為自己感到非常地羞愧,哭了一整個晚上。”不管在宮崎駿的記憶中有多少支離破碎的無助與哀傷,這件事始終是最刻骨銘心的。他深深戀上了堅忍不拔、一心一意、為了生活跌跌撞撞向前的白蛇。
1963年,大學畢業的宮崎駿以最后一批正式雇傭社員的身份,進入了東映動畫,開始了他的動畫師生涯。兩年后,宮崎駿結婚了,妻子恰恰是動畫電影《白蛇傳》的制作人大田朱美。從此,宮崎駿再也不必從異域的古老傳說中虛擬“令人害臊”的暗戀對象了。
然而,無法回避的是,宮崎駿在東映的事業發展遲緩,妻子無論在資歷還是收入上都比他高出一大截兒。很多人甚至認為前輩級的大田朱美在動畫創作上顯然更有實力,也更有前途,為了丈夫辭職當主婦實在是斷送前程。直至1970年離開東映,宮崎駿一直做著原畫等初級工作,始終沒能獲得一次編劇或執導的機會。
宮崎駿在動畫生涯的第17個年頭,獨立執導了自己的第一部動畫長片《魯邦三世:卡里奧斯特羅之城》,并獲得日本第一流動畫大獎“大藤信郎獎”。然而,在評論界廣受好評,并不一定意味著票房上的成功。事實上,《魯邦三世》不只在影院留下了大片空座,還為宮崎駿“預留”了長達三年的“空窗期”。
那時候,科幻題材開始流行,宮崎駿的作品常因為與所謂的時尚格格不入,被人戲謔為帶有“一股泥巴味兒”。好在日本第一本動畫雜志《動畫志》的時任總編鈴木敏夫有一雙慧眼,真心賞識并信任他,不辭辛勞為連載漫畫《風之谷》搬上大銀幕奔走游說,成為了讓動畫作品堂堂正正跨入電影大門的幕后功臣。這是在1984年。
第二年,日本著名電影人、德間書店首任社長德間康快為“吉卜力工作室”的創建解決了資金難題,從此,宮崎駿的時代開始了。
父母的缺席使得孩子“被需要”
宮崎駿從童年起便罹患腸胃病,孱弱的身體使他在跑不能跑、跳不能跳的生活中愈加自卑。那時候,每當想到這樣的自己給父母添了多少麻煩,就有無盡的自責從心中生出來。為當一個“好孩子”,他不得不在與父母的相處中言聽計從,以致在長大后為此深感悲哀。異常的親子關系,讓宮崎駿不斷在動畫作品中試圖修復。
最明顯的便是影片《借物少女艾莉緹》,主人公小翔作為宮崎駿對自身的某種投射,是一個患有心臟病、馬上就要動手術卻被寄養在鄉下姨婆家的孤獨少年。如果不是有“小小人”艾莉緹的意外出現,他大概要一輩子有氣無力地沉默在憂傷里。然而,正是這“快要滅絕的物種”讓病弱的小翔嘗到了體型上的優勢和種族上的優越感,并在成為“有用的人”的過程中獲得巨大滿足。可以說,正是處處擔驚受怕、孤立無援、無以為家的“小小人”,給了小翔“被需要”的機會與可能,從而為內心深處無處釋放的“保護欲”提供了出口。
如我們所見,在宮崎駿動畫中,父母的缺席數見不鮮,小翔的媽媽因為忙于工作,連兒子的心臟手術也不能照看;《懸崖上的金魚姬》中,少年宗介的父親常年在海上航行。
童話世界中的家庭仿佛歷來就是不完整的,父母總有這樣那樣的理由將孩子丟在一旁,小主人公們似乎注定要在精神世界里感受孤獨,進而試圖以一己之力,成為拯救危難的英雄。
當宮崎駿在影片中抱怨家庭關系的疏遠,并為此一再塑造那些善良純潔同時又有著超強決斷力與行動力的少女時,是懷著怎樣的心情看待他那不快樂的童年和反思成人后的自己的?
在《風之谷》中,娜烏西卡是英雄式的,雖然只是年少的公主,卻有著驚人的本領和號召力,她不僅有著領袖式的襟懷,而且比最年長的智者、精通預言的大婆婆更加通靈。在腐海蔓延、蟲族肆虐的家園,只有娜烏西卡知道該如何對待其他生命。在她看來,冒風險帶迷路的玉蟲回家跟忍下狐松鼠的一口撕咬以使對方感到愛與信任,同樣值得,也同樣自然。
在《哈爾的移動城堡》中,因咒語而變老的蘇菲哪怕已滿臉皺紋、直不起腰來,面對救命恩人哈爾的愛情,也從未自慚形穢。相反,較之在帽子店時的溫吞順從,蘇菲有了更強的行動力。無論是對城堡自作主張的清潔打掃,還是對宮廷魔法師莎莉曼的勇敢控訴,都體現出她內心中逐漸蘇醒的獨立意識。而正是這份對真實自我的珍視與回歸,使她重新掌握了生命的自主權,并最終讓愛情有了回饋。
《千與千尋》更是在片名上點出了一字之差的重要意義:“不要忘記自己的名字,名字一旦被奪走,就再也無法找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千尋”不是“小千”,“琥珀川”也不是“小白”。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受之于父母的名字亦如一個完整的家庭結構,是不能被隨便拆分或簡化的。盡管作為天神浴場中唯一的人類,千尋頗為透明人和動物精怪們所不齒,可千尋卻隱忍著,拼命地干活,只為救出因貪吃而變成豬的父母回家。
這樣的少女,正是宮崎駿對這世界最溫柔的獎賞,一如《紅豬》中飛行員羅森對少女菲奧說的:“我看著你,就覺得人類還有救。”
忘卻了動畫的初心
宮崎駿曾多次感嘆自己的創作之路布滿荊棘。在那個年代,上了高中還在看漫畫或者畫漫畫是一件頗為同齡人所不齒的事兒。但是,在準備高考的黑暗季節里宮崎駿始終“懷著對現實的滿腔仇恨畫著漫畫”,并且堅定地認為是“身邊這些人不明白漫畫的潛力”。
他最終考入了東京學習院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主攻日本產業論,與包括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內的皇親國戚們做了同學。即便在大學期間,他也堅持不懈地練習繪畫,并且加入了學生社團“兒童文學研究會”,直至畢業后才正式投入自己熱愛的事業。
這樣的經歷和情緒,在《側耳傾聽》中幾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作為少年宮崎駿的寫照,臨近中考卻茫然無措的月島滴滴,整日泡在圖書館“看閑書”,除了寫詩填詞沒有什么真正的作品。少年天澤圣司闖入她的生活,成為戀人后卻突然要結束學業去意大利學做小提琴——這是他的個人理想,滴滴猛然發覺自己按部就班地混日子是多么無趣。于是她給自己一個期限,看自己到底能夠在文學這條路上達到怎樣的高度。盡管“第一讀者”圣司爺爺給了她很多贊美和鼓勵,滴滴還是深切感覺到自己高估了自己,從而選擇了繼續專心學業、復習中考,讓家人放心。
在“萬物有靈”的傳統信仰下,日本人在對待大自然的態度中有著相當的平等性和不加拘束的自覺,認為自然之美在于它本來的面目,不必加任何人為的改動;宮崎駿不僅以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山川草木、風雨雷電構成自己清新、質樸、自然、靈動的畫風,更以未經世事的小孩子的夢想,重塑著人類的靈魂。
一如片中圣司爺爺對月島滴滴所期望的,不必畏縮,不必雕琢,就像那含有翡翠的原石,雖然粗糙有裂隙,卻因為未經研磨仍保持著天然的形狀。而“滴滴和圣司都是與那石頭一樣的人”,若要實現夢想,首先要找到自己內心的“原石”,讓動人的光哪怕從裂縫里也能發出來。這里面的道理,就是“自然”。它不僅指“大自然”,也是“自然而然”的“自然”。
在有序的文明社會中,生活被不斷異化,哪怕“虛空的努力也可以被無條件接受”。現代人以停不下來的快節奏,或萎靡不振或樂此不疲地讓“忙”字幾乎填滿了一切時空,忘記了本心,以致在壓力下不斷擠壓年少時的夢想,直至變成粉末。因此,宮崎駿在作品中不斷強調“初心”的重要。
可與此同時,更深的矛盾也在宮崎駿心中滋長,他曾對大眾坦言:“雖然我們認為自己的作品都是有良知的,但影像作品的的確確在刺激兒童的視覺和聽覺。我們剝奪了讓兒童走出小天地,感受整個時代的權利。”在他看來,動漫產業的日益膨脹,正是日本發展現代化的腳步過于粗暴的結果,而他自己也恰恰在這糟糕的環境下,從“邊緣”走向“流行”。
如此觀之,病了、累了恐怕并非宮崎駿多次宣布退休的真正原因,而看透世事、失去了“創作初心”,才是他決定收山的根源。
從倒影里找到回家的路
《紅豬》中的羅森,既不愿為法西斯效力,也不愿當奪人財物的飛賊,寧可將自己變成一頭豬。即便身為一頭豬,在和美國佬基斯的飛行決戰中也始終堅守著“不開槍、不殺人”的原則,只在空手肉搏中與對方廝打一番。《風之谷》中的娜烏西卡,即便面對挑起戰爭的多魯美奇亞公主庫夏娜,也能在千鈞一發之際救她的命,全然沒有敵我之分。
不難發現,宮崎駿筆下的人物并不以所謂的道德標準為行動指南,甚至也不能粗暴地以敵我善惡兩分。即便是弱勢的一方,在力求自身生存之道的過程中,也往往并不以報復為手段或目的。沒有恒定的壞人,就算是壞人也有可取之處。沒了湯婆婆,千尋就沒有工作,就會變成怪物而失去自救與救父母的機會;沒了人類,小小人的吃穿用度和所謂的家園也將不復存在。
因為家族所從事的是專門制造飛機的軍工企業,所以,經歷過二戰災難的宮崎駿從小心里就有一道深不見底的傷痕。包括他的工作室的名字“吉卜力”,都是二戰時意大利的一款偵察機,意為“撒哈拉的熱風”。但是,作為一名公開講故事的人,宮崎駿顯然并不認為對和平的渴望,是在作品中以道德評判定結局的理由,他主張“不制作打倒壞人就能得到世界和平的電影”。
他肯以企業資金為吉卜力員工的孩子們建造有山有水的托兒所,卻不愿在動畫作品中為這些孩子虛構一個“邪不壓正”“人定勝天”的完美世界。《天空之城》中,不是也以海盜們樂呵呵地展示從拉比達奪來的戰利品結尾么?如此歡快的大團圓氣氛,代替了控訴、諷刺的筆調,而這種不粉飾、不遮掩的態度,事實上正是宮崎駿做童話的可貴之處。
面對眾人對自己手繪風格的贊美——對于傳統技藝的堅持,代表了日本乃至東方的品位,與好萊塢分庭抗禮——他總是平淡地說:“我們不是競爭對手,我們之間只有友誼。”在他的觀念中,手繪并不因其傳統,就承載了高人一等的藝術道德,也不因為看似具有文藝氣質,就忽略對市場和票房的掌控。
之所以堅持手繪,只因為它是回歸內心的一種方式。說起來,宮崎駿不僅拒絕別人為自己封上的“藝術家”頭銜、給他的電影貼上“環保”標簽,更拒絕以這樣的“二分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他最欣賞的,不是陽春白雪的精英藝術,而恰恰是卓別林那種“笑中帶淚”的喜劇風格,在看似粗鄙的、雜耍般的情節中,以普通人的視角與感知,蘊藏對生命莫大的關懷。
2012年,美國《紐約客》雜志記者采訪宮崎駿時表示自己的孩子一遍遍地看他的動畫時,宮崎駿當即“大怒”:“我的片子最好一年內不要看兩遍,因為孩子們把太多時間花在電影電視上不是好事,這會讓他們忽略現實世界。”極其悲觀的宮崎駿對小觀眾們似乎有著一種敬畏式的保護與愛,他不想讓自己的悲觀厭世的情緒影響他們。他筆下那些象征人類美好情感與純潔生命的女孩子們被他投注了太多的關懷、熱情與希望。為此,他拒絕將自己的動畫片制成電腦游戲,“電腦游戲并不能給青少年以激勵,反而加深了他們的失望感。孩子們的業余時間應該盡可能用于了解他們的現實世界。”
宮崎駿還半開玩笑地說:“我希望再活30年。我想看到大海淹沒東京,日本電視廣播網的電視塔成為孤島。我想看到紐約的曼哈頓成為水下之城……我對這一切感到興奮。金錢和欲望,所有這一切會走向崩潰,綠色的雜草將會接管世界。”但相信他在“口出惡言”的同時內心卻充滿著無限的慈悲,一切都愛得不留痕跡。
童年,一段遙遠且短暫的時光,卻往往在人們的拾掇與反思中變得無孔不入、經久不息。宮崎駿因為那一段不可逆轉的童年記憶,一次次在作品中修補著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也許,宮崎駿一生只拍了一部電影,名字就是“我們的失落與純真”。
這樣的修補沒有盡頭,大師已再次宣告離退,留下孤獨的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去窺視他的內心,然后從那深邃的倒影中,去尋找到回家的路。
(摘編自《課堂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