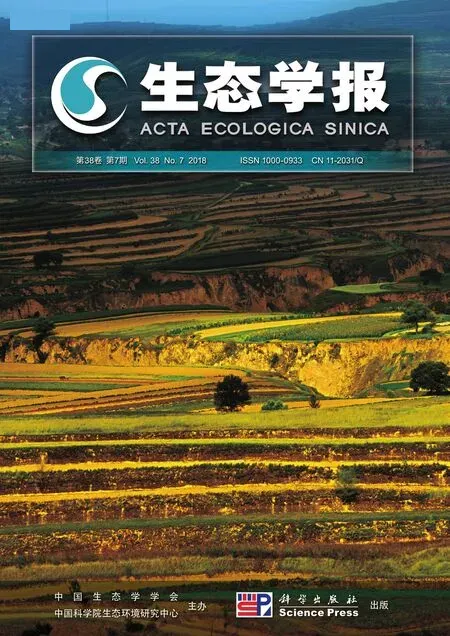西藏自然保護區現狀分析及其空間布局評估
李士成,李少偉,希娜·吉,次仁羅布,央 珍,鄧雨杰,孫 維,*
1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公共管理學院,武漢 430074 2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3 中國科學院生態系統網絡觀測與模擬重點實驗室(拉薩站),北京 100101 4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081 5 西藏自治區科技信息研究所,拉薩 850000
自然保護區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區域[1- 3],在保護珍稀特有物種資源、典型生態系統以及珍貴自然遺跡資源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4- 7]。中國目前已建立2740處自然保護區,總面積達147萬km2,已基本形成類型比較齊全、功能相對完善,布局較為合理的自然保護區體系[8]。然而當前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人類開發活動與生態保護的矛盾仍然突出[9- 10],自然保護區的建設管理還面臨嚴峻挑戰[11- 12]。如有不少自然保護區的立標勘界未完成[13],自然保護區的空間布局評估較少開展等[14]。最新研究表明,中國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與生物多樣性空間格局和生態系統服務格局匹配性不高等[3]。
西藏自治區是世界第三極的核心區[15- 16],其自然保護區的發展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17- 20]。然而,目前多數研究是針對自治區內某個或者部分自然保護區[21- 22],而將全區的自然保護區作為整體,對其空間布局的合理性進行評估的研究較少[23- 24]。而其整體布局是否合理,則直接關系到西藏自然保護區的科學管理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3, 11]。
有鑒于此,本研究以《2015年全國自然保護區名錄》為數據基礎,在分析西藏自治區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現狀的基礎上,從人文和自然兩個角度來對西藏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的合理性進行評估,以期為其空間布局優化提供科學參考。
1 研究區簡介
西藏自治區北部是昆侖山、岡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為骨架的藏北高原,往南則是以雅魯藏布江干、支流河谷為主的藏南谷地,東南側緊密排列著南北向的高山峽谷[25]。總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平均海拔從5000m以上漸次遞減至4000m左右。西藏輻射強烈,但氣溫低,年均溫為-2.8—12.0℃,降水和氣溫均由東南向西北遞減[26]。此外,西藏是中國河流數量最多的省區之一,也分布了星羅棋布的湖泊。西藏植被從東南到西北依次為森林、草甸、草原、荒漠和高山植被。西藏還是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熱點區域之一[27]。西藏人類活動主要分布在雅江中游以及自治區東部等地區,且近年來呈增強的趨勢[28]。
2 數據與方法
2.1 數據來源
西藏自然保護區數量、面積、主要保護對象、類型、級別以及始建時間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發布的《2015年全國自然保護區名錄》。《中國自然保護區區劃系統研究》及其附圖[29]提供了巴結巨柏、察隅慈巴溝、拉魯濕地、類烏齊馬鹿、芒康滇金絲猴、羌塘、色林錯、雅魯藏布大峽谷、雅魯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頸鶴和珠穆朗瑪峰共10個自然保護區的空間分布,予以直接引用。中國生態地理區劃、中國植被區劃、西藏1990年1km人口數據、1990年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1990年道路矢量數據引自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放牧強度數據引自生態10年成果[30]。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選取數量、面積、類型和空間分布等指標,采用分級統計、分類匯總和薈萃分析等方法,對西藏自治區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現狀特點進行分析。要指出的是,對于13個空間分布還不明確的自然保護區的空間分布,本研究參照《2015年全國自然保護區名錄》、《西藏自然和生態》以及相關自然保護區網站和前人研究[3,19]提供的信息進行勾繪。
接下來,將人類活動強度與自然保護區空間疊加,來探究自然保護區設立時生態保護與人類活動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基于國際上廣泛應用的評估方法[28,31],并結合西藏自治區的特點,選取人口密度、土地利用、道路、放牧強度等主導因子,依據其對環境擾動程度的不同,分別進行賦值量化,最后累加得到人類活動強度。考慮到上述數據的特點,將評估分辨率設定為1km。其概念模型如公式(1)所示。
HII(i)=popden(i)+landuse(i)+road(i)+grazden(i)
(1)
式中,HII(i)為人類活動強度;popden(i)為賦值量化后的人口密度因子;landuse(i)為賦值量化后的土地利用因子;road(i) 為賦值量化后的道路擾動因子,grazden(i) 為賦值量化后的放牧強度因子。
自然保護區建成以后,保護區內部限制甚至禁止人類活動,而未設立保護區的地方人類活動不受限制,所以當前的人類活動強度并不能用來評估保護區設立時生態保護與人類活動之間的矛盾。因此,應以自然保護區建立以前的人類活動強度來評估保護區設立時空間布局的合理性。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研究選取1990年的人類活動強度數據與自然保護區空間分布進行疊加。
最后,將自然保護區空間分布與中國生態地理區劃和中國植被區劃進行空間疊加,從自然的角度評估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的合理性。選取自然保護區在各個生態地理區和植被帶內的類型、密度和面積等指標進行評估。自然保護區密度是指每萬平方千米自然保護區的數量。要指出的是部分自然保護區跨生態地理區和植被帶,數量統計時本研究按其在各個區(帶)內的面積占比進行分配。
3 結果與分析
3.1 基本現狀特征
截至2015年底,西藏共建有自然保護區47個,其中國家級有9個,自治區級有14個,地市縣級有24個。從數量的變化看,1993—2003自然保護區數量增加比較多,其中1993年前后是西藏自然保護區數量增加最為明顯的一個時點,速度明顯要高于全國(圖1)。

圖1 西藏國家級和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數量和面積隨時間變化Fig.1 Changes of number and area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or 1985—2015
2015年底全區自然保護區面積達到41.37×104km2,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排名第一位,約占全自治區國土面積的34.47%,明顯高于全國陸域自然保護區占國土面積15%這一比例。面積的變化可以劃分為3個階段:1985—1993年西藏自然保護區面積增加速度高于全國,面積占比整體逐漸增加的階段;1993—2002年西藏自然保護區面積增加速度要緩于全國,面積占比逐步下降的階段;2002—2015年西藏自然保護區面積增加速度和全國基本持平,面積占比基本穩定的階段(圖1)。
全自治區23個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涵蓋內陸濕地、森林生態、野生動物、地質遺跡、荒漠生態和野生植物6個類型。內陸濕地型自然保護區數量最多,有10個;森林生態和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區各有4個;地質遺跡類自然保護區有3個。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類型為荒漠生態,面積最大,占整個自治區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的72.2%。就主要保護對象而言,23個自然保護區中,有12個主要保護對象是或包含濕地生態系統;有5個主要保護對象是或包含森林生態系統;有2個主要保護對象是或包含荒漠生態系統;有6個主要保護對象是或包含黑頸鶴、藏羚羊、馬鹿等珍稀野生動物;3個地質遺跡類的保護區主要保護對象為地熱噴泉群、土林、枕狀巖溶[19,31]。總體而言,西藏已建立的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面積大、類型全,其主要保護對象較全面地保護了高原脆弱生態系統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
3.2 空間分布特征
總體而言西藏自治區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在全區分布較為均勻,中部相對較多(圖2)。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自治區西南部沒有分布,省級保護區從自治區西部到東部均有分布,中部居多。
就保護區類型的空間分布而言,保護內陸濕地生態系統的自然保護區大致分布在北緯31°線附近;保護荒漠生態系統的羌塘自然保護區分布在西北部,面積較大;札達土林自然保護區分布在西部,在地質遺跡類自然保護區中面積最大;野生動物類保護區分布在自治區的中東部,以色林錯保護區面積最大;主要保護對象為森林生態的自然保護區分布在東部,以及南部的珠穆朗瑪峰自然保護區;野生植物類自然保護區巴結巨柏面積只有0.08km2,分布在藏東部(藏44)。
從空間分布的變遷來看,1990年時只有4個國家級和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其中珠穆朗瑪峰自然保護區分布在自治區南部,其余3個分布在自治區東南部。2000年時,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的數量增至14個,分布也由東南部往中西部擴展,表明保護區的分布趨于均衡,類型也更加全面。至2014年,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增至23個,新增的9個自然保護區有8個為內陸濕地型,分布在自治區中部。

圖2 西藏自然保護區空間分布圖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3.3 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評估
3.3.1 與人類活動強度的關系
自然保護區與1990年西藏人類活動強度的空間關系如圖3所示。人類活動強度變化范圍為0—43(0表示人類活動強度最小,是基于當前考慮的人類活動因子計算而得,不表示絕對沒有人類活動,43表示人類活動強度最大),全區的人類活動強度平均為2.69。從圖3可以看到,自治區西部的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強度較小,如羌塘自然保護區和札達土林自然保護區幾乎沒有人類活動。中東部的部分自然保護區內部存在人類活動強度較大的區域,如雅魯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頸鶴、拉魯濕地、日喀則群讓等自然保護區直接分布在西藏自治區社會經濟的中心“一江兩河(雅魯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拉薩河和年楚河)”地區。西藏所有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的人類活動強度為1.39,約為整個自治區2.69的一半。隨著人類活動強度的增加,對應自然保護區的面積在逐漸減少(圖3)。人類活動強度為0的自然保護區面積約為16.36×104km2;人類活動強度增至3時,對應保護區面積下降為0.94×104km2。人類活動強度大于3的所有保護區面積為3.32×104km2,只占保護區總面積的7.84%。

圖3 西藏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空間分布與人類活動強度的關系Fig.3 Spatial pattern of nature reserve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influence intensity
上述結果表明西藏自然保護區設立時其內部人類活動強度整體較小。因此,雖然自治區保護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1/3以上,但保護的過程并沒有大量的人類開發活動需要遷出保護區;而且也不會因為對保護區內人類活動的限制,而明顯影響西藏的經濟發展。表明西藏自然保護區的空間分布與人類活動的矛盾不突出,空間布局總體合理。在23個保護區中,有11個保護區的人類活動強度小于西藏全區平均值,剩下12個大于全區平均值(表1)。表明西藏自治區部分自然保護區的分布與人類活動是存在矛盾的,還需要對其布局進行優化。

表1 西藏23個國家級和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1990年的人類活動強度平均值
3.3.2 與生態地理區的空間關系
西藏自治區8個生態地理區內均有自然保護區的分布(圖4a)。就各個生態地理區內自然保護區類型來看,羌塘高原湖盆等3個生態地理區內保護區類型有4類(生態地理區名稱可參見表2),阿里山地等2個生態地理區內保護區類型有2類,昆侖高山高原等3個生態地理區內保護區類型有1類。總體而言,每個生態地理區內自然保護區的類型和主要保護對象存在較好的區內獨立性和區間互補性(表2)。

圖4 各生態地理區和植被帶內西藏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分布Fig.4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n each eco-geographic and vegetation zone
Table2Theamount,area,anddensityofnationalandprovincialnaturereservesoftheTibetAutonomousRegionineacheco-geographicregion

生態地理區(代碼)Eco-geographicregion(Code)類型Typesofnaturereserve自然保護區面積占生態地理區面積的比例/%Proportionoftheareaofthenaturereservetothatoftheeco-geographicregion自然保護區密度/(個/萬km2)Densitiesofnaturereserve昆侖高山高原(HⅠD1)Kunlunalpineplateau(HⅠD1)荒漠生態95.560.03阿里山地(HⅡD3)Alimountain(HⅡD3)地質遺跡,內陸濕地9.640.32青南高原寬谷(HⅠC1)SouthQinghaiPlateauValley(HⅠC1)荒漠生態28.500.01羌塘高原湖盆(HⅠC2)Qiangtangplateaulakebasin(HⅠC2)地質遺跡,荒漠生態,內陸濕地,野生動物48.610.14果洛那曲丘狀高原(HⅠB1)Guoluo-Nagquhillyplateau(HⅠB1)內陸濕地,野生動物6.270.17川西藏東高山深谷(HⅡA/B1)WestSichuanandeastTibethighmountainsanddeepvalleys(HⅡA/B1)內陸濕地,森林生態,野生動物,野生植物17.150.30東喜馬拉雅南翼(ⅤA6)SouthsideofeastHimalayan(ⅤA6)森林生態6.480.16藏南山地(HⅡC2)SouthTibetmountains(HⅡC2)內陸濕地,森林生態,野生動物,地質遺跡12.890.28
各個生態地理區內自然保護區面積占比差異較大(表2),昆侖高山高原區里自然保護區面積占比達到了95.56%,而果洛那曲丘狀高原區內保護區面積占比只有6.27%,面積占比的方差達到913.93。考慮到各個生態地理區面積不同,本研究進一步計算了各個生態地理區的自然保護區密度(表2)。密度最大的生態地理區是阿里山地,為0.32。川西藏東高山深谷和藏南山地緊隨其后,分別為0.30和0.28。青南高原寬谷的自然保護區密度最小,是0.01。各個生態地理區內自然保護區密度的方差為0.02,表明各個生態地理區內保護區密度整體較為接近。
3.3.3 與植被帶的空間關系
西藏自治區8個植被帶內全部有自然保護區分布(圖4b)。就各個植被帶內自然保護區的類型而言(表3),同生態地理區類似,每個植被帶內自然保護區的類型和主要保護對象,亦存在較好的帶內獨立性和帶間互補性。
各個植被帶內自然保護區面積占比差異較大,高寒荒漠地帶保護區面積占比為93.18%(植被帶名稱可參見表3),為最高值;高寒灌叢/草甸地帶保護區面積占比只有2.16%。保護區面積占比的方差達977.05。本文進一步計算了各個植被帶內自然保護區的密度。溫性荒漠地帶自然保護區密度最高,為0.32;其次是亞熱帶山地寒溫性針葉林地帶,為0.3。自然保護區分布密度最小的是高寒荒漠地帶,只有0.03。各個植被帶自然保護區密度的方差為0.01,可以看到,各個植被帶內保護區密度較為接近。
表3各植被帶內西藏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數量、面積和密度
Table3Theamount,area,anddensityofnationalandprovincialnaturereservesoftheTibetAutonomousRegionineachvegetationzone

植被帶(代碼)Vegetationzone(Code)類型Typesofnaturereserve自然保護區面積占植被帶面積的比例/%Proportionoftheareaofthenaturereservetothatofthevegetationzone自然保護區密度/(個/萬km2)Densitiesofnaturereserve高寒草原地帶(ⅧBi)Alpinegrasslandzone(ⅧBi)地質遺跡,荒漠生態,內陸濕地,野生動物54.420.14高寒灌叢/草甸地帶(ⅧAi)Alpineshrubs/meadowszone(ⅧAi)內陸濕地2.160.23高寒草甸地帶(ⅧAii)Alpinemeadowzone(ⅧAii)內陸濕地,野生動物8.130.05亞熱帶山地寒溫性針葉林地帶(ⅣBiii)Subtropicalmountainoustemperateconiferousforestzone(ⅣBiii)內陸濕地,森林生態,野生動物,野生植物16.130.30高寒荒漠地帶(ⅧCi)Alpinedesertzone(ⅧCi)荒漠生態93.180.03溫性荒漠地帶(ⅧCii)Warmdesertzone(ⅧCii)地質遺跡,荒漠生態,內陸濕地14.460.32溫性草原地帶(ⅧBii)Warmgrasslandzone(ⅧBii)地質遺跡,內陸濕地,森林生態,野生動物10.420.25北熱帶季節雨林、半常綠季雨林(ⅤBi)Northerntropicalseasonalrainforest,semi-evergreenmonsoonrainforest(ⅤBi)森林生態13.360.19
各個生態地理區或植被帶內自然保護區的類型存在較好的區(帶)內獨立性和區(帶)間互補性,各個區(帶)內自然保護區的密度較為接近,表明從類型和數量的角度來看,當前自然保護區的布局基本均衡合理。但保護區面積占比在各個區(帶)差異較大,對于保護區面積占比很小的區(帶)而言,則有可能其保護對象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4 討論
對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進行合理性評估,是優化自然保護區網絡、規劃國家公園體系、保障國家與區域生態安全的科學基礎。本研究在對西藏自然保護區現狀特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從人文和自然兩個角度對西藏自然保護區的空間布局進行了評估。與前人相比,本研究的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思考:①從全局的角度對自然保護區進行分析和評估,研究結果可以用于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的優化,甚至國際保護地體系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保護地體系的完善;②從“保護”與“發展(人類活動強度)”這一對矛盾的角度對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合理性進行評估,有助于明確哪些保護區的空間分布需要調整,哪些保護區的保護措施需要進一步加強等。此外,本研究繪制了部分空間分布不明確的國家級和自治區級保護區分布圖,可用于保護區功能區劃[32]和保護成效評估等研究。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如部分保護區的空間分布信息較少,只能進行大致勾畫,其合理性還有待實地驗證。此外,由于數據的缺失,人類活動強度評估當前只考慮了4個因子,實際上對生態環境帶來擾動的因子很多,如污染、旅游、水電站、采礦等,在接下來的研究中需要收集更多數據獲得更完善的人類活動強度。還有就是地市縣級自然保護區的分布范圍,以及對于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和管理具有重要意義的功能區劃與制圖等[32],本研究亦未進行討論。在以后的研究中,應繼續強化自然保護區的基礎研究工作,明確自然保護區及其功能區范圍等[8, 14]。還可以采用其他指標,如生態系統服務等保護目標來評估自然保護區空間布局的合理性等[3]。
5 結論
(1)截至2015年底,西藏共建有自然保護區47個,面積達41.37×104km2。內陸濕地型自然保護區數量最多。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共23個,全面地保護了西藏脆弱生態系統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
(2)西藏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在全區分布較為均勻,中部相對較多。1990—2015年,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由西藏東南部往中西部擴展,分布及類型逐步趨于均衡合理。
(3)西藏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的平均人類活動強度為1.39,約是整個自治區2.69的一半,與人類活動空間分布的矛盾不突出;部分自然保護區內部人類活動強度較大,還需進一步緩解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優化布局。
(4)從自然角度看,每個生態地理區和植被帶內自然保護區類型存在較好的內部獨立性和外部互補性,各個區(帶)內自然保護區密度較接近,但各個區(帶)內自然保護區面積占比差異較大,空間布局還需優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Soutullo A. Extent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2): 362- 363.
[2] Jenkins C N, Joppa L.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9, 142(10): 2166- 2174.
[3] Xu W H, Xiao Y, Zhang J J, Yang W, Zhang L, Hull V, Wang Z, Zheng H, Liu J G, Polasky S, Jiang L, Xiao Y, Shi X W, Rao E M, Lu F, Wang X K, Daily G C, Ouyang Z Y. Strengthening protected areas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114(7): 1601- 1606.
[4] Chen Y H, Zhang J, Jiang J P, Nielsen S E, He F L.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rotected areas to conserve current and future amphibian diversity. Diversity & Distributions, 2017, 23(2): 146- 157.
[5] Geldmann J, Barnes M, Coad L, Craigie I D, Hockings M, Burgess N D. Effectiveness of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in reducing habitat loss and population decline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3, 161: 230- 238.
[6] Ervin J. Rapid assessment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four countries. Bioscience, 2003, 53(9): 833- 841.
[7] de Almeida L T, Olímpio J L S, Pantalena A F, de Almeida B S, de Oliveira Soares M. Evaluating ten years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a mangrove protected area.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6, 125: 29- 37.
[8] 陳吉寧. 關于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 (2016-07-01) [2016-08- 25]. http://www.cecrpa.org.cn/sxyw/zx/8649.htm.
[9] Faith D P, Walker P A. Integrating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effective trade-offs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cost in the selection of protected areas. 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1996, 5(4): 431- 446.
[10] Twyman C.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livelihoods in Botswana′s wildlife management areas. Applied Geography, 2001, 21(1): 45- 68.
[11] Li J S, Wang W, Axmacher J C, Zhang Y Y, Zhu Y P. Streamlining China′s protected areas. Science, 2016, 351(6278): 1160- 1160.
[12] 夏欣, 王智, 徐網谷, 張昊楠, 周大慶, 蔣明康. 中國自然保護區管理機構建設面臨的問題與對策探討. 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 2016, 32(1): 30- 34.
[13] 徐網谷, 王智, 錢者東, 張昊楠, 范魯寧, 蔣明康. 我國自然保護區范圍界定和有效保護面積現狀研究. 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 2015, 31(6): 791- 795.
[14] 陳雅涵, 唐志堯, 方精云. 中國自然保護區分布現狀及合理布局的探討. 生物多樣性, 2009, 17(6): 664- 674.
[15] Qiu J. The third pole. Nature, 2008, 454(7203): 393- 396.
[16] Yao T D, Thompson L G, Mosbrugger V, Zhang F, Ma Y M, Luo T X, Xu B Q, Yang X X, Joswiak D R, Wang W C, Joswiak M E, Devkota L P, Tayal S, Jilani R, Fayziev R. Third pole environment (TP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2012, 3: 52- 64.
[17] Wu R D, Zhang S, Yu D W, Zhao P, Li X H, Wang L Z, Yu Q, Ma J, Chen A, Long Y C.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nature reserves in representing ecological diversity.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1, 9(7): 383- 389.
[18] 張鐿鋰, 吳雪, 祁威, 李士成, 擺萬奇. 青藏高原自然保護區特征與保護成效簡析. 資源科學, 2015, 37(7): 1455- 1464.
[19] 劉務林. 西藏自然和生態.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7.
[20] Zhang Y L, Hu Z J, Qi W, Wu X, Bai W Q, Li L H, Ding M J, Liu L S, Wang Z F, Zheng D. Assessment of effectiveness of nature reserv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net primary production and the large sample comparison method.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 26(1): 27- 44.
[21] Weckerle C S, Yang Y P, Huber F K, Li Q H. People, money, and protected areas: the collection of the caterpillar mushroomOphiocordycepssinensisin theBaimaXueshannature reserve, Southwest China. 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2010, 19(9): 2685- 2698.
[22] 王斌, 彭波涌, 李晶晶, 普窮, 胡慧建, 馬建章. 西藏珠穆朗瑪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鳥類群落結構與多樣性. 生態學報, 2013, 33(10): 3056- 3064.
[23] Wang L Y, Chen A Z, Gao Z F. An exploration into a diversified world of national park systems: China′s prospects within a global context.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1, 21(5): 882- 896.
[24] 曲格平. 中國自然保護綱要.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1987.
[25] 孫鴻烈, 鄭度. 青藏高原形成演化與發展. 廣州: 廣東科技出版社, 1998.
[26] 張榮祖, 鄭度, 楊勤業. 西藏自然地理.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82.
[27] Myers N, Mittermeier R A, Mittermeier C G, da Fonseca G A B, Kent J. Biodiversity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Nature, 2000, 403(6772): 853- 858.
[28] Venter O, Sanderson E W, Magrach A, Allan J R, Beher J, Jones K R, Possingham H P, Laurance W F, Wood P, Fekete B M, Levy M A, Watson J E M. Sixteen years of change in the global terrestrial human footprint and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7: 12558.
[29] 張榮祖, 李炳元, 張豪禧, 劉林山. 中國自然保護區區劃系統研究.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12.
[30] Ouyang Z Y, Zheng H, Xiao Y, Polasky S, Liu J G, Xu W H, Wang Q, Zhang L, Xiao Y, Rao E M, Jiang L, Lu F, Wang X K, Yang G B, Gong S H, Wu B F, Zeng Y, Yang W, Daily G C. Improvements in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investments in natural capital. Science, 2016, 352(6292): 1455- 1459.
[31] Sanderson E W, Jaiteh M, Levy M A, Redford K H, Wannebo A V, Woolmer G. The human footprint and the last of the wild. Bioscience, 2002, 52(10): 891- 904.
[32] 呼延佼奇, 肖靜, 于博威, 徐衛華. 我國自然保護區功能分區研究進展. 生態學報, 2014, 34(22): 6391- 6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