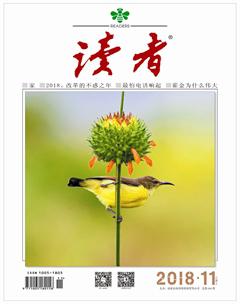最怕電話響起
小綠桑
我以31歲的“高齡”去學(xué)了駕駛。此前之所以拖著不學(xué),是覺得沒有必要開車,北京的交通狀況糟糕,日常出行靠打車、公共交通均可解決,何況家里還有父親這個老司機。
直到去年年底,父親患了眼疾,看東西有重影,我?guī)诒本┧奶幥筢t(yī)問藥,奔赴各大醫(yī)院。有一家醫(yī)院和我家在地理位置上成大對角線,我?guī)麚Q乘了兩次地鐵,歷經(jīng)一個半小時,終于抵達。路上,他跟我說:“你去學(xué)個本吧,我的眼睛怕是不能碰車了。”
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得去學(xué)開車了。
父親退休以后,身體出現(xiàn)諸多不適,是年輕時辛苦工作落下的病根。很長一段時間,為了供我深造,他的工作三班更替,作息日夜顛倒。不規(guī)律的生活、不健康的習(xí)慣所埋下的伏筆都在退休后日益顯現(xiàn)。3年前,他做了一次腦部手術(shù),手術(shù)結(jié)束,我跟母親擁上前去幫忙推病床,醫(yī)生問:“家里沒有男人嗎?”
麻藥勁還沒完全消退的父親說:“嗨,家里唯一的男人在這兒躺著呢。”
這次父親生病,也是突如其來。一天散步回來,他發(fā)現(xiàn)看東西有重影,以為是沒休息好。第二天依然如此,只得去附近的醫(yī)院就診。一去就被留在了醫(yī)院里,眼科醫(yī)生說不出究竟,轉(zhuǎn)掛神經(jīng)內(nèi)科,神經(jīng)內(nèi)科醫(yī)生懷疑是血管瘤壓迫視神經(jīng),需要留院觀察。
清晨,我送他去辦住院手續(xù)。醫(yī)生在開會,護士在聊天,我們在走廊里站了一個多小時,沒人搭理。最后我從別的病房借了一把椅子給他,自己在走廊里走來走去,看到各種痛苦。
醫(yī)院一住就是十幾天,診斷不出病因,就把所有檢查做了一遍。每次父親去做檢查,我都焦慮萬分,生怕檢查出什么不好的結(jié)果。他抽煙喝酒,又有高血壓史,血糖偏高,脾氣暴躁,還拒絕體檢,什么都有可能發(fā)生。
那段日子,我害怕電話上閃爍父親的名字,怕他打電話來,說檢查結(jié)果出了問題。
終于在最后一項檢查結(jié)束后,電話響起。父親在電話里說,加強核磁的結(jié)果是懷疑眼睛里長了東西,讓轉(zhuǎn)到知名眼科醫(yī)院繼續(xù)檢查。
2018年伊始,我?guī)几氨本└鞔笱劭崎T診,幫他制定了就醫(yī)攻略,逢人就打聽醫(yī)療資源,每天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到點就開始搶號,幸運地掛到了幾個專家號。父親抱怨住院時年輕的主治醫(yī)生待他不好,于是每次就診前,我把“好大夫”網(wǎng)站上關(guān)于醫(yī)生的評價一條一條看過,提前了解醫(yī)生的脾氣。
我工作時間自由,能隨時陪伴父親,算是優(yōu)勢。可我缺乏就醫(yī)經(jīng)驗,又不會開車,走在路上又要擔(dān)心他摔倒。他總是這樣跟醫(yī)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我現(xiàn)在不敢過馬路,那些車在我面前晃來晃去,明明就兩輛車,在我眼前成了一排車。”我“腦補”了一下這個畫面,拉緊他的胳膊,像牽著個孩子。
排隊、取號、候診、就診、刷卡、拿藥、報銷,我逐漸熟悉了就醫(yī)流程,學(xué)會了跟加塞的人理論。在等待的過程中,我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看掛在墻上的醫(yī)生履歷,聽其他病人是否有類似的疾病,了解對醫(yī)生的反饋和最新的治療手段。
經(jīng)過漫長的叫號等待,我陪父親進去,書包里偷偷準(zhǔn)備好了錄音筆,是怕醫(yī)生說得太快,想著錄下來多聽幾遍可以上網(wǎng)搜索。父親總是以一段冗長、無關(guān)緊要的描述來介紹病情,沒說幾句就被醫(yī)生打斷:“你到底怎么看不見?”后來我干脆把他的病情和疑問打印在紙上,代為陳述。
醫(yī)院A給出的建議是立刻打激素,也說了激素的副作用:發(fā)胖、骨質(zhì)疏松,導(dǎo)致青光眼。父親跟我都猶豫了,說回去考慮一下。第二天去了醫(yī)院B,先找了副主任醫(yī)師,又花300元掛了特需。輪上第一個看病,大夫和藹可親,指出手術(shù)切除的可能,并坦承建議我們換家醫(yī)院,治這病并非他們的強項。過幾日返回醫(yī)院A,換了一位醫(yī)生,給出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建議我們?nèi)メt(yī)院F查視神經(jīng)。
又過幾日,我?guī)Ц赣H去了全國眼科最好的醫(yī)院C,掛了專家號,第一次就診安排了各種檢查。醫(yī)生懷疑是甲亢眼病,我們遞上甲亢化驗單,說指標(biāo)一切正常。醫(yī)生說有些人甲亢指標(biāo)是看不出來的,開了一些藥物讓回家服用,又做了個加強掃描,讓隔周再來復(fù)查。第二次就診,醫(yī)生看了看說,你的情況已經(jīng)穩(wěn)定了,應(yīng)該沒有好轉(zhuǎn)的可能,也沒再治療的必要。隨后開了幾瓶眼藥水,讓我們回去滴。一路上父親悶悶不樂,像被宣判了死刑。我安慰他說沒關(guān)系,還有醫(yī)院D。我揮揮手機,又搶到了專家號。
到了醫(yī)院D,專家否定了之前的診斷,說是由高血壓和血糖引起的視神經(jīng)病變,加上年紀大了,腦子里本來就有些血管堵塞,影響眼球正常轉(zhuǎn)動。專家開了些營養(yǎng)神經(jīng)的藥物,讓他回家調(diào)理,也可以以針灸作為輔助治療。這結(jié)論終于讓父親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不開刀,不打激素,還有治愈的可能。
回家服藥許久卻未見好轉(zhuǎn),聽人介紹去了E醫(yī)院眼科,就診的多是被其他醫(yī)院宣判無法治愈的患者。醫(yī)生要求他輸液營養(yǎng)神經(jīng),再針灸刺激。為避免路途奔波,也不想再給家人添麻煩,父親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住院。他在醫(yī)院住了二十幾天,以免療程中斷,除夕傍晚趕回來吃了年夜飯,初一清早又去治療。闔家歡樂的日子,父親在醫(yī)院度過。好在這二十幾天的治療有了效果,他的眼球漸漸可以轉(zhuǎn)動,看東西重影的問題也大有改善,便準(zhǔn)備出院。
我很高興生活又步入了軌道,可以繼續(xù)在家里讀書寫字,過閑散的生活。可好景不長,一天,母親遲遲沒有回來,我打電話過去,她支支吾吾,說在醫(yī)院,應(yīng)付著掛斷電話。我聽出她的慌張,掛上電話以后,心里也跟著一陣發(fā)慌,提前結(jié)束工作返家。
等我到家,發(fā)現(xiàn)她又出門了。我打電話給還在醫(yī)院的父親,才知道母親節(jié)前在社區(qū)醫(yī)院做癌癥篩查,有腫瘤標(biāo)志物指數(shù)偏高,社區(qū)醫(yī)生建議她去大醫(yī)院復(fù)查。今天去父親所在的醫(yī)院復(fù)查,片子顯示肺部有條狀陰影,又照了CT,過幾天才能出結(jié)果。接診醫(yī)生支支吾吾,說像是有問題。
肺部、陰影、腫瘤標(biāo)志物,這三者交織到一起時,像天空中劃過一道閃電。
母親不在家,她去了附近最好的醫(yī)院。她想加號被拒絕,回家后開始手足無措,翻出這些年的所有病歷。她不在家的幾個小時,我害怕聽見任何響動,在網(wǎng)上輸入關(guān)鍵詞:肺、陰影、腫瘤,結(jié)果觸目驚心。
晚上,我怕她胡思亂想,帶她看了一場電影。電影結(jié)束后,我請她去吃深夜食堂,一碗濃香的拉面,但她根本吃不下幾口。
我表面鎮(zhèn)靜,內(nèi)心慌張,設(shè)想了無數(shù)種可能,祈禱著不要出現(xiàn)什么問題。我愿意用自己的一切交換母親的健康。
等結(jié)果出來的那兩日,我度日如年。我翻出平日收集的彩妝、香水,開始想著賣了它們給母親看病。
母親成宿地睡不著,半夜兩點臥室的燈還亮著,她拼命回憶跟這個病有關(guān)的一切。清晨,她興奮地告訴我,記起年輕時肺部有過雜音,吃了一年多的藥。這段回憶給她帶來了莫大的安慰,中午她還多吃了幾口飯。
取化驗結(jié)果的那天,我去上班,整個人卻是提心吊膽,等著她的電話,心里做了各種打算。
終于,在電話里,她松了半口氣,說診斷結(jié)果寫著疑似陳舊性病變,建議繼續(xù)觀察。
我依然無法放松,指出腫瘤標(biāo)志物偏高的問題,是否會導(dǎo)向那個讓人害怕的字眼?
母親又去大醫(yī)院重新查血。拿到化驗報告的那天,她的手是顫抖的,根本不敢看,還是父親告訴她指標(biāo)正常。她一瘸一拐舉著兩張化驗報告和片子去問醫(yī)生,醫(yī)生說社區(qū)醫(yī)院的化驗結(jié)果可能存在偏差,結(jié)合片子,證明是一場烏龍。
至此,他們才松了一口氣。
可我的那口氣始終還在,我知道,這并不是結(jié)束。隨著父母年紀的增大,問題只會越來越多,一道道坎在等著我邁。
平心而論,我的境遇要好過多數(shù)同齡人。我生長在北京,住家里的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相互照應(yīng),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且時間相對自由,還沒有經(jīng)濟壓力。父母也各自退休,有退休金和醫(yī)療保險。他們年輕時吵鬧,在老了以后變成相互陪伴。
在這樣看似美好的家庭生活里,父母隨著年齡衰老而不斷出現(xiàn)的各種疾病,是埋伏著的一顆顆炸彈。一旦爆炸,美好就將燒成灰燼。
再往前幾年,父母也分別做過手術(shù),那時我還在讀書,不懂人間疾苦,他們也可以互相照顧。一次父親失聲,是母親陪他跑遍了北京各大醫(yī)院的耳鼻喉科,沒人向我描述過就醫(yī)的艱難。
這幾年,父母的健康狀況都開始變差,每天需要服用各種藥物。尤其是母親,膝蓋積液,腰椎間盤突出,在莆田系醫(yī)院做了一次失敗的手術(shù),現(xiàn)在連續(xù)走路不能超過半個小時。我?guī)ヂ糜蔚某兄Z,根本無法兌現(xiàn)。
陪伴他們看病、治療的任務(wù)落在我的身上。我能有時間陪伴,已是幸運,在醫(yī)院里,很難看到像我這樣每天都出現(xiàn)的子女。
有一次父親住院,隔壁床是一個80歲的老人,陪伴他的是妻子和護工,他們沒有子女。到了晚上,護工睡得死,老人難受卻叫不醒他,是父親陪他折騰了一整晚。第二天,老人不停感謝著我父親,說著說著竟流下了眼淚。那是第一次,我開始考慮,如果沒有子女,將來自己的晚年會怎么度過?
從父母身體頻繁出現(xiàn)狀況開始,我的生活漸漸變得不安。每當(dāng)父母沒有按時回家,或是買菜回來遲了,我就開始焦慮是不是路上出現(xiàn)什么問題。母親不靈便的腿腳,父親升高的血壓,都會導(dǎo)致危險。
我的耳朵異常靈敏,能分辨父母的腳步聲,這腳步聲讓我踏實。我盼望他們快點回來,只要能回來,就代表著平安。
我有時會偷看父母的手機,偷聽他們講話。他們出現(xiàn)病痛,第一個告訴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彼此,或是朋友。
這些年,被當(dāng)作孩子保護的我開始經(jīng)歷死亡。我強迫自己目睹死亡的整個過程,一個人從活生生,到在死亡線上掙扎,再到被帶走,化成灰燼。我在微博關(guān)注了一個賬號,里面發(fā)布各種對逝者的哀思,讀著讀著淚就在眼眶里打轉(zhuǎn)。我追看各種醫(yī)療劇,從急診、外科,再到殯葬。通過強化觀看,鍛煉心理承受能力。因為終有一天,這些事情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
我不再喜歡出遠門。年少時出去讀書,父親生病時,恨自己沒有陪在他身邊。
我不再有野心,選擇了最穩(wěn)定的生活狀態(tài),不想讓父母為我操心。
我變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朋友總是勸我快點獨立,搬出去住,獲得自由。他們不知這念頭在我腦海里已經(jīng)漸漸逝去,我想的是,在盡可能多的時間里陪伴父母,以后才不會后悔。在我心里,親情比自由更加重要。
可即便在時間、距離、金錢都不成問題的情況下,我依然覺得害怕。父母的衰老是不可逆的。我,一個獨生子女,該如何面對不斷變老的他們?
曾裝作不經(jīng)意地問母親,她老了以后怎么辦。她斬釘截鐵地說:“不用你管,你管好自己就行。”
可真的不用我管嗎?他們還停留在清晨四點去醫(yī)院排隊掛號的階段,不會使用網(wǎng)絡(luò)繳費,迷信養(yǎng)生謠言,還沒徹底改掉吃剩飯的習(xí)慣,更別提享受生活。
那天我看到《LENS》雜志制作的專題《最怕電話響起,是父母生病的消息》,作者就父母的養(yǎng)老問題采訪了幾位獨生子女,發(fā)現(xiàn)大家有著類似的困擾,他們大多還面臨跟父母分居異地,結(jié)婚后需要照顧四位老人的情況。雖然這對我暫不成問題,可我的焦慮一點沒有減輕,因為我眼睜睜地目睹著他們變老。
就像采訪里說的,我們的精神世界很豐富,可是父母的心里只有孩子。
我和父母,變成彼此在世界上唯一的支撐。
此刻,父母正在客廳看電視,不知什么畫面讓他們發(fā)出笑聲,可以肯定,那種節(jié)目的畫面通常是我不屑一顧的。節(jié)目結(jié)束后,父親要幫母親按摩雙腿,再各自刷一會手機睡覺,響起讓我踏實的鼾聲。
我是多么希望時光能定格在此刻,那個可怕的電話鈴聲,永遠都不要響起。
但我知道,這愿望多半不會實現(xiàn),該來的總會來。好在我快要拿到駕照了。
(彭慧慧摘自騰訊《大家》欄目,沈 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