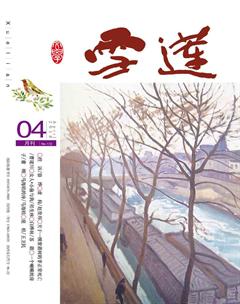短歌行(組詩)

晨 煉
最早的練習是沿黑暗的路徑行走
在古老的西山 天光黯淡
形形色色的人在輪番上路
急促的呼息聲此起彼伏
星辰幽明
戲樓新建的寬闊地上
一個七歲的男孩在玩他的腿
一個女孩子的倒立引來朦朧的圍觀
一個六十歲的男人
已停下了奔跑和跳躍
開始倒退著走路
從終點回到起點
最早上山的人就是最早下山的人
在山下 只有最后起床的人
才打開了門和窗子
屋子里彌漫出一夜長談
和前一世的習氣
在下山如潮的人流中
這個短襟打扮的人
仗風而行 溯流而上
最后的練習是沿五彩的懸崖奔走
從早晨走向中午
誰打開了清晨
放出了清新的空氣
誰擦亮湛藍的天空
放出了青草和鳥鳴
此刻,近處的云嶺雪一樣潔白
遠處的馬銜山,一千年來
只是幾片云的故鄉
山下行走的那人
像一束光一樣匆忙
不寂寞也不孤單
他要從早晨一直走向中午
黃昏還遠
他的黑夜遠沒有到來
大風之夜
大風翻飛的今夜
什么在不停的追逐
一個人糊涂在天地間
一個人糊涂在十億人的腳步中
聽到生命在漸離漸遠時傳來
輕輕的回音
大風使我想起了隱匿的祖先
想起了我們的前生
想起了曠古持久的道路
每年的風中都走過耕田的隊伍
無雨的清明故鄉遙遠
春荒卻使麥粒無處落種
今夜,春風就這樣穿過
千秋青史,班駁文案
咬文嚼字的人只在一頁紙上
看到萬眾的生命隨風播種
而自己只是一粒
無法下播的麥種
書本中的生活
讓我們遠離繁華的塵世
遠離窗外碌碌無為的奮斗
停在書本中,像一枚潔白的書簽
讓我們把短暫而珍貴的時日守住
不讓風翻走。文字啊!
這上帝的蜘蛛……
讓它到人心上結網
讓它像墨雨一樣散落那些秋天的木葉
散落花朵一樣無告無望的鐘聲
散落日暮窮途中的山路和雪
散落一個時代的繁華的舊夢
讓那些偉大的城邦和他的人民
把古人的思想不只掛在嘴巴上
還要在紊亂的燈火里
用書本把黯淡的生活點成快樂
拾穗者
這些暫時還沒有歸倉的顆粒
仍在秋風吹拂的大地上
聲勢浩大的收獲已經過去
那些曾把臉映在麥芒邊的人
是一群被命運壓彎了腰的人
此刻早在陰涼處休息或交談
主人要了卻的心愿
得靠幾個拾穗者的謹慎前行
在我知道的時光中
他們從這個秋天走到那一個秋天
一個秋天也不原漏掉
但只能
從蒼茫大地上
收藏一束束冷卻的火焰
麥桿畫
早晨它們還是生長的莊稼
晚上已被割下,曬干
讓柔麗的生命在轉瞬間感受荒涼
沉默的是大多數
它們將在家畜中得到永生
成為地上的糞,風中的土
只有少數被挽留下來
去珍惜自己的骨頭
去可憐同類的塵土
想著日后全新的生活
將被硫磺熏蒸
將被烙鐵燒著①
身體疲憊如煙熏的皮袋
回憶麥地里曾經的吹唱
追想到春天時它們已哭了
當麥桿們在痛苦的涅槃中達到永生時
有人在黃土的墻上聽到了這殘缺的聲音
有人已借此贏得了美學史上幾平方尺的土地
注釋:①麥桿畫是用當地的麥桿曬干后,用硫磺熏蒸,烙鐵烙燒等多種工序而成。
愛石說
起初所愛的是古劍
愛它的鋒芒不露銹跡斑斑
后來所愛的是陶罐
愛它的樸實自然沉默不言
現在所愛的是石硯
愛它的漆黑如夜寂靜如禪
之后我將愛石上的落日
愛它的輝煌和大氣
愛石上的曠野和大樹
愛它的落葉和塵土
愛那些卑微得近乎無用的東西
愛那年走在赤壁上的人
懷念古人也懷念自己
南山下荷鋤的人
賞花也賞人
古硯旁奮筆的人
磨墨也磨沮喪的人生
于是愛上了養鶴的人,種草的人
煉氣的人,打坐的人
愛上了鶴鳴九皋,花開四照
愛上了百無一用大雅絕論
愛上了他們與時代脫節的生活
(在夕陽的殘照中郁郁寡歡
他們都被人流擠到路的一邊)
我愛他們慧明而絕望的眼神
如同春天的曹植愛著仙子
秋天的老杜懷念著李白
他們中年齡最大的
也只是我的師兄
現在,我就要拍拍他們的肩膀
說出我的些許癡愛
散客說詩
像明朝的中期之后,時代正經歷一個精力旺盛后的怠倦。嶄新的事物在崛起,在慢慢長大,但舊的事物在衰退中還沒有崩潰。經濟在主導一切,包括社會生活和文化藝術,如果現在反用前兩年那句流行的俗語會更有意思:那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中,膚淺的繁華給膚淺的文化提供了生存的可能。這其實也是棄詩的時代,許多東西流行得太快,消亡得過早,其中包括詩歌。說詩歌其實是在說思想,說人。目前,至少有兩類人正在成為詩歌發展的障礙:第一類人是語言精致而思想平庸,缺乏人格力量的寫作者,他們是近年來平庸詩歌居高不下的原因;第二類是具有詩人氣質而缺乏語言力量,他們理應成為一個好詩人,但狂放的天性使他們讀書甚少,根底薄弱,他們耗費一生也可能燒不出幾顆詩歌的舍利子。所以,前一類人的作品太像詩,精致過頭而傷于小氣,技術含量過高而人格魅力過少,這樣的詩歌適合于南方,那些書院小才人小市民常為此類作品而揚揚得意;后一類人的作品太不像詩,廢話連篇而累于抒情,語言功底太差而無大意境,這類詩常見于北地,是偏僻地方缺乏詩歌訓練和交流的作品。所以前一類詩容易騙編輯而不能騙熟悉他的朋友,后一類詩容易騙自己而不能騙真正懂詩的人。但這兩類作品常常見于報刊,原因大概只有一條,這就是那些不以詩為重的編輯已成了這些寫作者的朋友。
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這里,我用手寫下的漢字不計其數,但最多的是報告,是通知,是用別人的姓名替代我勞動成果的東西。但在業余時間我還會寫下:蒼涼的命運之書,寫下在隴中的天堂里,我和我的朋友用夢幻播種的貧窮。這個時候我出手極快,因為這是我生命中真正擁有的東西。于是我可以讀詩自誤,擁書自重,朋友遍布隴中,自詡是深知詩家三昧的一方人物。但目前我還不敢說,我擁有詩歌評判的標準,擁有尺子和秤。對于真正意義上的一首詩,也許沒有固定的評判標準,除了我的經驗,一定有別人的經驗,更有歷史的經驗——因為我們都是凡夫俗子,我們都缺乏一雙好眼睛,根本談不上孫大圣的本事。因為我們缺乏在世俗的五指山下長時間修煉的耐心和勇氣。
【作者簡介】林野散客,1975年出生于甘肅定西,原名楊學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雜文學會理事。自1998年以來開始以林野、散客或林野散客等筆名寫作,詩歌散見于《星星》、《秋水》、《飛天》、《甘肅日報》等報刊雜志或文化網站。已出版發行的個人詩集有《老屋》(中國戲劇出版社1996年)、《漂萍》(作家出版社1998年)等。2002年主編《隴中青年詩選》。作品曾獲甘肅省第十四、十七界雜文獎、甘肅《飛天》文學獎等,并入選多種選集。現為定西市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