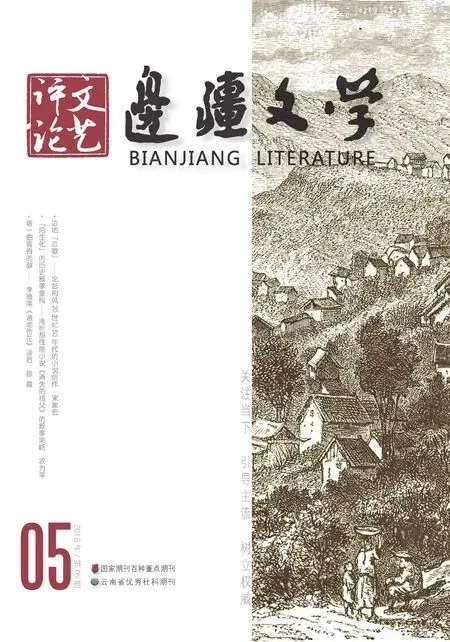追憶詩意年華
董保延
人生如歌也如詩。詩意,是人在一生當中孜孜以求和無比向往的境界。
因為詩意能夠給人帶來美感的意境,詩意具有的強烈抒情意味能使生活更多些恬淡。早在17世紀,法國一位最具天才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爾就斷言:人應該詩意地活在這片土地上,這是人類的一種追求理想。
曾經有名家說過,人進入花甲之年后,就屬于詩意的年齡。到了這個階段,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經卸除,生活的甘苦大體了然,萬丈紅塵移到別處,加上寧靜下來的環境和逐漸放慢的生命節奏,構成了一種總結性、歸納性的輕微和聲,于是,詩的意境就出現了。這種詩意,讓你超越功利,面對自然,打開心扉,縱情回憶。如果這一切用文學的名義來解讀,抑或以詩的方式來宣示,定會顯得別具一格且更加津津有味。
我讀黃懿陸剛剛出版的詩歌集《壯錦紅星》(以下簡稱《紅》)時,第一個感覺就是如此。
從這本詩歌作品集中,我首先讀到的是一位文化人已經具有的詩意的精神空間,那是灑脫、純凈、清澈,很少雜質。我以為,這是詩意的基礎,也是作品的素質。
知道黃懿陸的名字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了,從軍時常年輾轉于邊防一線,持續的邊境戰事讓我通過舞文弄墨接觸到許多好友,也認識了不少活躍在文壇上的老將新兵。那時,由文山州文聯創辦的《含笑花》詩歌報就是我經常關注的一份很有特點、極富生命力,深受戌邊官兵敬仰和喜愛的報刊。在紙質傳媒尚少的年代,一份《含笑花》無疑就是戰士一份不可或缺的精神壓縮干糧。黃懿陸就擔任過《含笑花》的主編。后來,經常在報刊雜志上讀到黃懿陸的文學作品,在云南少數民族作家群中,這位壯族青年作家獨具風采,卓爾不群。再后來,我轉業到地方,有緣與黃懿陸成了同事和鄰居。這樣,我看到的黃懿陸,便不再僅僅只是通過作品,還有了更多的近距離了解、認識、感觸。在我的印象里,黃懿陸是個嗜書如命,學有專攻,善于鉆研,勤奮筆耕的學者型人物。我曾經想過,按照一般規律,他長期給省級領導做過秘書,應該深諳官場,善用韜晦,可是身邊的黃懿陸,卻務實務本,專注專心,學識學問,潛心業務,我看到的黃懿陸,是一個重本事、精業務、有善心的文人,讓我幾乎忘記了他的從政履歷中有過的秘書身份。
我比黃懿陸年長幾歲,直到我們都已經先后邁入花甲,并且相繼退休,又共同做一些大家都有興趣、有能力、有成就的事之后,我更加感覺到,他的人格品質一旦滲透到他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之中,就隨時可能產生出一批批令人咂舌的東西來。
這幾年,黃懿陸將主要精力用于中華文明史的研究,其煌煌大作層出不窮,幾乎是年年有新著新論問世,在國內外史學界不斷產生振聾發瞶的影響力。而當屬于文學類作品的《紅》擺在我面前時,我并不因為他很多年沒有出版過文學作品集而感到驚訝,反倒將它看做是黃懿陸對這些年若干史學專著的一種響應或者補缺。如果說,作者在史學著作中體現了他對光彩燦爛的中華文明沿革與精髓的探索與展示;那么,文學新作中卻在證明,他所尋找到的華夏文明中,本來就是一個巨大的孕育著詩意的溫床。只不過,黃懿陸用一支筆追尋著中華文明輝煌中的奧秘,另外一支筆創作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在內的文藝作品。
我們把詩歌稱為心靈的歌唱,是較之其他文學體裁而言,詩歌更能坦陳心跡,直抒胸臆。在《紅》書中,這種感覺更多的是作者對人性的詩意詮釋,是他儲存在心底的詩的歲月。收入集子中的58首詩歌,最早的創作于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最近的距現在不過幾個月,但是都具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質樸真誠,詩意盎然。即使作品的跨度長達48年,作者的人格仿佛與生俱來,一成沒變,其用心良苦都體現在文學藝術創作的精度上,而作家的品質則飽含在作品字里行間的力度中。
我比較看好的是那幾首創作于早期的詩歌作品。讀這些作品,一眼即能透視到作者的坦蕩靈魂,看似直白其實深沉,仿佛平靜夜空中閃爍著靈動的星光。于是,這些詩歌,便有了生命的活力,也有了時代的烙印。《自勵詩九首》可能是黃懿陸初涉詩壇的處女作,卻已經表現出他對詩歌定義的準確理解。見景生情,以物勵志,少年詩人的壯心豪情和盤托出,亮出了一條雖身處逆境卻不氣餒,雖路途坎坷而滿懷希望的心路歷程。無論“壯志豈能一風吹,丹心永爭日月輝”的氣魄,還是“不做三年鳴驚鳥,甘當百載養樹人”的恒心,以及“書生意氣懷抱負,苦心求學攀前程”的毅力,在詩歌張力中體現著作者的追求,所謂“詩言志”不過如此。
以詩歌組成的編年史,在詩意的闡述中抒發著對青春、愛情、生活、學業、人生的觀點,是作者寫詩的又一特點。從《苦難的我》《行路難》《畫眉》《寫在高小畢業》等詩作中,我,們讀出了他中小學時代的迷茫與突圍;從《知心話》《著書之夢》《階梯》《笑》《隨感錄》等,我們讀出了他大學生活的快樂與舒心;《夜巡國境線》《哨兵之歌》《邊疆保衛戰之歌》、則讓我們讀出了他對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守衛者的崇敬與禮贊。一組《青春萌動的暢想》向我們講述的,是一個屬于作者也屬于青春的唯美的愛情故事,在這些寫于40多年前的詩行里,我們窺見了一位多情才子的愛意盎然,“我覺得自己可愛的家鄉,生活再苦也神似天堂。要問為什么這樣,因為我在愛著一位姑娘”,多么坦率直言,多么入木三分。為了證明自己的快樂,他沒有忘記詩歌所給予的力量,“多情的生活已經將我擁抱,詩歌的韻律已經將我熏陶”。愛情的魅力,即使在看到一張照片也那么熾熱,“快啊,快啊,你睜大眼睛凝視,你從遙遠的壯鄉來到我的面前”。讀這些詩,無論地作者對讀者,都能夠激發起對曾經芳華的耿耿于懷。黃懿陸用詩歌寫成的人生日歷,每一頁都是心靈的歌唱。
在詩歌創作中,敘事詩具有特別的力量。它以其特別的架構和風格,讓讀者從中能夠獲得對故事的詩意解讀。《紅》書里收入的兩首長篇敘事詩,不僅體現了作者在詩歌創作中的身手不凡,也表達了他以詩歌的名義,對歷史、民族、傳統精神的理解。詩意,因此而顯得更加史詩風范,氣勢磅礴。
抒情性,是敘事詩的一個重要特征。敘事詩以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見長,通過對具體事件的描繪來體現作者的思想感情。敘事詩雖然有故事情節、有人物形象,有環境交待,但是,它整個過程中必須滲透詩人的強烈感情,彌漫濃郁的抒情氣息。詩歌是各種文學表現形式中最富有激情和最具感情色彩的文體,創作敘事詩就更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學藝術造詣。《紅》中的敘事詩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
讀著1500行的敘事組詩《壯錦紅星》,仿佛是在讀富寧右江革命根據地的一部輝煌歷史。因為作者對紅色革命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歷程的史詩解讀,那些已經凝固的日子,被賦予了詩意的別樣色彩。一段發生在80多年前的歷史往事,在詩歌的大海里,展現激流洪波、驚濤駭浪,高揚勝利旗旌,奮進風帆。一支隊伍的功勛卓著,一個民族的無尚光榮,一塊土地的殷紅厚重,在詩意盎然的雄渾交響中,產生了強烈的感染、警醒、鼓舞人的力量。《壯錦紅星》以其主題鮮明,氣勢恢弘,突出典型,節奏得當,給云南文壇上久違了的敘事詩創作帶來了希望。
這首詩的“上篇”以大寫意的筆調,通過龍勞、谷桃、皈朝、多立村、谷留勞、碉堡、紅軍洞等7個革命歷史遺址,以及圍繞紅色根據地、紅軍指揮部、慘案等所發生的事件,全方位展現了在風雨如磐的年代,老一輩革命志士帶領勞苦大眾鬧翻身、求解放的經歷。“中篇”凸顯其特寫風格,濃墨重彩的講述了16個革命志士、英雄群體的故事,無論是悲壯、慘烈的細節,還是曲折、驚險的畫面,都洋溢著強烈的革命英雄主義,濃縮進追求理想,執著信念,甘于奉獻等理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詩中坦言:“革命根據地的故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詩人作家尚沒有深入其地讓它們發光閃爍”不僅是對革命歷史的致敬,更是對文學藝術工作者要深入基層、深入生活的呼吁。“下篇”是對全詩主題的升華和再強調,好像是一個交響樂隊中的定音鼓。它擇取了建立革命根據地之后幾十年中,老區的幾個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的故事,意在禮贊人民群眾對紅色基因的堅信不疑和世代傳承。其中《文藝演出隊》將舞臺上下融匯一體,《老紅軍的歌唱》對革命經歷的如泣如訴,《紅色根據地贊歌》瞄準“紅”的重點大做文章,作品中都跳躍著作者對革命老區故鄉的拳拳赤子之心,體現了他在駕馭長篇敘事詩這一文體時的不菲功夫。必須提及的是,作為這一篇章的壓軸篇章《壯錦上的紅星》,頗有高屋建瓴,統攬全詩的架勢。作者以巧妙的構思,將壯民族最具有特色的壯錦與革命紅旗上的紅星放到同一個畫面上加以審美:“紅色旗幟上的紅星蘊藏在人民的心里,壯錦上的圖案就繡著一顆閃爍的紅星”。通過這個關于壯錦和紅星的傳奇故事,一語道破個中真諦:“繡著紅星的壯錦掩蓋共藏身的紅軍,告慰烈士的祭品墊著彩色的壯錦”,“紅星不僅在人們心里閃亮,紅星配上壯錦就代表人民革命到底的決心”。在詩的氛圍中,歷史與未來交相輝映,浪漫與現實相得益彰,詩歌的韻律與象征意蘊酣暢淋漓,響徹在我們耳畔的,是一曲蕩氣回腸的軍隊與老百姓的壯麗頌歌。
其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所走過的路,本身就是一部恢弘的史詩,中國當代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理所當然應該反映它、表現它,這是一項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中,用文學藝術的方式,謳歌中國革命的紅色征程,不忘初心,繼承傳統,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黃懿陸的長篇組詩《壯錦紅星》,無疑是一個成功的示范。
在《紅》書中,還收有另外一首長篇敘事詩《螺螄姑娘》,這是作者對一個壯族民間傳說的詩意講述。讓我們驚訝的是。這首作者寫于40年前的作品,至今讀起來卻毫無因年代遙遠的陳舊感,反倒有一種清風徐來,小河淌水的快感。我想,這會不會與作者在那個時代的創作心境有關系呢?創作是很講究狀態和氛圍的,詩意,原本就需要有一顆干凈、透明、真誠的心來營造。很難設想,一個思緒嘈雜,心地渾濁的人會產生美好靈感,寫出佳作,尤其詩歌創作,更是對作者心態、心靈的考量。不禁想起一度在網絡上流傳過的“生活不僅有茍且,還有詩和遠方”,雖然概念有點模糊,但是每一個認同它的人都知道“詩和遠方”是一種美好。否則,這說法就不會一石激起千層浪,觸動那么多自以為茍且的人們。寫《螺螄姑娘》時的黃懿陸正值清純韶華,那時他也許也有煩惱,有茍且,但是,一旦進入了寫詩的意境,他肯定已經避開了那些生活中的浮躁和焦慮,嘈雜和喧囂,冷漠與戒備。他確乎明白,生活并不一定至善至美,但心靈是可以涵養詩意的。“詩和遠方”并非遙不可及,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恬淡悠然的情懷,釋懷感恩的心態,“詩和遠方”的到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敘事詩《螺螄姑娘》的誕生是不是首先因為如此?
《螺螄姑娘》源于壯族民間傳說,講述孤兒阿甲打漁時邂逅天仙螺螄姑娘,倆人相戀成婚,后遭惡勢力迫害,阿甲、螺娘不畏強暴,斗智斗勇,戰勝土司,獲得自由的故事。這首敘事詩最大的特點是在其中應用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歌元素,具有民歌風格,通俗達理,比興得當,情感渲染,朗朗上口。在詩歌的氛圍中,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故事被講得繪聲繪色。寫阿甲與螺娘相互傾吐愛慕之情,“妹是珍珠哥是蚌,蚌殼里面把珠藏。活著我倆不分離,死了我倆緊緊沾”,山盟海誓,如膠似膝;寫螺娘的歌聲,“蜜蜂跟著蜂王走,羊群必有帶頭羊。山歌起處天下靜,螺娘歌聲最響亮”,聽似無聲,震撼八方;寫螺娘與土司斗智,“打獵不怕山中豹,打魚不怕浪里蛟。戰勝困難靠智慧,那怕條件三百條”,斬釘截鐵,擲地有聲;寫阿甲與螺娘為百姓撈田螺解困境,“甜津津的螺肉,硬生生把鄉親們養活。吃了三七二十一天肉,燒了三七二十一天火”,言簡意賅,出神入化;寫鄉親們懷念阿甲和螺娘,“河水想起阿甲會漲,山坡想起螺娘會傷,小伙想起阿甲吹竹笛,姑娘想起螺娘就歌唱”,樸實真摯,情深意長……因為詩的表達,故事顯得更具感染力,其人物個性各異,情節細節有味,起伏跌宕出彩,為敘事詩的創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經驗。
我國的敘事詩創作曾經涌現過一大批膾炙人口、流傳已久的作品,如古代的《木蘭詩》《琵琶行》《孔雀東南飛》《長恨歌》,少數民族的《格薩爾王》《阿詩瑪》《葫蘆信》《梅葛》《望夫云》《創世紀》等等。今天,作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敘事詩應該繼續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黃懿陸創作的兩首長篇敘事詩,對于敘事詩創作無疑是一個倡導。它至少說明,當我們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的當下,如果能夠將敘事詩的作用發揮好,一定也會產生正能量的。
有詩的生活是美好的,有詩意的人生是快樂的。作品是作者的精神基因,徜徉在詩的走廊,雖然芳華漸行漸遠,但生命之夏花卻歷久彌香。《壯錦紅星》提供了又一個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