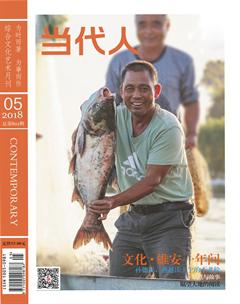美,蕩漾荷花淀
程雪莉
夏日雄安,暢游荷花淀。蕩舟荷花園,孫犁先生的美麗文字如帶著荷葉水珠,晶瑩入耳;徘徊在孫犁紀(jì)念館,久久地思考著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為什么在那樣艱苦抗戰(zhàn)的歲月里,美,依然流淌在孫犁筆下?
孫犁先生的戰(zhàn)爭(zhēng)故事里,那些洋溢著美和真情的細(xì)節(jié)常常讓我們感慨萬(wàn)千。無(wú)論是荷花淀、蘆花蕩,還是山地回憶,無(wú)論月光下編席,還是山溪邊洗衣,總有一個(gè)個(gè)美的場(chǎng)景在我們面前浮現(xiàn)。
孫犁先生的散文里曾有這樣一個(gè)細(xì)節(jié):有一天早晨,我醒來(lái),天已不早了,對(duì)間三槐的母親已經(jīng)“嗡嗡”地紡起線來(lái)。這時(shí)進(jìn)來(lái)一個(gè)少婦在洞口喊:“彩綾,彩綾,出來(lái)吧,要去推碾子哩。”她叫了半天里面才答應(yīng)了一聲,通過(guò)那彎彎長(zhǎng)長(zhǎng)的洞,還是那樣?jì)赡鄣穆曇簦骸皝?lái)了。”接著,從洞口露出一頂白氈帽,但下面是一張俊秀的少女的臉,花格條布的上衣,跳出來(lái)時(shí),腳下卻是一雙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來(lái),扔在一邊,就露出淺藍(lán)色的鞋來(lái),隨手又把破氈帽也摘下來(lái),抖一抖墨黑柔軟的長(zhǎng)頭發(fā),站起來(lái),和她嫂子爭(zhēng)辯著出去了……
據(jù)孫犁先生觀察,這些被敵人追逐奔逃的婦女們,一旦發(fā)現(xiàn)沒(méi)有危險(xiǎn)了,就倚在樹上,用衣襟擦去臉上的汗、頭發(fā)上的塵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然后成群結(jié)隊(duì)歡天喜地說(shuō)笑著回家。他分析這種心理時(shí)寫到:只要活著就是歡樂(lè)的,而且勝利的信心最堅(jiān)定。
又比如,在華北聯(lián)大讀書的葛文這樣描述土岸村的駐地:坡坎上的一棵大樹下就是我們的課堂,坎下就是我們的宿舍……大樹下,細(xì)高個(gè)子的孫犁先生,穿著婦救會(huì)做的黑粗布鞋,筷子粗的白布條綁在腳面上,粗笨的大腳伸向前去,惹得同學(xué)們?nèi)滩蛔⌒Γ犓?xì)聲慢語(yǔ),分析《紅樓夢(mèng)》的結(jié)構(gòu)、語(yǔ)言、技巧,不一會(huì)兒,林妹妹寶兄弟薛姐姐等書中人物,便被他描繪得活靈活現(xiàn),同我們生活在一起了……葛文說(shuō),文學(xué)的美好,青春的熱情,給予人們無(wú)懼無(wú)畏、寧死不屈的力量。
今天,我們也許無(wú)法體味戰(zhàn)爭(zhēng)年代,文學(xué)在生死之間有著怎樣巨大的力量,只知道,有文學(xué)夢(mèng)想的人生是那樣美好。
在尋找平山團(tuán)時(shí),意外發(fā)現(xiàn),孫犁先生在抗戰(zhàn)時(shí)期也曾采訪過(guò)“太行山上鐵的子弟兵”,和他們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并寫過(guò)“走馬換衣”的故事:孫犁先生到延安的途中,大水把他的行李沖跑了,他只好穿著部隊(duì)發(fā)的羊毛棉衣,但沒(méi)幾天,羊毛跑到衣服底部,上面就只剩下薄薄一層。當(dāng)平山團(tuán)南下支隊(duì)要出發(fā)時(shí),每人發(fā)了一件新棉衣。有一位戰(zhàn)友決定把新棉衣送給孫犁先生,他們約定,平山團(tuán)出發(fā)的凌晨,兩人在行軍路過(guò)的橋兒溝,走馬換衣。
穿著新棉衣的孫犁先生依依送別,也許這將是永別……徹骨的寒風(fēng)里,孫犁先生把這個(gè)暖心的故事記錄下來(lái),至今讓讀者心生溫暖。
正是這些歷史的記憶,紐結(jié)起我們和前輩的情感聯(lián)系,讓我們登上文學(xué)之舟,尋著紅色文脈,在美麗的荷花淀蕩漾。
從雄安回來(lái),不覺(jué)又去翻閱《孫犁文集》,忽然讀到一個(gè)細(xì)節(jié):“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村莊附近,敵人安上了炮樓。一年春天,我從遠(yuǎn)處回來(lái),不敢到家里去,繞到村邊的場(chǎng)院小屋里。母親聽說(shuō)了,高興得不知給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親養(yǎng)了一春天,剛開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給我送去了。父親很心痛,母親笑著說(shuō):‘我說(shuō)為什么這朵花,早也不開,晚也不開,今天忽然開了呢,因?yàn)槲业膬鹤踊貋?lái),它要先給我報(bào)個(gè)信兒!”
在我們的想象里,殘酷歲月,鬼子眼皮底下,應(yīng)該是提心吊膽的母親,懷揣幾個(gè)饅頭兩角烙餅,摸索到小屋,淚水漣漣竊竊私語(yǔ)……然而事實(shí)完全不是這樣。一朵綻開的紅月季(孫犁先生沒(méi)有寫什么顏色,我想一定是同母親的心一個(gè)顏色)灌滿慈愛(ài),被歡欣鼓舞的母親捧著,汲取著大地深處的力量,送到兒子的手上。讀到此處我落淚了。我瞬間明白,孫先生的美是從哪里來(lái)的了。
我們期盼著,這些荷花淀里的美,在這片夢(mèng)想之地的上空久久蕩漾。
編輯:安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