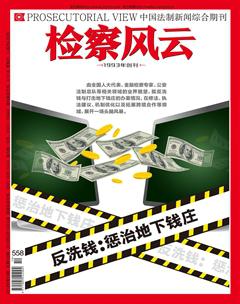抖音迷思
楊皓
以你為對象的媒介,沒有把你包含進去,它就是沒有意義的。——麥克盧漢
要問近來哪一款手機APP最為流行,那一定是抖音了。上至中老年人下至十歲不到的孩子,抖音能在各種年齡段人群中流行開去。2018年3月19日網絡上更是爆出武漢一位父親在使用抖音觀看視頻時,發現了一個可以與孩子互動的高難度翻跟斗動作,便躍躍欲試與自己兩歲的女兒嘗試起來。誰料在孩子翻轉的過程中,他沒有抓牢孩子的手,導致孩子頭部著地,脊椎嚴重受損。
那么抖音究竟是個怎樣的軟件,又緣何會突然如此流行,它的魔力真的這么大么?
從秒拍到抖音
抖音是一款社交短視頻類APP,開發者為京微播視界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創始人為今日頭條技術總監梁汝波,2017年年初,抖音獲得了今日頭條的數百萬元天使投資。抖音最早于2016年9月登陸各大手機應用商店,上線初期的抖音并沒有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反倒是在2017年3月左右在各路明星的參與帶動下突然發力,至今抖音已經成為了家喻戶曉的一款短視頻類手機APP。抖音用戶可以在抖音DIY時長為15秒左右的MV作品,只需要選擇歌曲,配以5—15秒的短視頻,就可以上傳屬于自己的作品并公開于網絡之上供人觀看。
其實短視頻類手機APP并不少見,也并非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流行起來。早在2014年左右,秒拍、快手、小咖秀等短視頻類APP就已在中國掀起過一波不大不小的熱潮。這些短視頻類APP打著各種各樣的旗號,以人人可以參與創作上傳的開放姿態,一改原本視頻網站觀眾多上傳者少的狀況,迅速在國內走紅。2015年6月,快手用戶破1億,8個月后,快手用戶就達到3億。快手CEO宿華曾在2016年12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過,快手的日活4000萬,日上傳視頻超過500萬條。2016年12月秒拍用戶滲透率達到61.7%,領先第二名頭條視頻超過8%、領先第三名快手近20%。但無論是快手還是秒拍,在經歷了短暫的瘋狂之后,皆出現了明顯的頹勢,個別短視頻類APP還因產品定位等問題遭致各種非議。
2017年下半年開始,抖音正式登上短視頻類手機APP的盛大舞臺并一躍成為當之無愧的主角。相比其他短視頻類手機APP,抖音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潮”。無論是APP的LOGO設計,還是短視頻可選配樂皆以電音、舞曲為主,都與其他手機短視頻APP大相徑庭,獨樹一幟。配合抖音軟件內自帶的各種視頻濾鏡與特效,給人以一種明顯的強節奏感、酷炫魔性之感,此特點迅速籠絡了手機重度用戶的主要分布人群——年輕人。快手、秒拍等APP曇花一現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人群定位過于單一,其作品也往往以低俗、惡搞、奇葩為主題,此亦即是它們為人詬病之重點。
抖音的“潮”可謂把快手、秒拍遇到的難點一舉擊破,在追逐時尚的年輕人中迅速打開一片市場并流行至今,如此看來也就不意外了。
魔力短視頻
當然,短視頻APP的流行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Ella是一位抖音重度使用者,每天花在上面的時間至少一兩個小時,“自從用了抖音我就很少發朋友圈了,朋友圈都是家人、同事、朋友,很多東西在發的時候都會有所顧慮,考慮合不合適在朋友圈發。但是抖音就不會,它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娛樂性的軟件,大家在上面不是跳舞搞怪,就是惡搞炫技,在上面滿足自己的娛樂需求,我覺得比朋友圈更合適。” Ella告訴《檢察風云》記者,“另外抖音會把我創作的視頻隨機推送給各種用戶,而不是像朋友圈那樣在一個封閉環境里展現,看到自己的作品獲得不斷飆升的點贊與評論,還是有點虛榮感的。”從Elle的描述中不難看出,抖音打破了朋友圈的傳播閉環,無論是用戶觀看內容還是發出內容,都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過程。用戶無需為了作品是否適合發布而困擾,也不用為了作品是否會被關注而多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品從被上傳的那一刻便不屬于用戶本身,而是屬于抖音這個巨大娛樂場,成為了所有抖音用戶可能去消費的娛樂產品。這樣的公開性,一方面讓所有用戶滿足了人類尋求關注的本性;另一方面,也極大幅度地減少了用戶為自己所創作作品負責的義務性。在一個娛樂至上的大環境里,用戶自覺組成了一個無意識的大狂歡。
抖音等短視頻內容的流行,也是人們追求短平快傳播的最佳體現之一。現代化的大趨勢之下,人類社會經歷了從閱讀文字到讀圖,從讀圖再到影視。然而影視的時間成本已經不為現代人所承受,追求簡單的刺激反饋代替了長時間的機械觀看。短視頻在15秒的時間里給用戶提供了一個尋找爆點的可能,即便是用戶在發現某一短視頻并不能給他帶來刺激之時,也可以通過手指滑動點擊,輕而易舉地進入下一個短視頻,繼續尋找可能潛藏其中的神經刺激點,似乎從不失落。
Ella表示,“其實之前那些短視頻軟件我也都有用過,但是都不長久。相比抖音這次倒是牢牢抓住了我,我想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抖音總是一股腦的把內容扔給我,而不是讓我去選擇。這種感覺一開始有點摸不著頭腦,但是慢慢地我卻愛上了這個感覺,仿佛這個軟件里永遠充滿了驚喜。”Ella所述的情況,記者也深有同感,抖音與其他短視頻類手機APP不同,打開APP直接進入的頁面并不是讓用戶去選擇觀看某一類別或多個視頻可供選擇的視頻縮略圖,而是直接開始播放某一個視頻。這類視頻往往是觀看人數較多,系統后臺經過篩選推薦給用戶,其中當然不乏刺激點。整個APP并不能找到按照類別選擇的頁面,用戶只有通過不斷的滑動來尋找下一個刺激點。但是用戶在篩選視頻的時候,也更容易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視頻,主要表現在,只要你看過幾個視頻,抖音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喜好,并主動推送類似的視頻給你。用戶對手機短視頻類APP的使用從原本的主動選擇觀看,變為了被動接受觀看。
20世紀加拿大原創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曾經說道,“以你為對象的媒介,沒有把你包含進去,它就是沒有意義的。”此言意圖說明互動性對于人類傳播的重要性。從目前抖音所提供的傳播圖景來看,我們不如把這句話稍作修改:以你為對象的媒介,沒有把你牢牢控制住,它就是沒有意義的。
圍觀與反制約
如果說快手、秒拍等手機短視頻APP還沒有抓到現代人真正需要的神經麻痹點的話,抖音就可謂切中要害了。
快手、秒拍等早一批手機短視頻APP由于其內容趨向于低俗化、鄉村化,“吃玻璃、鞭炮炸褲襠、15歲孕婦、6歲文身”等低俗甚至駭人聽聞的內容在上面屢見不鮮,不少人對其嗤之以鼻。快手、秒拍即便是贏得了巨大的市場,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用戶實質上是抱著一種調侃與戲謔的心態在使用這個APP,且他們的使用行為僅僅停留在觀看與分享,幾乎不會參與創作。這也是快手、秒拍等APP存在的最大爭議之一,網絡上甚至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言論:“南抖音,北快手,智障界里兩泰斗。”“中國腦殘千千萬,快手秒拍各一半。”
此等情況并不難解釋,玩微博、微信、豆瓣、知乎的網民,把自我視為站在互聯網用戶鄙視鏈的上游,瞧不起看快手、秒拍直播的網民,在他們眼里,這幫人太low。說白了這是一種文化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或來自于較好的家庭物質條件,或來自于高等教育的培育,但說到底,這種優越感之所以存在,乃是該軟件未能迎合他們的喜好以及他們所認為的優秀內容、值得為之逗留甚至參與的內容。抖音的出現打破了這群人的文化優越感,許多人一改原本的圍觀者角色,奮不顧身地投入到抖音的娛樂場里,尋求屬于自己的參與愉悅。
但這種愉悅終究是虛妄的,人們在耗費時間投身于一個個十幾秒的視頻狂歡中,早已忘記了尋求意義的人生目的,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全然反制約于媒介的形式而非內容。因此,許多人一邊驚嘆于刷抖音時光陰過得飛快且沒有任何實質性收獲,一邊卻難以擺脫抖音給自己帶來的精神愉悅,仿佛被其牢牢抓住,身陷囹圄。
這其實恰恰符合社會學分支之一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學說:文化在文化工業中走向反面,文化產品不再提供審美價值、不再激發思考和批判,反倒成為麻醉人、欺騙人舒舒服服順從于某種機械物的操縱與支配的工具。換言之,媒介產品的要求壓倒了作品本身的要求,效果、修飾以及技術細節獲得了凌駕于作品本身的優勢地位。
馬克思有過一段名言,我們不妨一起來欣賞一下: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他們并不是由自己選擇的條件下創造歷史,而是在他們直接遇到的、既定的、由前代人傳承給他們的條件下創造歷史。
也許下一代的歷史,注定是虛妄且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