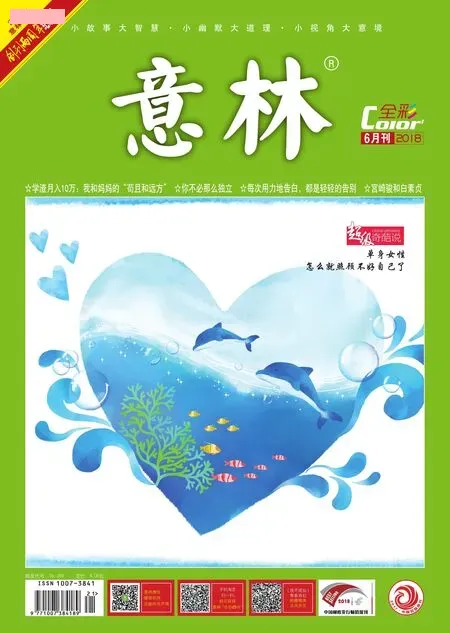一直以為是我在保護你,直到自己被你治愈了
□張佳瑋

去年初冬,我去郊區某農場練騎馬。
農場頗大,容得下幾匹馬散步放養,爭風吃醋;容得下四只鴨子并排走路,看見人就饒有興致地圍觀;也容得下一窩野貓。
眾所周知,貓媽媽養了一段時間孩子,便會母性消退,驅趕孩子。它的三個孩子,老大老二都膀闊腰圓、威風凜凜,最小的那只小母貓相形之下則柔弱嬌嫩。農場主隔三岔五來,給貓們喂一盆貓糧;貓媽媽與老大老二埋臉入盆,吃得吱吱有聲。小母貓在外圍轉著,嚶嚶柔柔地叫一聲。大哥二哥回頭朝它“唬”一下,它就回頭跑幾步,呆呆看著。
但它對人類有奇怪的好奇心。我在騎馬時,它穿過柵欄,過來看著我們。我朝它伸手,它呆呆地看著,小心翼翼地用臉蹭了蹭。我要走時,它在大柳樹下看著我,又柔柔地叫了一聲。
入冬了,天氣寒冷。我出去跑步,已覺朔風如刀。看公園里鴨子們都哆哆嗦嗦,不知怎么,我想起那只小貓來。
但我知道養貓有多麻煩,不太想真養……但是入冬了,那只小貓怎么辦呢?
我帶了一個專業的貓包,坐上小火車去了郊區農場。遠遠看見大柳樹了,聽得一聲叫,再看,小母貓已經朝我跑來了。
我抱起它,先喂了點貓糧,摸摸它的腦袋。我拉開貓包拉鏈,它自己鉆了進去,還挺享受似的趴平在絨毯上。
我拉上拉鏈,朝車站走。它大概覺出不對,開始哀聲叫喚,撓包,我也不管。
上了小火車,我料它逃不走了,這才拉開拉鏈,它伸出個腦袋,呆呆看我。我也不會貓語,只好柔聲對它說:“乖,帶你去一個暖和的地方。”
從此直到我進家門,它在貓包里一聲都沒吭。
它以后要有個名字了,嗯,就叫Shiva吧。
Shiva到家的第一天,看見貓糧盆如不要命。大口吞咽,須臾不停,讓我想到杰克·倫敦的小說里,那個餓過之后胡吃海塞,還在被褥枕頭下面藏面包的人物。平時它膽子很小,家里有人來回走,它就縮到床下,唯恐攔了我們的路。
到家第二天早上,它喵喵叫著把我引到洗手間,讓我看昨晚備好的貓砂——它已經排過便,又仔細扒拉過貓砂了,仿佛在怯生生跟我說:“你看,我這么操作對嗎?”
我給它喂了一嘴魚干,它高興地舔了舔我的手。
經過了頭半個月的報復性暴飲暴食,Shiva變得放松了。
大概發現了貓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發現了主人對它的好并不是片段給予的,它變得溫和了。我在灶臺做飯時,它呆呆地在旁打量,疑惑地聞聞食材——Shiva從不偷吃,它只是總帶著種“不可以瞞著我偷吃好吃的喲,我要看著的”的神氣。
若和我同去逛街,買了玩具,買了貓窩,買了自動喂食器,買了自動飲水機。
玩具,Shiva玩得很開心:它喜歡練習狩獵技能——雖然這輩子未必用得上了——但依然樂此不疲地來回奔跑,時不時朝我們叫一聲,儼然“你看看,我可能耐了”!自動喂食器每天定點一響,它就下樓去吃。飲水機,它瞧著新鮮,會像文人墨客看小橋流水似的,長時間看著流動的水,小心翼翼地舔一舔,再舔一舔。
這個冬天,我經歷了幾年來最深的一次季節性情緒失調——原先就有這毛病,只是這次在1月下旬加深了。我自己一向的對抗方法,是提升光線,提升體表溫度,是喝水,是好好睡覺,是自己做飯攝入大量蛋白質與水果,是收拾屋子,是運動。
但在這年冬天,這些招都不太有用。尤其是,Shiva總是在凌晨五點半就撓我起床,讓我缺覺。而缺覺對抑郁是加深的。
但我回頭想了想,既然Shiva可以接受從農場到家居的環境變化,我大概也……可以?
我開始每晚提前到十點甚至九點半睡覺,次日五點半起床。天還沒亮,喝一碗粗綠茶,開始寫東西。期間,Shiva有時跳在我膝蓋上睡回籠覺,有時嚶嚶叫著要吃魚干。我經常在早上八點半就完成了當天需要的大多數寫作內容,然后可以安心地繼續給它營造生活環境。——“不要抓!給你把玩具裝好呢!”“不要舔!!這不是吃的!!!”
二月到三月,我翻譯完了一本120頁的法語畫冊,寫完了一本書——都會在夏天出版。
除此之外,我學了點西班牙語,掉了五公斤體重。而Shiva到了三月中旬,也終于可以放棄一點依賴了——它樂意躲到鋼琴凳下的貓窩去躺一會兒,不再一味跟屁蟲似的跟著人轉。
3月下旬,我回上海見朋友。說起Shiva,眉飛色舞。
說到怎么給它構筑生活環境,說到怎么讓它從農場的寒冷環境里的野貓變成一只溫柔的貓。朋友提醒我:
“你好像也變了。”
“是嗎?”
“嗯,真的變了。”
我想想,似乎,是的。
當我給Shiva構建它的世界時,也是在改變自己,構建一個自己同樣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成長了,與此同時,我也多少成長了。雖然我這個年紀的成長與它這樣幾個月小野貓的成長,不可同日而語,但終究是,成長了。
世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改變從來是相互的,而世界如此紛繁不同,所以才值得我們去慢慢建設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