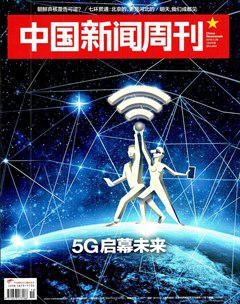生活過敏癥
東籬
每回聽人一本正經地說,“我熱愛生活”,趙小姐總忍不住想偷樂。因為她不可避免地聯想起《戀愛的犀牛》中的臺詞:“他對許多東西都過敏,米、面,他是對生活過敏。”從不認為自己感染文藝病的趙小姐想問:那個聲稱熱愛生活的人,你愛它的哪種面目?
張愛玲說,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趙小姐對這種形態的生活自是照單全收。她所不能接受的,是自我循環的庸常,是缺乏可能性和想象力的歲月。一聽別人說起“居家”“過日子”,她便暗自齜牙咧嘴地反對。
日常、穩定、規律……類似語詞是攝魂怪一般的存在,包藏著吸走靈性和創意的禍心。趙小姐有個詩人朋友,一日幽幽地發問:人為什么要有作息這回事呢?那位朋友是反日常的先鋒,畢竟靈感不按時上工,廢寢忘食小心伺候才是正經。睡夢中起了詩興,也要翻身起床捕獲佳句。
或許在詩人朋友眼中,皮囊活是累贅,自己也不稀罕奉承它。《圍城》中青年哲學家褚慎明同樣感慨,“人沒有這個身體,全是心靈,豈不更好。”只不過與透支年輕資本的詩人朋友不同,褚慎明卻是養生派,要靠外國補藥加持。不過自稱非為保重身體,只是哄乖了它,好別跟自己搗亂。
一粥一飯、灑掃應對,這種層面的生活,大概是趙小姐的過敏原。但話說回來,人總要稍事整頓,才能從事再生產,甭管生產什么。褚慎明的“自我保存論”不無道理,畢竟想活得輕盈超脫,也不能全無基礎。
趙小姐設想,在財力允許的前提下,依靠外掛,把生活讓人不快的方面外包出去。比如美食為人所愛,但為何要親自做飯?有人會說做飯自有樂趣,但每日三餐常年操持,趙小姐和身邊中青年朋友想想都不寒而栗。做飯能與創造相連,那洗碗又算什么?那擦桌子、洗衣、拖地、清潔抽油煙機和馬桶、交水電煤氣費……又算什么呢?
趙小姐有過數月駐外工作經歷,期間從不做飯,吃遍派送范圍內看得過眼的外賣,搜刮過周邊便利店所有種類快餐便當。到后來一見便當盒,她幾乎要吐出來。她有時會自我安慰:這些都是為了節約時間投入信息和情感的再生產,這點代價值得。
有時候,抱有“做點什么不好,何必為家務所累”想法的人,也會樂顛顛地花錢買逍遙,APP上花式生活服務簡直是懶人福音。不過外掛也有不穩定的時候,趙小姐遇過把早午飯拖到下午茶時段送達的外賣,也有讓她“后悔遇見你”的保姆。本想省去些麻煩,卻招來了新的煩惱。
生活過敏癥,脫敏治療本非易事,而女性想要少受生活過敏癥折磨,難度系數更躥高。直男們還在用“君子遠庖廚”來逃避烹煮,抽油煙機和洗衣機卻又掛上了“愛妻牌”,廣告里還說著“相信她喜歡”。趙小姐翻了翻白眼,那種被傳統觀念限定的生活,她可不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