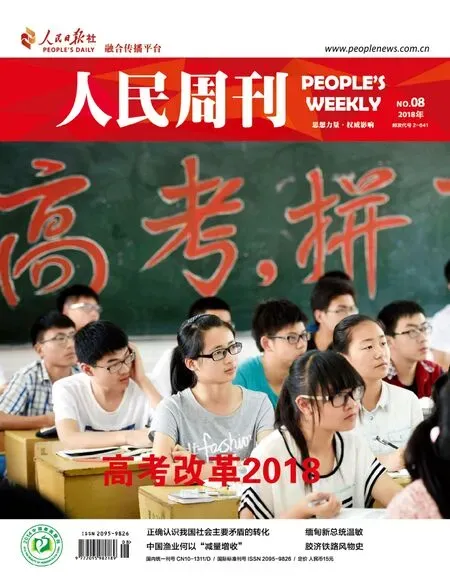財稅改革:讓頂層設計“落地生根”
本刊記者 王純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財稅改革居于重要位置。全會公報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無論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還是“轉變政府職能”,財政改革都起到頗為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財稅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改革遺留問題仍然沒有完全解決。
頂層設計都有 只需層層落實
“我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改革已有20多年,應梳理總結,借鑒西方先進經驗,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分稅制財稅體制。”山東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稱。
我國與美國等國家“稅種分開,稅權分立,機構分設,轉移支付”的分稅制有所不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1994年分稅制方案,設立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體系,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是地方主體稅種。但隨著2002年所得稅實行中央與地方六四分成,2016年5月1日全面營改增后新增值稅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地方稅體系群龍無首,缺乏主體稅種。而且,作為中央地方共享稅的新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占稅收總收入比重70%左右。顯然,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九大提出的“健全地方稅體系”的改革任務,必須立足于“共享稅為主體、專項稅為輔助”的國情,不可能建成美國式的各級政府都有主體稅種和輔助稅種的分稅制體系。同時,與美國的分權模式不同,我國稅權是高度集中的,再加上這次國家機構改革確定的國稅地稅機構合并,形成了“共享稅為主體、稅權高度集中、國稅地稅合并統一”的中國特色的分稅制財稅體制,這種財稅體制適應了我國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
還要看到,分稅制的基礎是中央與地方事權的合理劃分。因為事權范圍決定支出規模,進而決定收入規模。“中央與地方事權支出責任劃分不明確”是這次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比如,外交、國防自然歸中央財政,但像高等教育行業有時就不好劃分,一些高校常常被收歸中央或下放地方。盡管如此,隨著改革進程,國家先后推出了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劃分以及基本公共服務領域財政事權劃分辦法,來逐步理順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其實已經有了頂層設計,只需要去層層落實。”潘明星稱。
完善財稅體制尚有空間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高培勇認為,在“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上,財稅體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了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將從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三方面入手。前兩項明確了具體的改革任務,后一項更大程度上涉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類似企業只有一個財務部門,不能所有的部門都來收錢,其他職能部門應將重點放在提供公共服務上,否則會出現利益沖突。現在不少政府部門通過設立各種審批、檢查的門檻,設立各種收費項目,作為部門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未來,可從財政制度上保障各部門的經費,使得他們的立足點放在提供更好的服務上,罰款僅僅是處罰措施,而不是收入措施。
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認為,目前財政體制運行中存在不少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地區性的稅收優惠政策繁多。因為多年事權模糊的結果造成“事權層層下移”,使得基層財力壓力頗大。現在地方政府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亂開口子”的問題,這種結果部分歸咎為我國稅法的內容比較寬泛,地方在執法過程中,有很多變動。地方“亂開口子”,即政府任意增稅或減稅的行為,實際就造成了企業成本的增加或減稅,導致了不正當的競爭。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經濟法室主任席月民認為,公共財政是法治財政,強調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法治化。2016年財政部專門制定了《法治財政建設實施方案》,強調要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并大力推行財政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這對依法規范和治理地方稅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今年,分稅制改革又邁出了新步伐,全國人大已經同意國務院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并,從而改革了國稅地稅征管體制,這為集中地方稅權、降低征納稅成本、提高稅收征管效率提供了組織保證。從未來一段時期的立法取向看,應當在財稅立法中全面建立各級財政重大決策的合法性審查機制,嚴格規定財政重大決策責任追究制度,依靠各類監督和問責制守住地方稅收政策的合法性底線。
讓法律約束稅收權力
要維護市場統一,不能對某些部門或行業有過分的稅收優惠,而對其他一些部門又有過分的稅收打壓,稅收應通過法律的規制來盡可能維持中性。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山東團代表高明芹、李學海也曾提交議案,指出了目前財稅改革中存在的一些現實問題。

“在市場經濟國家,稅收中性強調的是政府課稅不能扭曲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應盡可能地減少對市場機制的干擾或破壞。但從各國實際情況看,稅收激勵是不可避免的,與經濟增長有關的某些稅收減讓優惠措施也被認為是合適的。實踐中,稅收優惠被詬病往往是因為其權力行使缺乏制度制約,導致有關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屢屢濫用稅收優惠權。”席月民稱,雖然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我國已經越來越強調稅收法定原則,但現行稅收法律法規對稅收優惠權的規定仍顯粗疏,立法對相關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是否享有稅權(包括稅收優惠權)并不清晰,未來的分稅制改革需要進一步強化稅收立法權的行使,在稅收的產業發展激勵、地區發展激勵方面給予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以必要稅權,形成資本激勵、外資激勵、出口激勵等稅收減讓措施的合理設計,進而使目標行業和目標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更接地氣,更符合我國產業升級和區域平衡發展的要求。
三中全會的公報提出“現代財政制度”的概念,該制度意味著收稅、財政支出、預算管理等都要有法可依。實踐中,可能存在通過的預算規定了當年的財政收入,但稅法要求依法征稅,因此造成了超收收入,一些部門刻意在年初報低預算,造成大量超收收入,免于人大審議。
對此,席月民認為,我國現行《預算法》是2014年修改的,在立法宗旨、調整范圍、預決算原則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全口徑預決算、地方政府債務、轉移支付、預算公開方面也作出了諸多創新,在預決算編制、審查和批準、執行和調整、監督和法律責任方面也進行了修改完善,從該法的實施效果看,總體情況良好。我國預算收入按預算年度統計計算,實踐中應嚴格執行《預算法》,使預算編制、審查、批準、執行、調整和監督真正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