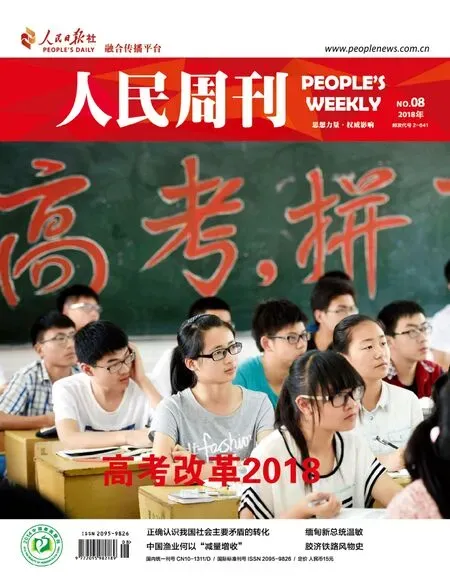張彌曼:82歲的“國民女神”
錢敏
近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彌曼在法國巴黎獲頒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成為我國第六位獲此殊榮的女科學家。領獎臺上,82歲的張彌曼自信從容、優雅端莊,多國語言來回切換,技驚四座。

圖 / 2018年3月22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教授張彌曼(中)榮獲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
“女性諾貝爾科學獎”
素有“女性諾貝爾科學獎”之稱的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設立于1998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法國歐萊雅集團聯合設立,每年評選出全球5位杰出女科學家。最初,該獎只針對生命科學領域,獎金為每位獲獎者2萬美元,從2003年起,該獎評選范圍擴展至其他科學領域,獎金也增至10萬美元。迄今為止,已有來自45個國家的91位女科學家獲得了這一獎勵。
據了解,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獎項分地區設置,分別為拉丁美洲獎、歐洲獎、亞太獎、非洲與阿拉伯語國家獎、北美洲獎。該獎側重于對科學家整個學術生涯的評價,兼顧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公共服務三方面的貢獻。
今年的5位獲獎者分別為來自亞太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張彌曼,來自歐洲的英國植物分子生物學家卡羅琳·迪恩,來自北美洲的加拿大發育生物學家珍妮特·羅桑,來自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生態科學家艾米·奧斯汀,以及來自非洲的南非兒童健康醫學專家希瑟·扎爾——她們都是在各自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女科學家。
在張彌曼之前,我國已有5人先后獲得過該獎項,她們是:從事高分辨率顯微電子學物質結構研究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方華教授(2003年),在神經生物學方面的發現使人類最終治愈帕金森氏癥、老年癡呆癥成為可能的中國香港科技大學葉玉如教授(2004年),在發光材料和太陽能創新技術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國香港大學任詠華教授(2011年),憑借納米固體化學原理尋找新型能源材料獲獎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謝毅教授(2015年),以及在禽流感生物學領域取得領先成果的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陳化蘭教授(2016年)。
“她的創新研究工作為水生脊椎動物向陸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證據,推動了人類對生物進化史的認知進入新的階段。”本屆頒獎典禮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如此評價張彌曼。
“先結婚后戀愛”
古生物專業是個不折不扣的冷門專業。還記得因“一個人的畢業照”而走紅的北大女生薛逸凡嗎?她學的就是古生物專業。9年時間里,北大這個專業6代單傳,只出了6個畢業生。就是這樣一個冷門專業,82歲的張彌曼將一生交付給了它。
1936年,張彌曼出生于江蘇南京。小時候,張彌曼喜歡跟父親去溪邊網蝦,到菜地捉蟲,到麥田看螞蟻爬上麥稈尋找蚜蟲,用放大鏡觀察花蕊和昆蟲復眼……盡管社會動蕩不安、生活顛沛流離,但在有著留洋學醫背景的父親庇護下,年幼的張彌曼樂在其中。
響應國家號召,17歲的張彌曼放棄學醫的愿望,毅然報考了北京地質學院。一年后,張彌曼被選送至蘇聯學古生物。一頭霧水的她拿不定主意選哪個方向,躊躇之際,魚類學家伍獻文給出了學古魚類的建議。
“決定你一生就要做這件事之后,就開始做起來。慢慢地,就覺得很有意思。”獲獎感言中,張彌曼將之比作“先結婚后戀愛”。求學蘇聯期間,她經常到莫斯科河岸邊采集魚化石,拿它和撒網捕來的河魚作對比。1960年回國后,進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工作的張彌曼繼續她的尋“魚”之旅。那時候,每年張彌曼都有3個月左右的時間在荒野采集化石。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飯,有時不得不在村里祠堂戲臺過夜,身上長有虱子……回首往事,張彌曼不覺辛苦,但覺幸福。
1966年,張彌曼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自然博物館做了一年研究,1980年,她又回到那里攻讀博士學位。其間,張彌曼利用瑞典學派的連續磨片法對4億年前的云南早泥盆世楊氏魚進行了研究。這是個精細活兒,但難不倒中學解剖蚯蚓時連血管都不會碰壞的她。
張彌曼把楊氏魚化石封閉在模型中,每磨去約1/20毫米就繪制一張截面圖,2.8厘米的化石整整繪制了540多張。采用這種方法,楊氏魚腦顱、腦腔及血管、神經通道的結構等都被精細復原,這是即使CT照影法也無法做到的。經過研究,張彌曼發現楊氏魚不但沒有內鼻孔,也沒有鼻淚管、顱中關節等。
當時學術界普遍認為: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四足動物都是從總鰭魚類演化而來的,因為它們有和外鼻孔相連的內鼻孔,所以可以上岸呼吸。果真如此的話,為何眼前的楊氏魚屬于總鰭魚類,卻沒有內鼻孔呢?楊氏魚沒有,那其他總鰭魚類呢?帶著這樣的疑問,張彌曼繼續對國內外發現的多種總鰭魚類化石進行了仔細研究,結果發現它們全都沒有內鼻孔。
沒有內鼻孔,也就不存在上岸生活的物質基礎,那認為總鰭魚類是四足動物祖先的說法自然無從談起了。張彌曼的發現震動世界古生物界,由此開啟了對四足動物起源的新一輪探索。
“拔尖人才還需要更多一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目前全世界女性科研人員的比例僅為28%,比起20年前盡管已經增長了12%左右,但不到30%的比例仍然很低。此外,女性獲獎者在諾貝爾科學獎歷史上所占比例更小,僅為3%。
“中國女科研人員的比例在持續上升,但拔尖人才還需要更多一些。”張彌曼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她又明確表示:“我覺得女性和男性在科學研究上沒什么區別。”她說自己帶過3個優秀的女學生,研究所中的女孩子在能力上完全沒有問題。中國科學院大學地球與行星科學學院研究員朱敏就是她口中的優秀女學生之一,早些時候,張彌曼將學術“含金量”頗高的泥盆紀魚類研究傳給了她。繼承恩師“衣缽”的朱敏不負眾望,帶領團隊在《自然》《科學》等重要刊物上發表重要論文十余篇,還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重要獎勵。
“當我慢慢意識到許多女孩子、特別是我自己的學生,并不是沒有實力,只是因為社會家庭的共識,因為在某一階段或主動或被動地必須做選擇題,而脫離了她們本來挺有天賦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中國著名女科學家顏寧在一篇名為《女科學家去哪兒了》的文章中提到。她觀察了自己身處的生物學界,發現性別失衡往往發生在博士畢業、博士后結束、獨立事業開始的時期。博士后訓練結束開始求職時,成為學術帶頭人(PI)的女性比例驟減,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為例,70位PI中,女性僅3位。
為了事業,難免會有所犧牲,女性科學家尤其如此。獲獎感言中,張彌曼特別提到感謝家人,包括女兒。女兒出生不久,就被送去了上海爺爺奶奶家,從此一家三口分隔三地多年。當大家紛紛為張彌曼的不凡成就驚嘆時,她這樣寄語年輕人:“遵從內心選擇職業,學會堅持。”
“我們正生活在不斷創新的科技時代,解決面臨的問題要依靠人類共同的智慧,也需要女性科學家的才能和創造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阿祖萊強調。如何讓更多女性參與其中?這本身也是對我們智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