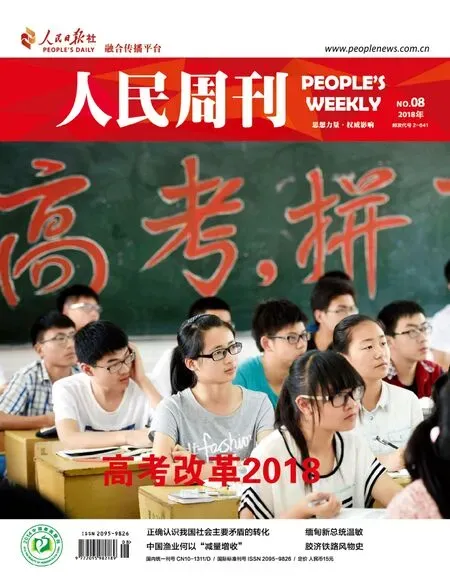打通高校與院團的“最后一公里”王珮瑜的國粹傳承路
本刊記者 付冰冰
在梨園行被稱為“老板”的大多是大腕式的人物,他們能撐起一個戲班,引領一段風潮。王珮瑜就是這樣一個人,熟識她的朋友都稱她為“瑜老板”。作為上海京劇院著名京劇余派老生,第二十五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這個舊式梨園行的叫法,在她身上沿用至今。
漫漫啟蒙路
得益于母親的啟蒙與培養,王珮瑜兒時就開始學習評彈、琵琶、書法、講故事、演小品,并取得了一定成績。到了十一二歲時,票友舅舅對她說:“珮瑜,你雖然學了這么多東西,卻連京劇都不會,那就不算很厲害。”彼時因評彈成為蘇州小童星的珮瑜,下定決心走近京劇。
王珮瑜最初學習的是老旦,僅僅兩個月之后,便獲得了江蘇省京劇比賽第一名。獲獎后不久,有一次電臺錄音京劇傳統曲目《釣金龜》時,王珮瑜在錄音棚里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來自上海、專門研究余派的范石人,他是王珮瑜從老旦轉攻老生的引路人。從此以后,王珮瑜邊讀初中,邊學老生,并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去上海,仔細琢磨范石人給她的兩張唱片——一張余叔巖先生的《十八張半》,另一張則是孟小冬《搜孤救孤》的現場錄音。
1993年底,在參加紀念程君謀先生的演出上,王珮瑜獲得了梅派傳人梅葆玖大師的賞識。次年春天,王珮瑜隨中國少年京劇藝術團去香港訪問演出,蔡國蘅先生(蔡先生是孟小冬弟子)夫婦、余慧清先生(余叔巖次女)的女兒一家亦在現場。演出結束后,蔡先生夫婦邀請王珮瑜和恩師王思及老師宵夜。到餐廳坐下的第一句話,蔡先生說:“珮瑜一出場,我們就感覺‘老師’回來了。”
此后多年,她與蔡國蘅先生一直保持著聯系,蔡先生將坊間未公開的戲稿、錄音,以及孟小冬先生的遺物——一條絲絳,傾囊贈予王珮瑜。這場演出對王珮瑜來講意義非凡,它不僅是一次交流演出,更是一次朝圣之旅。
用行動化解質疑
“研究生班是培養新一代京劇每一行每一當領軍人物的集體,希望學員都能朝著這個目標去努力。”在上海戲校聽到的這番講話,一直深深地印刻在王珮瑜的心里。從那時起,她把成為中國京劇新銳領軍人物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這個目標也許達不到,但我會為之不斷努力。”
王珮瑜身體力行地投入慈善、公益活動中。經歷恩師王思及的辭世、2008年的天災地震等無法預料的事情之后,王珮瑜愈發深刻地堅信:“不能僅僅為自己活著,要做一個建設者,讓更多人因為自己而變得美好。”
僅僅2017年一年,王珮瑜全年各項演出高達40余場,吸引超過3萬人次觀看;《瑜樂京劇課》30余場,近1.3萬人次參與;喜馬拉雅音頻節目《京劇其實很好玩》更新近100期,開創了戲曲付費音頻的先河,節目中近20萬字的內容撰寫和整理,吸引了超過2萬訂閱用戶,140萬人次收聽。在碎片化閱讀、快餐式學習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常態時,王珮瑜用實際行動為入門門檻很高的京劇文化打開了一扇大門。
“舞臺之外的延展地很廣,未來我會繼續通過‘互聯網+音頻’‘互聯網+視頻’的方式去普及推廣京劇教育。”在王珮瑜看來,喜愛京劇的人們可以選擇在劇場里花幾個小時去看一場戲,同理,只要有真功夫,人們同樣會為知識、為藝術付費,通過多種途徑去感知京劇的魅力。
傳承與推廣的過程中,問題和困難始終存在。“這是非常公平的事。”王珮瑜告訴本刊記者,最大的困難是時間不夠用,用于公益的時間多了,用于自身的時間對應著就少了。面對關心的聲音,她用一如既往的高水準演出消除善意擔憂,面對質疑的聲音,她用積極的心態和行動去化解質疑。“我在做的事情不是馬上能看到效果的事,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也需要時間來證明自己。”
“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一開始大家對個體做京劇文化推廣及傳播會有顧慮,對于資質以及專業度會有質疑。”隨著時間的推進,王珮瑜身體力行推廣京劇文化進高校、進社區的公益系列講座,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可,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社團機構的慕名邀請。

圖 / 王珮瑜,著名京劇演員,余派老生,京劇新生代領軍人,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上海市第十二屆政協委員,2013年上海領軍人才、2015年中華十大文化人物、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文化部優秀專家,第十五屆人大代表,中國戲劇梅花獎、白玉蘭戲劇主角獎獲得者。(2017年9月,王珮瑜在香港黑盒劇場出演《春水渡》現場)
打通高校與院團的“最后一公里”立足教育夯實戲曲藝術根基主體
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民族文化,近些年,隨著一系列扶持傳統文化的政策先后出臺,社會各界對中華優秀文化的認同感越來越強,學習與了解傳統戲曲藝術的需求日益增多。
如何做好大眾層面尤其是青少年群體的公共戲曲藝術教育,是王珮瑜與她所在的上海京劇院一直關注的問題。
據了解,我國文藝院團始終擔負著創作與演出的中心任務,隨著社會各界尤其是中小學校對傳統文化需求的不斷擴大,專業院團近些年的教學資源已明顯感覺供不應求,依靠專業院團和演員個人去做戲曲藝術的傳播與推廣,精力與能力均受限。
為響應文化部試點“京劇進課堂”政策,從2008年開始,上海市教委安排京劇院專業演員進校教課。相關統計數據表明,很多試點學校因沒有懂得戲曲專業的配套老師輔導,無法深入開展教學工作。
王珮瑜認為,戲曲藝術的根基主體應該立足于教育。據了解,長期以來,我國中小學的藝術和審美教育相對單一,主要以音樂課程為主。中小學音樂老師大多畢業于師范類藝術教育專業,所學的大多是通用類音樂知識,基本無任何戲曲功底。為中小學培養一批擁有戲曲功底的音樂、藝術老師,擴大專職從事青少年戲曲、音樂教育的師資隊伍的任務,迫在眉睫。
“現在全國重點國有京劇院團很多,政府的扶持力度非常大,辦學習班,給年輕的藝術家提供不同的平臺展現自己,去學習和進修。但最大的問題是,專業培養戲曲人才的院校與專業劇團之間的銜接不夠緊密。”
據王珮瑜介紹,由于戲曲表演的特殊性,只有少數畢業生能夠進入專業院團工作,成為專業演員。由于專業戲曲院校對人才培養的方向具有單一性,使得很多懷揣“成角兒”夢想的學生,不但面臨高淘汰率以及倒倉等高風險,同時也面臨一畢業只能改行的困窘局面。“戲曲藝術的專業教育人才已經成為新時代急需的人才。立足于戲曲這個行業,希望專業院校在學科的安排設計上更合理、寬泛,讓更多熱愛戲曲的年輕人除了追求‘角兒’這條路還有別的選擇。”王珮瑜說。
自誕生之日至今,作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京劇已走過兩百年歲月,傳承的時代使命落在了以王珮瑜為代表的青年一代身上。
談及未來,王珮瑜對本刊記者表示,會繼續活躍在推廣和演出的舞臺上,并成為平臺的搭建者,讓熱愛京劇的朋友在平臺上看到更多的年輕面孔,讓更多專業京劇演員通過這個平臺走到更閃亮的舞臺,做更大眾化的戲曲教育與普及工作。
王珮瑜說:“京劇本身具有自我迭代能力,傳承與傳播靠人。不能一味活在過去,要有活力,從‘被動輸血’轉為‘主動造血’,作為戲曲從業者,我們要有成長以及學習的能力。”珍藏過去,立足當下,著手未來,這是新時代呼喚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