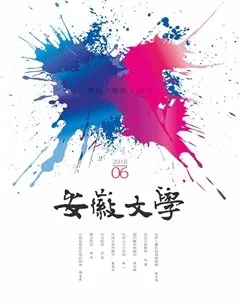讓語言和存在同時到場
郭寶亮
春林兄囑我寫一篇有關自己批評道路的文章,這使我有時間檢視一下自己,正好談談自己的一些粗淺的體會,好供大家批評指正。
我的文學批評活動起步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時候我的批評和研究在方法論上還不是很自覺,比如對張煒小說的研究,雖然是從“意象/關鍵詞”進行的研究,也屬于我后來實踐的“文體學”研究的范疇,但尚處于朦朧階段,所以比較自覺的批評和研究活動還是九十年代末對劉震云的研究。那一年,我奉朋友之約寫一本有關劉震云的小冊子。在這本書中,我意識到劉震云小說的基本藝術品質與其所要表達的思想意蘊之間的關系,比如新寫實階段的劉震云,喜歡在小說的第一句話寫“吃喝拉撒”,這第一句話的“吃喝拉撒”絕不是隨意而為,而是奠定了整個小說敘事的基調,通過這第一句話,我們可以觸摸整個小說的文化意蘊。還有劉震云這一階段小說的“流水賬式”結構,這種以事件“堆砌”的方式所體現的就是主人公庸俗、無奈、尷尬的現實處境的表征,而劉震云的這種結構方式,也是大部分新寫實小說的基本結構方式。另外,在新歷史主義階段,劉震云的反諷戲謔風格、共時性歷史時空體等等藝術上的特質,也是我們理解他的這些小說的一把鑰匙。劉震云善于通過時間的空間化,以共時性歷史時空體的結構方式來展現歷史恒定不變的本質。
二十一世紀初,我有幸跟隨著名文學理論家童慶炳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王蒙小說文體研究》的時候,童先生的“文體學”和“文化詩學”的理論方法,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使我更加自覺地堅定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這一方法就是“大文體學”的方法,也就是童慶炳先生倡導的“文化詩學”的方法。童先生說:“我理解的文學有三個向度,這第一就是語言,第二就是審美,第三就是文化。……語言—審美—文化,這三個向度是文學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文化詩學的旨趣寓含在文學的語言向度、審美向度和文化向度中。”我所理解的童慶炳先生的“文化詩學”的這三個向度,就是充分注意了文學的“語言(形式)本體”與“生存本體”,并通過“審美”這一中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讓語言和存在同時到場的方法。實際上,所有的文學創作和批評都是人的一種生命活動。因而,對文學的研究和批評從來都不應該是只對修辭學意義上的狹義的“美文”的關注,而是通過對“語言(形式)本體”的穿透而直達人的生存困境,并發掘生命本體內在的文化精神的一種體驗的詩學。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在對王蒙小說的研究中,采用這種“大文體學(文化詩學)”的理論方法,即首先從語言、敘述、結構、文本體式等形式層面入手,進而發掘這些語言(形式)背后的作家心態;同時又深入到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去,從而將語言(形式)本體與生存本體連結起來,力求打通形式與內容、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界限。
在后來寫作《新時期小說文體形態研究》一書時,我將王蒙這一個案的研究方法擴展到對整個新時期小說的研究上,試圖從文體學角度對新時期幾個獨特成熟的文體形態——諧謔—狂歡體、象征—寓言體、詩化—散文體、新成長—自傳體——加以研究,在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反響。
對以上的方法,我有時也把它簡化地叫作“從文本中來,到文化中去”。從文本中來,就是說一切應以文本的閱讀為出發點。在對文本的細讀中,探討文本的藝術價值。我覺得,文學作品的價值首先在于它的藝術價值。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必然在藝術上有它的獨異性,有它的對文學史而言的特殊貢獻。批評家要以自己專業的眼光發現、挖掘文學作品獨具的藝術價值,尋找其語言、結構、敘述方式乃至文體諸多方面的問題。正像巴赫金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復調”;熱拉爾·熱奈特發現并深入研究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的敘述話語;海德格爾對荷爾德林及其詩之本質的揭示;羅蘭·巴爾特對巴爾扎克小說《薩拉辛》近乎超級細讀的《S/Z》……這些先賢們的批評實踐難道不能夠給我們深長的啟發嗎?
然而,我覺得,如果把文體學研究只限定在文學的形式層面,那只是文學的一部分,還不能界定文學的全部特質。文學是自律與他律的統一,如果說,文學的自律性正是文學的形式要素,而他律性則是文學的內容要素。文學作為有機體,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因而說形式實際上也是在說內容。故此,我贊同童慶炳先生給文體所下的定義:“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這個概念實質上包含著三個層次:文體首先體現為外在的、物質化的,以語言學為核心的文本體式,其中包括語言樣式、敘述方式、隱喻和象征系統、功能模式以及風格特征種種;第二個層次則是通過文本體式折射出來的作家的體驗方式、思維方式與精神結構,它與作家的個性心理緊密相連;第三個層次則與作家所在的時代、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相聯系,體現的是支撐文體的復雜文化場域。而后兩個層次就是一定的話語秩序。由此可見,文體絕不是單純的語言體式,而是包含著多種復雜因素的話語秩序。實質上,童慶炳先生對文體和文體學的改造,就是要摒棄形式與內容二分的固有偏見,試圖打通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界限,使文學研究真正成為“文學”的研究,而不是單純的“形式”研究或“文化”研究。因此,這樣的文體研究,首先是要回到文本、回到文本的形式上來,但還要不止步于文本形式,而是要到文化中去。
“從文本中來,到文化中去”的文體學的方式,屬于一種新的批評范式。這決定了它與傳統的純形式批評不同。這種范式也要吸收一切形式批評方法的營養,比如傳統的修辭批評、新批評的細讀、經典敘述學的話語分析、傳統文體學的“前景化(突出)”方法等,但它更側重于對形式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要素的挖掘。因此,它更青睞于像羅曼·英伽登的現象學美學和巴赫金的超語言學的方法。英伽登的現象學美學認為文學作品是一種意向性的存在,這種存在既有實在客體的性質,又有觀念客體的性質,從而建立了由物質、形式、存在三方面構成的綜合本體論。進而,英伽登提出了文學藝術作品的結構層次說,他把文學藝術作品分為四個層次:語音現象層、意義單位層、再現的客體層、圖式化觀像層。四個層次各有獨特性,又有機地聯系成一個整體。英伽登的美學思想對于建構新的批評范式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巴赫金的超語言學方法,對于我們同樣意義重大。這種超出語言學的方法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對話關系。對話關系是人們實際生活中的交際語言,而這種語言正是索緒爾所摒棄的言語。言語的對話交際性質,決定了它所具有的社會事件的性質。活生生的言語都處于一種具體的語境之中,而每一種語言都以其獨有的語調而存在:“語調即評價”。這說明,言語(話語)研究不同于傳統的語言學研究,其特有的文化價值是不應該被忽略的。一般而言,語言都具有表意功能、表現功能和文化功能這三種主要功能。傳統語言學研究往往止步于前兩個功能,而巴赫金的超語言學研究則更加關注文化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巴赫金對對話關系中的雙聲語現象進行了分析,比如對《窮人》中的杰符什金語言風格的分析。他從其語言的阻塞和語言的中斷發現杰符什金的語言“是怯懦的、惶愧的、察言觀色的語言,同時還帶著極力克制的挑戰”,“杰符什金幾乎每說一句話,都要回望一眼那不在場的談話對方”。接下來,巴赫金分析了這種“察言觀色語言”的結構方式。這就是在杰符什金的語言中“折射”出他人語言。正是這種“折射”改變了原來的語氣和句法,使得主人公語言出現“語氣的斷續、句法的破碎、種種重復和解釋,還有冗贅”。而這種語言現象不是修辭方式,而是包含著深廣文化內涵的,那就是“在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中,滲入了他人對他的認識;在主人公的自我表述中,嵌入了他人議論他的話”。在這里,巴赫金改變了傳統語言學研究的方向,進而尋找到一種全新的研究天地,對我們進行文體學研究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
當然,任何方法都不是一種死板的教條,而是活生生的融入血脈的體悟的結果。因此,我并不反對批評甚或研究的文章在外在形式上的活潑和多樣風貌,但批評和研究在整體神髓上還是應該保有基本的學術品格。我贊成批評與學術研究的結合,一種缺少理論功底和學術支撐的批評是無根的批評。當然任何理論都不是萬能的,我主張的是理論內化、學以致用——理論在批評中是鹽和水的關系,鹽融化在水中,雖然看到的是水,但絕不是原來的水,而是鹽水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學院派批評是必要的。大家常常詬病“學院派”批評,主要是由于它那生吞活剝的刻板的理論“夾生飯”的緣故。它的名聲,主要是被那些疙里疙瘩引用西方理論家的名言警句的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給敗壞的。多年來那些假洋鬼子們,實際上屬于二道販子甚或三道販子,把西方的所謂理論,一知半解地塞進所謂的批評中,這樣的批評其實不應該是真正的學院派。真正的學院派批評絕對不是只掉書袋子的批評,而是將理論活用于文學的鮮活現場中的批評。我歷來認為,當代批評甚至學術,都必須是有鮮明問題意識的批評和學術,但這種問題意識,不僅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還應該是針對文學本身的,因此,從文本中來,到文化中去,仍然是一種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論。
2018年2月26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