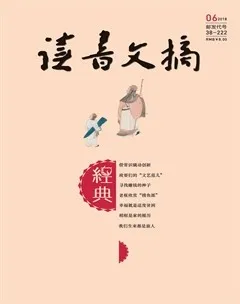長得好看的代價
2018-06-09 02:46:48蔣方舟
讀書文摘·經典
2018年6期
蔣方舟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去了一趟北京電影學院。回想起那個下午,就像《百年孤獨》的開頭——多年以后,我老得五官難辨四肢癱軟,還會回憶起我在北影看美人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我像土猴一樣蹲在地上,仰頭看著各式各款美人從我面前走過:有的長發及腰,靨笑春桃;有的帥氣清俊,嚴正方冷。我自卑得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最后甚至不敢抬頭看,只聽得藝校美人們腳步錚響,宇宙發飆。
我的記憶把那個下午渲染得太過魔幻,但我絕沒有夸大我受到的震撼。我去北影是為了找高中同學,她當年也是風云人物,是市電視臺的少兒主持人,走在街上會一路被小朋友當街撲倒,擅長琵琶古箏小提琴,大白蘿卜上鉆幾個眼也能吹出個曲子在學校晚會上表演。
在北影的校園,當她朝我遠遠走過來,環繞了好多年的霧障光圈忽然退去,我才發現她矮小蠟黃,一見到我,她立刻自我保護式地警覺笑道:“怎么樣怎么樣,我們學校好看的人多吧?”我點頭,對藝術生來說,好看的標準如此高,令我震驚,照《紅樓夢》的說法:“我們這些人,越發該睡到馬圈里去了。”
我還記得高三的時候,考生們毅然分成蹉跎走形型以及光鮮洋氣型,后者都是藝術院校的考生,陽光明媚的下午,藝考生們穿著緊身練功服從教室窗口走過,我們做題做得面如死灰,羨慕地看著他們,心想:長得好看真好。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出生的時候已經完成了,那就是漂亮。
而現在我才知道,長得好看并不是命運的大赦,偏心地網開一面。……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