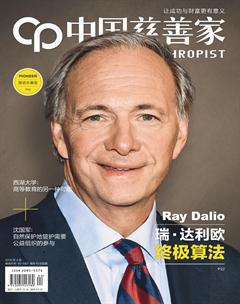陳禹嘉:看見世界,看見未來
王筱



薪火相傳
一開始,從未在商業上表現出過人天賦的陳禹嘉,試圖說服父親陳一心成立家族辦公室時,陳一心是極為抵觸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父子關系變得非常緊張。
家族辦公室最早起源于古羅馬時期的大“Domus”(家族主管)以及中世紀時期的大“Domo”(總管家),是指將金融專家、法律專家和財務專家集合起來,監督及管理整個家族財務健康、風險管理、教育發展、慈善安排等的管理模式。現代意義上的世界第一個家族辦公室誕生于1882年,由約翰·D·洛克菲勒建立,而后被西方頂級富豪家族廣泛應用。但截至上世紀90年代,家族辦公室在亞洲依舊屬于一個新鮮概念。
陳一心家族原籍江蘇省啟東市兆民鎮頭補村,于上世紀40年代遷往香港。之后,從英國學成歸來的陳一心與父親陳兆民一起興辦實業,先后開拓和發展了中國香港、東南亞、中東、非洲大陸等地的搪瓷業及煙草制造業市場,成為馳名香港的實業家。
陳禹嘉出生于中國香港,在尼日利亞長大,在英美接受教育,有著國際化的成長背景,卻深受家族家國情懷的影響。1994年,在美國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時,陳禹嘉發現這家業務規模龐大的公司之所以經營蒸蒸日上,正是因為采取了家族辦公室的模式。他意識到,可以嘗試引進這一模式,幫助管理祖父陳兆民在非洲創立的家族企業等財富,延續與增強家族的凝聚力。
被父親拒絕后,陳禹嘉并不死心。他“軟磨硬泡”,懇請父親先提供一筆起始投資,由自己負責家族辦公室的籌備與建立,父親僅需出席每季度的業務報告會,傾聽家族資產管理方面的進展與投資動態即可。在陳禹嘉的堅持下,其家族辦公室Legacy Advisors Limited成立并開始運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一次業務報告會上,陳一心驚喜地發現,家族辦公室的業績遠勝于大多資金管理公司。次年年底,他遞給兒子一張支票,上面的金額足以覆蓋家族辦公室之前所產生的經營成本費用。
“他能相信我的判斷,我也能以平等的地位跟他溝通了。”對陳禹嘉而言,這象征著父親開始認可自己的決策。父子關系自此改變。
是時,在故鄉江蘇啟東開展的慈善事業屢屢受挫,陳一心身心俱疲,正猶豫著要不要放棄。與父親達成和解后的陳禹嘉,開始試著從更深層面理解父親。
陳一心自小深受其父陳兆民“商業成功后不忘回饋”的教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離鄉四十多年后首次返回啟東。從上海到啟東,不遠的距離需要花費七八個小時,輾轉公共汽車、渡輪等交通工具。目睹家鄉的貧窮落后,陳一心決心做些什么。
當時,慈善捐贈并不常見,規模也非常有限,人們對于有規劃、可持續、以項目運作管理的“公益”概念幾乎聞所未聞。陳一心下定決心,以長期承諾代替一次性財務捐贈。
在童年好友趙景園與時任啟東市政協副主席倪國豪的幫助下,陳一心數次前往啟東走訪調查,并與當地政府官員和百姓進行當面交流和信件來往。
十多年間,根據考察結果,陳一心分別以父親、母親、舅舅等家人的名字命名,陸續在家鄉修建了六所學校、一家社區醫院,并承擔了啟東所需的大量公共建設。
自1991年起,陳禹嘉幾乎每年都會隨父親前往啟東。他為父親的慷慨而驕傲,也漸漸認識到除了金錢捐贈外,慈善事業更需要像父親那樣付出心力。
上世紀90年代,受政策變化、觀念差異、信息滯后等因素影響,陳一心那些廣受好評的慈善項目陸續遭遇變故,經歷了變質、產生糾紛乃至停辦的命運。2000年左右,倪國豪對陳一心表示,年紀漸長,無法繼續支持他在啟東的慈善事業。與此同時,許多啟東人仍然會給陳一心寫信,提出需求或者訴說抱怨。
陳一心無奈地問陳禹嘉:“我也不年輕了,是不是也到停下來的時候了?”
陳禹嘉卻覺得,父親這些看似失敗的慈善行動甚至比蒸蒸日上的家族企業更具意義。他將自己的想法拿到家族辦公室會議上探討,最終與所有成員達成一致:“一個家族真正的遺產是對于慈善的價值觀和在慈善事業中的實踐,這些更能夠定義其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與扮演的角色。洛克菲勒家族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陳禹嘉建議父親不要停止慈善事業,應該成立家族基金會,將慈善捐贈與公益項目系統化、專業化和策略化。對啟東的慈善項目進行反思總結后,陳一心同意了兒子的建議。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2003年10月,陳一心家族基金會(現“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成立。同年11月,陳一心溘然長逝,去世前簽署的最后一份文件是家族基金會的章程。
扎實前行
家族基金會成立后,陳禹嘉開始著手梳理與管理父親捐建的慈善項目。在啟東參觀一所小學時,陳禹嘉被看到的一幕所震驚:圖書館設在教學樓最頂層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大門緊鎖,書架落滿灰塵,即便為數不多的一些書籍也并不適合學生閱讀。
陳禹嘉聯系了啟東教師退休協會,通過聯合老師對學生的閱讀興趣進行調查再購置書籍的方式,在兩三所小學開啟了試驗圖書館項目。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學生們在圖書館外排起長隊,甚至有學生有計劃地列出自己的未來閱讀清單。
“我們不經意間跌入一個非常吸引我們的領域。”孩子們拿到書時興高采烈的表情讓陳禹嘉無比滿足。2007年,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以早期兒童閱讀為主題,在香港召開會議,圖書館學專家與全國近百名優秀教師、中小學校長等教育界人士,就“閱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閱讀與學習的關系是什么”等話題展開探討。
會后,來自安徽合肥的小學校長陳雪梅找到陳禹嘉,邀請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赴合肥考察。自此,從陳雪梅所在的小學開始,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在合肥推行了“好書大家讀”項目,免費為小學生提供優質兒童圖書。與此同時,通過圖書館老師培訓、圖書館軟硬件升級等方式,項目介入的一批學校成功把閱讀發展為學校核心文化,圖書館成為孩子們最喜愛出入的地方之一。
2012年3月,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與合肥8所學校共同發起成立“石頭湯悅讀(Stone soup)校園聯盟”,共同倡議建立“圖書館中的學校”。截至2018年2月,聯盟內共有26所學校,覆蓋近5萬名學生、3000名教師,900名家長參與圖書館志愿者工作。
除此之外,基金會的重點項目還有書伴我行(香港)項目與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前者開始于2006年,向香港地區的學校與社區中心資助圖書,提供培訓,倡導家庭親子共讀教育;后者于2008年舉辦第一屆頒獎禮,此后每兩年舉行一次,旨在鼓勵更多高質量原創中文兒童圖畫書的出版與發行。
從一開始,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給自己定下的宗旨就是,寧愿走得慢一些,但每一步都要專業且扎實。2002年籌備基金會時,陳一心家族邀請了畢業于多倫多大學公共社會學專業,在公益領域有著30多年工作經驗的辛西婭(Cynthia D'Anjou Brown)擔任咨詢顧問,主導設計家族基金會的規章制度與治理體系。辛西婭歷時一年設計出一本指導手冊,詳細地闡明了基金會的管理結構、運作流程、崗位職責,以及NGO的項目評審標準等。
“我們非常感謝你在‘撰寫食譜時提供的幫助,希望你能留下,享用你親自烹飪的這一道‘美味大餐。”基金會治理體系設計完成后,陳禹嘉誠懇地邀請辛西婭成為基金會理事會的一員。此后,以辛西婭為代表的非家族成員理事始終占據理事會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席位,為基金會理性專業的商討與決策環境奠定了良好基礎。
“理事會并不是一個蓋章過程。”陳禹嘉告訴《中國慈善家》,作為一家撥款和運作混合運營的基金會,理事會對于資助項目的評審過程非常嚴格。執行層向理事會遞交申請書前需要做到盡職調查,必要時理事成員也會參與其中。“即便如此,最后仍然有一定數量的項目申請被拒絕,或被要求重新評估。”
對陳禹嘉來說,扎實、專業、穩健是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的基本原則之一。“我們的宗旨是‘重深不重寬,致力于投入長期和可持續的慈善項目。”他說。
看見未來
陳禹嘉從15歲開始戴眼鏡,由此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包括自己,也包括他人。
“之前只能看見映入眼簾的一切,無從進行比較,戴上眼鏡后,才知道到底錯過了什么。生活了15年之久的世界一下子變得無比清晰,從此我絕不會想回到那個沒有眼鏡的世界。”
在此之前,陳禹嘉在尼日利亞度過7年童年時光。每隔一年回香港探親之前,母親都堅持帶陳禹嘉去看不同的歐洲城市。看過數不清的大教堂、墓地和博物館后,他很喜歡比較歐洲與非洲的不同:一個整潔,一個混亂;一個涼爽干燥,一個炎熱潮濕。
而在眼鏡給他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之后,陳禹嘉發現了另一個重要的不同:在發達國家,視力矯正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從商店或醫院獲得視力改善服務或產品十分方便;而在發展中國家,許多近視的人卻沒有眼鏡可戴。
“眼鏡700年前就被發明創造出來,現在全世界竟還有這么多人沒有辦法使用。”在于2017年底出版的《看見─讓已有七百年歷史的發明從今改變世界》一書中,陳禹嘉指出:“今天,大約有25億人(僅略低于中國與印度兩國人口總數之和)都處于視力不良卻無法獲得視力檢測或一副眼鏡的境況之中。”
他甚至認為,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忽視”之一,因為視力還關乎生產力、教育和性別平等。在家族基金會推廣早期兒童閱讀項目的過程中,陳禹嘉已意識到視力問題的重要性,及其被嚴重低估的現狀。“全世界各國政府已經建立了可持續發展目標,如果民眾視力低下的話,在2030年前這些目標沒有一個是可以實現的。”
不懈的關注為陳禹嘉帶來了變革的機會。2004年,他結識牛津大學原子物理學與激光專業的約舒華·席爾瓦(Josh Silver)教授,后者發明的可變焦鏡片可以供眼鏡使用者手動調節,滿足其對近處、中處和遠處的不同視野要求。
意識到這種眼鏡的巨大潛力,陳禹嘉與席爾瓦共同創立了擁有社會改善目標的商業公司Adlens,旨在建立可變焦鏡片科技的商業模式,更重要的是,解決發展中國家未被滿足的視力矯正需求。
在將Adlens作為一家商業公司運營的同時,陳禹嘉并不以傳統的、嚴格的財政收益標準計算回報,而是把為社會帶來的影響計算在內,積極尋求以慈善的方式將相關技術及專業運用在發展中國家。
這個簡單而直接的愿望,一開始卻讓他一度受挫。陳禹嘉曾經認為,既然擁有現成的技術,那么就可以將合適的產品賣給相關NGO或政府,幫助其從世界銀行等組織獲得資金支持之后,讓其獨立進行產品分銷。然而,這個模式推廣了整整兩年卻幾乎全無進展。
停下來分析原因,陳禹嘉意識到:“首先,世界銀行這樣的組織每天都會收到大量的申請,而在視力低下問題所屬的健康領域中,比這個更嚴重和迫切的問題數不勝數,因此視力相關項目根本無法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此外,成熟的視力改善市場模式中,配一副眼鏡價格不菲,培養一個眼科醫生更是投入巨大,這種模式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在NGO方面,視力領域的NGO大多把重點放在白內障、青光眼等眼科手術方面,而非視力低下問題。”
找到癥結,陳禹嘉決定采取先從單個國家入手,逐一突破的新模式。
2010年,陳禹嘉以“讓全世界存在視力問題的人都能及時得到視力檢測和保健服務,并購買能承擔得起的眼鏡”為目標,成立Vision For A Nation(VFAN)。考慮到非洲國家盧旺達面積較小、人口較少,且從首都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在6小時車程范圍內,VFAN首先在盧旺達著手建立全國性項目,引進視力評估體系,提供針對護士的短期視力檢測培訓,向國家健康機構提供低于成本價的可變焦眼鏡。
項目建立之初,盧旺達的視力檢測資源極為匱乏,平均每100萬人口僅對應1名專業眼科人士。經過7年努力,VFAN共培訓超過2700名護士,支持230萬盧旺達人得到視力檢查。在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英國國際開發部(DFID)、瑞銀慈善基金會的支持下,截至2017年底,該項目正式并入盧旺達國家衛生服務體系,覆蓋盧旺達全國所有15000個村莊和全國近1200萬人口。這意味著全部盧旺達國民都能及時獲得視力檢測并以合理的價格獲得眼鏡。
完成了在盧旺達的使命后,VFAN的下一個計劃是與英國慈善組織Vision Aid Overseas及加拿大防盲機構Operation Eyesight Universal攜手,將該項目引入非洲國家加納。
沿用在VFAN項目中積累的經驗,陳禹嘉在2016年創立了國際項目Clearly(“看見”行動),目標是在全球范圍內提升對視力低下問題的關注度與激發創新改善方案。目前,Clearly設立了創新競賽“看見視力大獎”(Clearly Vision Prize)與“看見實驗室”(Clearly Labs)。前者鼓勵人們探求各種方法解決視力問題,開發和支持從人工智能到智能手機診斷技術的突破性新技術;后者是一個計劃分布在四大洲九座城市的頭腦風暴項目,旨在囊括從企業家到政策制定者等所有利益相關方,共同孕育更具革命性、充滿未來主義色彩的想法。
Clearly計劃在今年4月舉辦的英聯邦峰會上舉行討論會,讓與會人士承諾推進解決視力問題,從而引起其他機構的重視。
“在當今世界,每個人,我指的是真真切切的每個人,都應該有權獲得清晰的視力。”陳禹嘉的表達有些浪漫:如果航天項目計劃在21世紀30年代甚至更早的時候將人類送上火星,他“希望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機會清晰地看到那一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