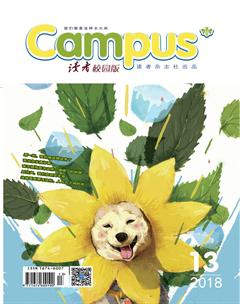父子書
趙松
“爸,這些書堆得都要倒了,你沒發現嗎?”兒子大搖大擺地晃了進來,往我的床上一躺,隨手拿起一本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這就是進化論?100多年前的了,都寫了些什么啊,你看完了嗎?”
“我一直都很奇怪,爸,你為什么總是喜歡看跟我們這個時代沒什么關系的書呢?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你才會去寫那些別人看不懂的東西。我覺得你寫這些已經證明自己了,為什么不去寫大家都看得懂的呢?你都不知道我們這一代人喜歡看什么書。”
“爸,你就不考慮考慮誰會看你的書嗎?我覺得這是不對的,你不能無視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個可能會讀你書的人,要是你不知道他們在想些什么,你怎么可能寫出他們喜歡的書呢?那樣的話你就永遠也寫不出暢銷書了,難道你不想讓自己的書賣得好嗎?你不想通過寫作讓自己變得很有錢嗎?那樣至少我們就不用租房子住了。”
“這本書太壓抑了!”他把我送他的那本厚厚的《奧尼爾自傳》丟到了一邊,“他后來活得太慘了,我都不想看了,真夠他受的,怎么會那樣?我還是喜歡能讓我振奮一點的書,不然的話我也會變得沒勁了……”
“你知道我為什么喜歡這本書嗎,爸?”他指了一下那本《極簡宇宙史》,“因為它簡單明了,不繞彎子,它用最平常的話告訴我關于宇宙的知識,看著很舒服,一點都不累,可以隨時翻開,隨便從哪一頁都能看下去,也可以隨時停下來,一點兒沒影響。我就喜歡它的簡單。”
……
從13歲到16歲,兒子經常會這樣跟我說話。每次走進我的房間,他都帶著審視的目光,仿佛頭一回進來似的,打量著周圍的書架,還有床上的那些書。他拿起這本,翻兩下,又換成另一本,再放下。他的問題永遠不是關于這些書的內容本身的,而是關于它們為什么會被我喜歡,因為他實在看不出它們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我已記不得他第一次質疑我的書是哪一天發生的事了,只記得當時他來到我的那個工廠園區里的工作室里,坐在沙發上,左右掃了幾眼那些書架,問我:“好像又多了不少書?”我點了點頭,半開玩笑地說:“它們將來都是你的。”他搖了搖頭:“給我?可我對它們一點興趣都沒有啊。”“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們捐贈給哪個鄉村圖書館。”我說。他出神地想了想,沒再說什么。
這個場景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時空落差。這意味著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已經不再是那個每天晚上迫不及待地要聽我講吉卜林的《叢林故事》,甚至逼著我編各種版本的狼爸爸續集,或是安靜地聽我講卡爾維諾的《意大利童話》的男孩了。他也不再是那個整天喜歡抱著那些關于恐龍世界的書看個沒完、把我跟他的角色分設在侏羅紀和白堊紀的男孩了。你還沒來得及把《一千零一夜》和《安徒生童話》讀給他,他就長大了——這種變化要遠比他從一米五五長到一米七二來得觸目驚心。他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隨意地挨靠著你了,而是在你每次出現在他面前時都會帶著某種警覺面對你;當你試圖摸一下他的腦袋或搭一下他的肩時他總是會下意識地避開。他會不失時機地表明態度:“我跟你一樣,喜歡獨自待在自己的房間里,不喜歡別人沒事就隨意進來。”聽到此言,我多少還是有些不習慣的,甚至有些尷尬。
為了理解他的這種變化,我不得不去想想自己在他這個年紀時是什么樣的狀態。那時候的我不明白,為什么我爸會把那套從朋友那里借來的線裝繡像版《紅樓夢》用布包裹著藏在衣柜里,好像唯恐被我們看到似的;家里沒多少書,除了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赤腳醫生手冊》,還有《東周列國演義》、林漢達的《春秋戰國故事》、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司各特的《愛丁堡監獄》和《艾凡赫》,以及半部《斯巴達克思》。而我感興趣的只有戰爭方面的知識,比如甲午海戰的細節、解放戰爭中每次戰役的情況。但印象最深的,卻是《斯巴達克思》里的角斗士和看臺上的那些羅馬高級妓女裸露的潔白如大理石的肩膀。當我把這些記憶講給他聽的時候,他一邊玩著魔獸游戲,一邊搖著頭說:“老爸,你想過沒有,要是那時候也有電腦和游戲,你還會看它們嗎?今天的孩子跟你們那時候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啊。你們喜歡的,不代表我們也要喜歡。”
不管我給他推薦什么書,他基本上都是拒絕的。他想要什么書,會把書名用QQ發給我,讓我去買。13歲時,他迷戀獵鷹的書,把能找到的都看了,而且還不止一遍,那時他只關注特種兵這個主題。接下來,《盜墓筆記》又成了他的枕邊書,差不多有一年多時間都在反復看。“那獵鷹呢?”我問他。“獵鷹?”他想了想,“他寫故事的能力還是挺強的,但語言太松散了,經不起反復讀……有段時間我寫作文都是模仿獵鷹,可老師覺得一點都不好。其實《盜墓筆記》也有類似的問題,只是題材更有意思一些。”問及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他不假思索地說:“那一定是《超越無限:邁克爾·喬丹人生哲理啟示錄》。”他特別喜歡喬丹的那段話:“如果我跌倒,那就跌倒吧。爬起來繼續前進,擁有一個愿景然后去嘗試……如果我成功了,那很棒。如果我失敗了,我也不愧對自己。”說完這段話,他還不忘批評我一下:“老爸,我覺得你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并不渴望成功。”在我表示不認同時,他補充道:“因為我看你整天除了悶頭看書和寫作,并沒有表現出對于成功的熱情。你只是寫你喜歡寫的,而不是別人喜歡看的。你寫得太小眾了……你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嗎?”
“不覺得。”我說。
“反正這是你的問題。”他搖了搖頭,“你回避不了的。”
“老爸,你能不能不那么寫我呢?”讀初二時,有一天,他看到同學轉給他的那篇我寫的《我們父子》。“我隨口說說的話,你也寫進去了,這真的讓我很尷尬,同學們都開我的玩笑,問這問那的。你應該問問我再寫,我覺得我跟你寫的我不一樣。這是不真實的。另外我跟你寫的《撫順故事集》里的那些人也不一樣,你不能用寫他們的方式來寫我,我也不是很贊同你那樣去寫他們,他們也有很多方面是你不知道的。”
我默默地注視著他,過了一會兒,我問他:“你看了嗎?”
“看了一半吧,”他晃了一下腦袋,“后面的就不用看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并不是要否定你的寫法,就是覺得還有其他的可能,只是你沒意識到而已……你還是太喜歡自己的那種寫法了。”
好吧,我無奈地聳了聳肩。他還沒完:“不過好像你們作家都不喜歡被別人批評。還有就是,我覺得你并沒有全力以赴去寫你想寫的東西,我看你經常都很悠閑,像沒什么事兒似的,今天去跟朋友吃個飯,明天又去參加個聚會,在家時也是沒完沒了地看書,你為什么不關上門寫作呢?我要是你就哪兒都不去。”
有段時間,他的同學都在看雷米的《心理罪》。他也讓我給他買來,厚厚的五大本。他看了幾天就放棄了,他把它們丟到角落里。在我拿起其中的一本翻看時,他問道:“老爸,以前,你剛開始看書的時候,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是哪一本呢?”
我想了想,說:“應該是《尼克·亞當斯故事集》吧,海明威寫的。”
“原因呢?”
“它讓我明白,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獨自游蕩有多么的重要。”
“哦。”他點了點頭,出了會兒神,沒再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