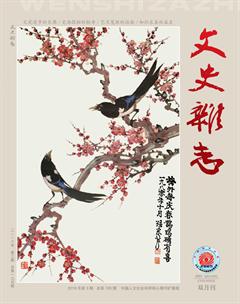古代的學與仕
王文承
學與仕的關系,是古代家庭、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敏感問題,直接牽涉到學習觀、仕宦觀和人生價值觀,牽涉到長達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對此,古籍中有不少論述,構成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品嘗研究。
一
1.學(讀書學習)與仕(從政為官),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古人求學或送子讀書,大體有兩種目的:第一種,不帶功利性質,旨在提高素質,完善自身,明理悟道,為善積德。古籍一再講:“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日就月時,學有緝熙于光明”“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讀書以明理,積學以富才”“欲知天下事,須讀古人書”“好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理自知”“書猶藥也,可以醫愚”“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裙”,以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于至善”“為善最樂,讀書便佳”“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學(讀書)與仕(做官)沒有多少聯系。
第二種,急功近利,讀書求學就是為了當官。所謂:“讀書都為稻粱謀”“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出仕先入學,讀書利萬倍”“賣金買書難,讀書買金易”“杖頭錢盡,俯仰何堪,論寒苦則書不可不讀;名場爭重,落魄人輕,論勢利則書不可不讀”,等等。古代大多數文人及其家庭的理想、動機、目標,就是讀書做官。在這種情況下,學與仕緊密相聯,合二為一。韓愈寫道:“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達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符讀書城南》)此詩把讀書的意義提到最高度(“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并指出:子孫能讀書為官者意味著飛黃騰達,為公為相為龍。反之,不肯讀書學習,就不能入朝為官,只能充當“馬前卒”,如同“豬”。
2.古籍提倡學以致用,經世致用。對此有兩種理解:其一,學以致用,首先和主要是將所學所學用之于治國理政、從政為官,故士(讀書人)必仕(從政為官)。《韓詩外傳》:“君子學之,則為國用。”子路:“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韓愈說:“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上宰相書》)其二,學以致用,其用頗多,既可以將所學用之于從政為官,也可以用之于修身齊家、為人處世。能修身齊家、與人和諧就是學問,而且善莫大焉。因此,士(讀書人)可以仕可以不仕。蘇軾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二者各有利弊得失,應做到“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指不仕)皆有節士廉退之行”。(《靈壁張氏園亭記》)宋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五人,杭州太守陳公作詩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雁也”。此詩以流水、高山、鴻雁、松柏為喻,講為官做人必須遵循的動靜出(出仕)處(不仕)之道。蘇軾《送杭州進士詩敘》評論:“士之求仕也,志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偽也。茍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道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他反對求仕者“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主張仕與不仕取決于“道”,決不能“視時上下而變其道”,還說“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這是相當堅定鮮明的立場和態度。
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曾國藩具有真知灼見,他認為讀書之目的和用處是進德修業。士子可以謀取科名仕宦,但不是讀書學習的主要目的和用場。兩相比較,進德修業是大者遠者,科名仕宦是小者近者。能否出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天意(科名前定),不應強求;自己應該力爭的是道德文章,孝悌齊家。這就叫“盡人事以聽天命”。他告訴幾位兄弟:“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至于“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無愧。”“總之吾所望于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悌為端,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科名之所以為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為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曾國藩家書》)
3.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當官究竟圖什么?出仕之目的何在?古代有四種觀點和主張:
其一,千里為官,只為吃穿。當官是為了獲取功名利祿,榮華富貴,有權有勢,升官發財,封妻蔭子,光宗耀祖。
其二,當官首先是為了謀利(取得俸祿,養家糊口,豐衣足食),與此同時也要行義(履職盡責,造福一方),把利和義、私與公結合起來,不可偏廢。
其三,當官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抱負,施展才華,建功立業,造福社會,報效國家(朝廷、社稷),因為朝廷中的宦位是最好的平臺、陣地和機會,讓讀書人(士)大有作為。歐陽修寫道:“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惜之所同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后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言下之意,仕宦之志有兩種,一種是追求榮華富貴,另一種是追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后者比前者更正確、更高尚。
其四,當官意味著策名委質,委身致命,將自己獻給朝廷,任由君王驅使,甘效犬馬之勞,而不再顧及自我和家庭。所謂“念念用之君民,則為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為賊臣”。這是一種極端的觀點和主張。
4.把讀書求學之目的與從政為官之目的聯系貫通起來思考追問。古籍提供的標準答案是:“讀書志在圣賢,為官心存君國。”(《朱子家訓》)文天祥就義前在衣帶上寫道:“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言下之意,讀書和做官,都應希圣希賢,成仁取義,忠君報國,憂國憂民。杜甫寫道:“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滿腹詩書,才華橫溢,志在獲取朝廷中重要職位,把皇帝變成好皇帝,讓民眾過太平日子。可是事與愿違:“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當作“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反映仕途艱難,命運多舛,命運捉弄人也考驗人。他還寫道:“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后兩句說自己只要不死,總想實現平生志向,意志何其堅定。杜甫還說自己“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也就是堅持忠君愛民。在不斷碰壁受挫之后,他說:“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最后兩句表示自己也不肯學堯時那兩位隱士的清高,不愿放棄、改變自己的初衷、志向、節操。這正是“讀書志在圣賢,為官心存君國”,而不是讀書志在仕宦,為官心系富貴。
與“讀書志在圣賢,為官心系君國”緊密相伴的,是“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起來是一個念頭”。(明·呂坤:《呻吟語·問學篇》)這個“念頭”,就是胸懷天下,以天下為己任。此“天下”,不僅是君王之天下,更是人民之天下。因此,無論讀書求學和從政為官,都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可以認為這兩句名言代表古代讀書學習和從政為官的最高境界,是學與仕的最佳結合,體現正確的高尚的讀書觀、仕宦觀和人生價值觀。它超越了世俗價值,擺脫了低級趣味,完全沒有私心雜念。問題在于,這兩句話說起來輕松容易,做起來沉重艱難,需要人們畢生為之奮斗。古代文場官場,不少人嘴上如此,外表冠冕堂皇,道貌岸然,內心深處和實際行動卻與此截然相反。他們學術、政術和心術都存在嚴重問題,類似于假道學、偽君子。明人呂坤寫道:“心術、學術、政術,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術要辨個真偽,學術要變個邪正,政術要辯個王霸。總是心術誠了,別個再不差。”“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視世之抵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唯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呂坤:《呻吟語·問學篇》)
5.讀書人(文人學士)入朝為官之后,還要不要繼續讀書做學問呢?大體有四種答案:
其一,當官后繼續堅持讀書做學問,“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仕與學、事業與文章(著作)相互支持促進,雙豐收。這是好傳統。
其二,擔負重任,公務繁忙,加之才智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顧一頭,于是舍學問文章而保事業和政績。
其三,一旦出仕為官,便不再讀書求學。他們對讀書學習毫無興趣,當年苦讀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那只不過是手段、梯子、敲門磚而已。韓愈寫道:“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于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韓愈:《上考功崔虞部書》)
其四,撰寫奏折呈文時,辦理政務遇到麻煩時,偶爾也翻書,從中找資料、依據、辦法;或借讀書作文吟詩賣弄風雅,裝點門面。
客觀地說,人的精力有限,既要從政為官干事業,又要讀書做學問寫文章(內含藝術創作),這是兩難。歐陽修寫道:“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于文章,而常患于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于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劉禹錫)、柳(柳宗元)無稱于事業,而姚(姚崇)、宋(宋璟)不見于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于兩得,況其下者乎!”(《薛簡肅公文集序》)與此同時,也要看到,古代確有一批杰出的文士出身的官員,包括歐陽修本人,從小就是“讀書種子”,始終熱愛知識學問藝術,讀書學習對他們來說,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樂生要素,雖然公務繁忙,仍然手不釋卷,筆耕不輟。他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既在官場政界大有作為,又在文壇藝苑大顯身手,仕與學相結合兩不誤。一旦告別官場,擺脫公務,便把主要心思精力用之于讀書做學問搞創作。他們的人生軌跡,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青少年潛心讀書——中壯年亦官亦學——老年致仕勤學。”在他們的心目中,公務有年限,讀書無年限;當官是一時的,問學是一生的。所謂“學不可以已”“學至于沒而后已”“朝于斯,夕于斯,數十年,如一日”“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偶有吟哦殊不倦,深知文字樂無窮”。他們真正做到了以學為生,學與仕互動兼顧,實現了五“有益”,即有益于從政為官,有益于文化繁榮,有益于自身完善,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教育培養子孫后代。
二
研究古代學與仕的關系,有必要重溫孔、孟、荀的論述,其中包含經典的學習觀、仕宦觀和人生價值觀。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講孔子。
1.孔子很重視學習,自己以學為樂,學而不厭,提出讀書人(士)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里仁》)而所以立者,仁義是也。《論語》記載,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言下之意,子羔質雖美而未學,遽使為官治民適以宰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范祖禹注曰:“古者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后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御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孔子主張先讀書學習然后從政為官,以免糊涂官害人,這是遠見卓識。關于學習目的,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憲問》)即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為己,指欲得于己也;為人,指欲見知于人也。孔子主張學習為己,即得之于己。用現代話講,這是提高素質,完善自身。需要說明的是,“學者為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見知于人,取悅于人,炫耀于人;另一種是幫助人,服務人,奉獻人。前者是惡習,后者是善行,應該加以區別。孔子曰:“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這個意義上講,“古之學者”即模范的學者,既為己又為人。《顏氏家訓》寫道:“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尤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字,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這段文章,是對孔子上述格言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再說,學者用自己的知識才能幫助人、服務人,這是利人利己的雙贏,如老子所說:“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孔子的門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子夏還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這也是孔子的觀點。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孔子雖然大力倡導非功利主義的或者說倫理主義的學習觀,但也有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他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衛靈公》)“三年學,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禮記·儒行》記載,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儒有……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儒有……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這是肯定儒者出仕為官。孔子還說:“儒……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通“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后祿,不亦易祿乎?”言下之意,儒者出仕為官應遵禮合義。《論語》記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子路》)所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出仕為官,而且是職位相當高的官。孔子主張士(儒)從政為官,是有前提和原則的。他一再重申和強調:“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憲問》)“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孔子還有一段話:“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確切的說是“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陽貨》),《四書章句集注》引胡氏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于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照此說法,則“士”有三種:志于道德者為丈夫,志于功名者為凡夫,志于富貴者為鄙夫。這分明是對讀書一心為做官者的鄙薄。
不可否認,孔子自己也想從政為官。他積極主動地參與政治,不辭辛勞地游說諸侯,必聞其政,欲謀其位。《論語》記載,子貢問孔子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罕》)他還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吾將仕矣。”(《陽貨》)《呂氏春秋》記載:“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所見八十余君。”《孔子家語》記載:“孔子適鄭。或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焉……累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嘆曰:‘如喪家之狗,然乎哉!”但孔子求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貪圖功名利祿、榮華富貴,而是為了行其道——以仁義治天下。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在教學上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這是崇高的思想品德。蘇軾寫道:“仲尼圣人,歷試于天下。茍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后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后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賈誼論》)在蘇軾看來,孔子和孟子從政為官,決不是志于富貴,也不是至于功名,而是至于仁義,即務引其君于道,以仁義禮樂等治天下、濟蒼生。
2.孟子對讀書學習講得不如孔子多,他簡略地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四書章句集注》:“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讀書學習旨在明義理,“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上》)孟子講得最多的,是仕宦(從政為官)之目的和原則。《孟子》記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滕文公下》)萬章問:“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孟子曰:“事道也。”(《萬章下》)在孟子看來,“士”或者說“君子”讀書學習是為了明道,從政為官是行道,伺候君王是事道,學與仕皆統一于道。孔子對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乎!”(《論語·述而》)《四書章句集注》:“圣人……其行非貪其位,其藏非獨善也。”孟子對孔子的話加以發揮:“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下》)他斬釘截鐵地說:“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告子上》)“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萬章上》)孟子和孔子一樣,把仁義道德看得比仕宦和生命更重要,“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3.荀子認為,在學習上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二者具有不同的目的(志向)。其中,“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一可以為法則。”“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君子之學,“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其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后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勸學》)言下之意,讀書學習之根本目的是進德美身,成賢成圣,與仕宦無關。荀子也贊成讀書人從政為官,他自己也出仕。但他認為,當官必須走正路,靠德行取位。“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后就也。”“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于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儒效》)荀子有一句名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修身》)他把官位(富貴、王公)看成身外之物,主張重道義、修志意而輕外物。對待官爵與對待學習一樣,也有君子和小人之分,結論是:“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修身》)。
在學與仕的關系上,孔、孟、荀基本觀點一致,他們都主張學以增其智、益其德、致其道、美其身。從總體上講,學不為貧,但有時也為貧。學者(讀書學習的人)可以仕,也可以不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仕意味著“達”,不仕意味著“窮”。達則兼善天下,建功立業;窮則獨善其身,安貧樂道。君子先學而后仕,學而優則仕。君子之仕也,決非貪圖榮華富貴,而是以道勸君(君主),道濟天下。官爵權勢,君子視之為身外之物;非其道而得之,君子不處也。
三
深入研究古代學與仕的關系,不能不高度重視科舉制。對此,學者們存在爭議。
1.科舉制始于隋、唐,發展于唐、宋、明、清,清末廢除,運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蘇軾指出:朝廷官員“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后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宋代)出于科舉。”(《蘇文忠公全集》第五)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繁多,最受重視的是明經、進士兩科,尤其是進士科。進士考試,試詩賦、帖經、實務策五道。武則天執政時重在詩賦取士。考試成績前三名獲狀元、榜眼、探花的稱號。據資料,有唐一代,科舉考試登進士科6646人,得人最盛。然而進士科最難考,每一百人中不過取一二名。民諺:“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是年輕的。所以,考取進士比作“登龍門”。關于科考,明代規定:先經童試——無論年齡大小,取得功名之前須經童試考取秀才,始有功名。次為鄉試——每年八月在省城舉行一次,也叫大比。中試者稱舉人,第一名為解元。然后會試——鄉試后第二年春在京城舉行,中試者稱貢士,第一名為會元。最后是殿試——此乃科舉制的最高級別,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人,第一、二、三名稱狀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分別錄取若干名。
2.科舉制為眾多士子開辟了一條從政為官的大路,備受其青睞。他們講“人生至樂事”有三,其中之一就是“金榜題名時”。一旦科考中第,命運立即改觀:“十年人謂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韓愈《送陸暢歸江南》寫道:“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夸映秀士群。鸞鳴桂樹間,觀者何繽紛。”如果不幸名落孫山,那就下次重來,一考再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可見其吸引力頗大。科舉制首先是一種選任官員的制度,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文官考試制度。較之以前的世襲制、察選制、九品中正制等,是一大進步。它第一次撇開了血緣、門第、出身、家世等先賦性因素,而將無法世襲的文化素養或者說學問,作為官員錄用的基本標準,從而更新了官員的成分結構,提高了官員的基本素質。從隋唐到明清,多數政治家都是科舉中人。科舉制為朝廷選拔錄用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韓愈、王安石、包拯、歐陽修、蘇軾、朱熹、辛棄疾、文天祥、海瑞、張居正、曾國藩、林則徐、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嚴復等。科舉制下應試,除了娼、優、隸、皂、罪戶子弟外,一切人原則上均可公開報考。其最大優點是開放、客觀、公正,在考試成績面前人人平等,成績優良者被錄取。即使是最貧賤家庭的子弟,也能通過正常的競爭程序而被擇優錄取,入朝為官。在明代,有“科舉天下之公;科舉而私,何事為公”之說。科舉制還意味著“學而優則仕”“學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學”,從而鼓勵朝廷和民間重學。這有利于文明進步。
不可否認,科舉制也有缺陷,如一考定終身。蘇軾指出:“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也不已太遽乎?”(《應詔集策略》)加之選士主要看文章才學,士的品德在考場上難以識別,這與任人唯賢的原則存在差距。更大的問題,是考試作弊,包括考生作弊和考官作弊屢禁不絕,歷來為人詬病。再說,士子在禮部考試中第后,不會立即委任官職,還需經吏部審查考核,有一段待命補缺時間,甚至有進士出身后二三十年待選的情況發生。禮部可以循私舞弊,吏部更可以循私舞弊,這種現象極大損害了科舉制的聲譽。
3.在學與仕的關系上,科舉制最大之弊(副作用)是使讀書學習之目的、意義和內容被扭曲。科舉考試的內容和題目,大都依據儒家經典,如五經、四書之類。眾多士子,確切地說是考生,他們讀圣賢書,只是為了應考中第,結果有意無意地使儒學異化為謀取官位的工具。說得嚴重些:科舉制使儒家仕途通而孔孟之道亡。在這種制度、機制的作用下,形象地說,在科考這根大棒的指揮下,讀書人變成趕考者和求仕者,他們心目中只有科舉——為科舉而讀書學習,按照科舉的要求選擇讀什么樣的書,根據猜測的若干考試題目花大量精力去搜集資料寫文章,包括應試對策之類。從此,“讀書→應舉→中舉→出仕為官”成為人生正途。古圣先賢諄諄教導的“古之學者為己”“君子之學也美其身”“讀書志在圣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等至理名言,被忽略、遺忘、拋棄。朝廷官場和民間流傳的是這樣一些說教:“讀書最為貴,可以登甲科”“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柳屯田勸學文》:“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司馬溫公勸學歌》:“勉后生,力求誨,投明師,莫自昧。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室中若未結親姻,自有佳人求匹配。”《王荊公勸學文》:“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書顯官人才,書添官人智。”宋真宗《勸學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還有一首廣為流傳的《勸學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而相天下,窮則善其身。白日莫閑過,青春不再來。窗前勤苦讀,馬上衣錦還。”明代顧炎武批評說,眾多士人“自其束發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鐘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日知錄》)。
4.關于科舉制扭曲讀書學習之目的、敗壞學風政風的問題,古籍中有不少批判性論述。韓愈的《答呂毉山人書》:“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識形勢,善侯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蘇軾寫道:“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于世,而詩賦幾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擬進士對御試策》)到了明清,主要考八股文,號稱“文章舉業”,遭人詬病。明代綠竹閣主人《續菜根譚》寫道:“讀書人,最不齊,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華,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圣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里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高背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晦氣。”《曾國藩家書》寫道,科舉考試,“此中誤人終身多矣。”“若再扶墻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為趕考而寫出的詩文,鮮有佳作。“若說考試,則需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為榮,則意淺矣。”梁啟超帶有總結性地指出:“宋太祖開館輯書,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制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間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制漢人。……試觀今日所以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為未足,而又設為割裂截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入于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遑及他事。”(《中國積弱溯源論》)
清人吳敬梓著《儒林外史》。魯迅稱作者“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在書中,作者借遲衡山之口說:“而今讀書朋友,只不過講學舉業,若會做幾句詩賦,就算雅致的了。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借杜少卿之口說:士大夫們“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里”。書中馬純上(馬二先生)對蘧公孫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須做的……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倘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指八股文)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那‘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賢弟,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講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說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是什么‘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馬二先生對“舉業”這番議論,是對科舉制透骨的揭底,差不多被所有文學史著作所引用。可以認為,科舉制上述缺陷弊端,是它后來被取消的原因。實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已經積淀為一種文化傳統。至今,它對讀書目的、學與仕的關系和學風文風官風以及人生價值觀的惡劣影響,并未因其已被廢除而消失。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