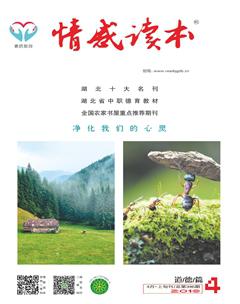北大情侶堅守58年,為中國留住千年文化遺產
蛋蛋姐
相戀在未名湖,相愛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他們共同走過了人生的58年,不僅成就了一段曠世奇戀,還用生命守護住了中華民族的千年敦煌。
他們在北大一見鐘情,但是因為工作,不得不相距兩千多公里分離了整整23年。然而,他們卻從來沒有一天想過要分開。23年后,丈夫放棄自己的事業,和妻子相守在大漠敦煌,就在那里,他們用高科技為中國守住了千年的文化遺產。
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初相識
1959年,在北大圖書館里,有一江南女子時時出入,21歲的年紀。她叫樊錦詩,來自繁華大都市上海,父親是清華畢業的工程師。受父親的影響,她從小讀三國、品水滸,聽音樂、看電影,沒事再逛個博物館,潛移默化學了考古。還有一個男孩叫彭金章,來自河北農村,人非常樸實,同樣學考古,同樣愛鉆圖書館。
于是,在圖書館,他們時不時就來個偶遇。老實的北方男孩,遇上婉約的江南女子,話自然很少。只是,彭金章這個老實小子,總是早早地到圖書館,在旁邊幫她占好位子,她來了也就悄悄坐下,心照不宣,默默無言。愛情就這樣生根發芽。
1962年,懷著對敦煌的無限向往,樊錦詩到敦煌去實習,她被這里徹底震撼了,精美的敦煌壁畫,被稱為“東方維納斯”的雕塑。數百個洞窟里囊括了中國從前秦到元代1000多年的幾乎所有雕塑和繪畫藝術。然而,洞窟里的畫再美,洞窟外的現實生活還是讓她整個人驚呆了。沒有電燈,水又咸又苦,黃沙漫天飛揚,她的人生走過了24年,從沒有想過在北京上海之外,居然還有這樣一個世界。更讓她難受的是,晚上上廁所要跑好遠,有一天晚上她想上廁所,一出門就看到兩只綠綠的大眼睛正瞪著她,那難道是狼?樊錦詩趕緊關上房門,一晚上憋著尿,瞪著天花板直到天亮。第二天才知道,原來那只是頭驢。
生活條件艱苦,再加上水土不服,樊錦詩整個人一下子就虛了,好不容易堅持到實習結束回到北京,她心里想的是:再也不要回到這里來了。校園愛情是甜蜜的,可是大多都逃不過畢業即分手的命運。
珞珈山下,敦煌大漠兩相離
1963年,樊錦詩畢業了,她最愛的人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漢大學。然而,敦煌研究院卻寫信到北大要人:當初一起來的四個實習生全部都要。樊錦詩的父親一下子急了,他給學校寫了一封長信,讓樊錦詩轉給領導。沒想到的是,樊錦詩卻默默地攔下了那封信,因為她還記得初見敦煌,仿佛聽到千里之外的召喚,讓她去保護敦煌。
于是她說:同意去敦煌。同樣學考古,這個彭金章深愛的姑娘,他自然理解,也就默默支持了她的決定。不過,二人約定,三年之后,她就去武漢和他會合。情侶分別兩地,但他們各有自己的江湖。
在敦煌,樊錦詩全身心都傾注在莫高窟上。在武漢,這所中國著名學府里,考古依然是一片空白,彭金章一心籌建考古系。他們各自忙著工作,閑暇時候偶爾鴻雁傳書。一年后,好不容易等到假期,彭金章趕忙千里迢迢奔赴大漠敦煌去見他心愛的姑娘,但他怎么都無法相信眼前這個“野姑娘”是昔日那個一口吳儂軟語婀娜婉約的江南女子。西北狂風的野,漫天砂礫的土,就像刻在她身上一般。他滿是心疼,卻只能戀戀不舍地回到武漢,等著她的歸來。
然而,與戀人相約三年期滿,樊錦詩卻因故沒能走成。同事朋友開始勸彭金章再找個新的女朋友吧,天涯何處無芳草啊。這個憨厚的男孩只是笑笑:我等她。樊錦詩默默感動著。1967年,探親假來了,樊錦詩奔赴武漢。在珞珈山下,他和她終于成了婚,接著她便匆匆趕回敦煌。
此后,便是三年之后又三年。樊錦詩和彭金章,一個在敦煌,一個在武漢,開始了19年的漫長分居生活。1968年,樊錦詩有了孩子,本想到武漢生產,沒想到孩子早產了。接到電報后,彭金章挑起扁擔就往敦煌趕,坐汽車轉火車再轉汽車,兩千多公里,等他到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快一個星期了。小小的嬰兒光著身子,裹在樊錦詩的大衣服里。從小衣食無憂長大、初為人母的她,哪里知道怎么帶孩子啊。慌亂、脆弱、無助,看到彭金章,她禁不住嚎啕大哭。彭金章滿是心酸,一心一意照顧她。可是孩子還沒滿月,他就不得不趕回武漢。
在武漢大學里,中國的夏商周文明考古正在等著他。在敦煌的大漠里,樊錦詩要工作,還要帶孩子。于是她每天用被子把孩子圍在床上,然后出門去上班。一下班就著急忙慌往家趕,只要聽到孩子的哭聲,她一整天揪著的心就放下了,因為這說明孩子安全。
可是有一次她一進門,孩子居然躺在煤渣子里,五六個月大的孩子,臉都被刮花了,樊錦詩難受到想哭。彭金章也心疼啊,他把孩子接到武漢,讓樊錦詩安心投入敦煌。再后來,他們有了第二個孩子,兩人卻依然兩地分居。彭金章又把孩子送到河北農村的姐姐家。
漫長的時間,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每日遙寄相思。老二5歲的時候,樊錦詩去接,一個小孩站在門后,樊錦詩徑直路過進門。當彭金章的姐姐說:你沒見你兒?樊錦詩這才發現,她居然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識了。當孩子喊出“媽”的時候,她的眼淚止不住地嘩嘩流,這是她第二次流淚,依然因為孩子。
千年敦煌,莫高窟下永相守
樊錦詩和彭金章覺得真的不能再這樣了,家人要團聚啊。若以武功來論考古,那樊錦詩便是敦煌派,獨家武器莫高窟;而彭金章則是武大派,絕門秘籍夏商周。在各自的江湖里,她是絕世高手,他是門派創始人。
當他們倆要動搖的時候,周圍的人就不淡定了。敦煌研究院三次派人前往武大,為了留住樊錦詩,他們想把彭金章調至敦煌。而武大也不甘示弱,同樣回敬三次,他們想要說服敦煌研究院放樊錦詩去武大。幾年間,大戰三個回合,卻終究是沒能分出個輸贏。
1986年,領導終于批準,樊錦詩可以離開。23年前的約定,整整遲到了20年。按理說,該喜極而泣啊!樊錦詩卻猶豫了,因為莫高窟病了,墻上的壁畫一點點脫落,照這么下去,沒多久就會被徹底毀掉。這是樊錦詩守了23年的敦煌,是中國人歷經十個朝代,花了千年建設的全世界的古文明博物館啊!她的整個青春,她的全部夢想,都在這里。她說:倘若敦煌毀了,那我便是歷史的罪人。她小心翼翼地向他傾訴心聲,沒想到他非但沒有生氣,只回了一句,看來我得過去跟你膩在敦煌了。
的確,時至今日,他一手建立的武大考古系已經良好運轉,即便他擅長的是夏商周,但是他決定自廢武功前往敦煌。他笑說:人們說她是敦煌的女兒,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
1987年,莫高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他們開始尋求國際合作,專業的團隊技術來了,溫度、濕度、風沙,經過重重檢測后,他們花了多年的時間,在石窟之外建起了防沙屏障,病害終于有了好轉。
一點點熟悉這個地方,彭金章發現,莫高窟的北區,在學術研究上竟然是一片荒漠,因為難出成果,但缺了北邊,怎么能算完整的莫高窟呢?于是,曾經自廢武功的他,拿出了自己帶隊考古的看家本領。他像個民工頭一樣開始帶人地毯式清理洞窟,這千年的無人洞窟,塵土厚得不像話,干凈衣服進去,分分鐘就變成個泥人。他說: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擤出來的是黑的,口罩一天換幾個都是黑的,咳個痰也是黑的。但是他卻絲毫不覺得苦,還得意地跟人炫耀:進了洞窟,用鼻子就能聞出這個洞是不是曾經存放尸體的。
就這樣,他篩遍了北區的每一寸沙土,把有編號的洞窟從492個增加到735個。他挖出了景教十字架、波斯銀幣、回鶻文木活字……其中,回鶻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實物。他從石窟中出土了大量漢文、西夏文、蒙文、藏文、回鶻文、梵文、敘利亞文的文書,這些中國的古文明很多早已失傳。他說:這是完整意義上的敦煌遺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繁華都市到大漠敦煌,本是為她而來,沒想到他卻意外愛上了這里,也踏上了他人生中最輝煌的階段。
與此同時,樊錦詩的人生也開啟了新的階段。1998年,60歲的她從前任手中接過擔子,成為敦煌研究院的院長,彭金章自然是全力支持她。然而莫高窟越來越出名,狂熱的游客們一批又一批到這里朝圣,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最后,人們的呼吸都會對壁畫造成傷害。
他又站出來和她一起,和國際組織反復研究,得出了洞窟的游客承載量:每天不能超過三千人。然而,這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幾乎所有到那里的人都是不遠千里,你總不能把游客拒之門外吧。
于是,她決定做出敦煌電影,而他永遠都是站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那個男人。此后,游客服務中心建立,電影《千年莫高》和立體球幕《夢幻佛宮》上映,游客看完電影再進洞窟,參觀時間一下子縮短了,承載量也多了起來。然而,就像人會老去一樣,即使莫高窟修建了一千年,即使它是人類的藝術寶庫,它也終將消逝,且永不再來。但是樊錦詩說:敦煌最終是要沒有的,什么時候呢?我希望它還能存在1000年。
于是,這個年近八旬的小老太太產生了一個偉大構想:為每一個洞窟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彩塑建立數字檔案,利用數字技術讓莫高窟“容顏永駐”。而他,自然是帶著欣賞全力輔助。
2016年4月,網站“數字敦煌”上線了,30個經典洞窟4430平方米壁畫。曾有外國人說: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而今,不必去敦煌,全世界的人們只要點擊鼠標,就可以進入洞窟游覽。網頁是全景漫游體驗,每一尊佛像,每一個畫面,每一根線條,都無比清晰,比實地參觀還要來得真切。
敦煌莫高窟,我們民族的文化瑰寶,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消逝,我們無法也無力阻擋。而他和她卻拼著命也要賦予莫高窟新的生命,以影像的方式送到我們的子孫后代面前。季羨林說:這件事功德無量。在《朗讀者》節目上董卿說:他們這是“逆天”的舉動。
可就像莫高窟終會消逝一樣,人也總有一天會油盡燈枯。而她知道,在莫高窟北區的塵土中,工作了多年的愛人離這一天已經很近很近。他們的門前種著幾棵李廣杏,他們會一起摘杏子,然后就像對待自己的孫子一樣,拉著來訪的學生一起吃。他們收養了好多流浪貓,在午后的陽光下,他們總是在院子里一起喂它們,大家都叫彭“貓司令”。
其實,節目組曾很多次邀請樊錦詩,但是她都拒絕了。她說自己很忙,她說她不喜歡接受采訪。可是有一天,編導極其興奮地說樊錦詩答應了,董卿問為什么,編導說:據說樊院長的愛人喜歡看我們這個節目。敦煌研究院院長,一輩子要強的樊錦詩在一旁重重地點頭:他在電視里看見可能高興。
也許是完成了最后的夙愿,就在節目播出后不久,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離世了,在他去世的前一晚,首屆飛天搖滾音樂節正在敦煌舉辦。
火樹銀花不夜天,那一晚,絢爛的煙火照亮了整個沙漠,那似乎是對他一生成果的肯定,也似乎是在預示著這場告別。
他在她背后低調了一生,這最后一次,他依然選擇低調。遵其生前遺愿:一切從簡。千萬人在難過,敦煌在難過。而最難過的大概是她。
相戀在未名湖,相愛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他們共同走過了人生的58年,不僅成就了一段曠世奇戀,還用生命守護住了中華民族的千年敦煌。
我們生活的社會,有時喧囂浮躁,有時底線沉淪。微博熱搜換了一茬又一茬,卻不知,真正的愛情,從來不會在網絡熱搜上。它是生活中的一蔬一飯,是異地時的問候和思念,是艱難時的包容和守護。它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們倦怠卻又無比熱愛的生活中。所謂的完美愛情,不過就是:我認準了你,便再也沒有想過別人。
汪國偉摘自《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