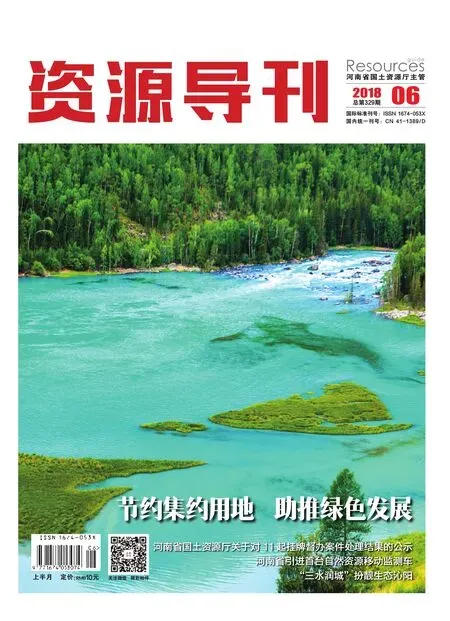【“漫話土地”之二十六】地發千祥草木興
文l景志剛



沒有什么比松柏,更能體會大地的厚重;沒有什么比草木,更能感受水土的恩澤。縱然大地可以孕育萬物,那隨風搖曳、顧盼生姿的一枝一葉、一花一果,永遠是地平線上最美的風情。
從楊柳依依的江南水鄉,到玉樹瓊枝的北國冰城;從桃李芬芳的陽春三月,到梅竹傲雪的數九寒冬……形形色色的植物,不僅妝扮了神州大地,更蘊藉著千年歷史文化的余韻流香。
土生萬物,地發千祥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自文明的曙光映入這片古老的東方大陸,土地創造生命的概念便深深烙印在華夏先民的頭腦之中。“土者,吐也。”正如這漢字中的“土”,形象地勾勒出一顆種子拱破泥土、吐出嫩芽的畫面,古人對“土生萬物”的理解,首先便來自于植物。百花斗妍、萬木爭春,人們感嘆大地的活力、生命的色彩;麥浪滾滾、稻谷飄香,人們感恩土地的饋贈、生活的豐足;花開花落、草木枯榮,人們感悟天地的造化、生死的輪回……
土地生草木,人類食五谷,植物無疑是連接人與土地的橋梁和紐帶。早在原始部落時代,人們以采集、漁獵為生,飲食所需的野果、野菜均直接取自于土地。但由于靠天吃飯,一旦出現災情,便不得不舉族遷徙,人與土地、植物之間難以建立持久親密的聯系。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人們開始在固定的土地上耕作。土地的肥沃與貧瘠,決定農作物產量的多少,決定全家老小的饑寒或溫飽。于是,以五谷為中心,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地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由此形成。
也許是植物與土地的關系過于緊密,以至于遠古的華夏先民們直接將植物作為土地的象征而加以崇拜。“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社。”古時的“社”,即指土地神;這里的“叢社”,便是以樹木為社,依樹立壇或壇上植樹,取其萬物生長于土的意涵,作為土地神明的代表進行祭祀。依照慣例、習俗,不同的朝代或族群,社樹的種類不同,“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甚至不同的類型和功能,所用的社樹也各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為槐。”
草土之道,各有谷造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植物根系于土地,地理環境的影響顯而易見。古人對此進行過深入研究,很早便有“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的說法。
地形異,草木異。《周禮·地官》記述,西周時掌管土地事務的大司徒,將全國土地分為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種地形,“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其中,山林“宜皂物”,適于生長櫟、栗等可供染色的植物;川澤“宜膏物”,適于生長蓮、芡之類結子多的植物;丘陵“宜核物”,適于生長梅、李等有果核的植物;墳衍“宜莢物”,適于生長豆科有莢角的植物;原隰“宜叢物”,適于生長禾、谷類叢生的植物。
地勢異,草木異。《管子·地員》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并舉例說明地勢對植物的影響:荷葉比菱生長得低,菱比水蔥生長得低,水蔥比香蒲生長得低,香蒲比蘆葦生長得低,蘆葦比小蘆草生長得低,小蘆草比蔞蒿生長得低,蔞蒿比馬帚生長得低,馬帚比艾蒿生長得低,艾蒿比薛荔生長得低,薜荔比益母草生長得低,益母草比白茅生長得低。從水邊到陸地,這十二種草本植物“各有所歸”。
土壤異,草木異。“壤,柔土也。”各類植物所需土壤環境不同,土壤對植物分布有著直接影響。大禹平治水土后,將九州之土分為白壤、黑墳、白墳、斥、赤值墳、涂泥、壤、墳壚、青黎、黃壤等十類,各有宜生植物。“揚州、荊州,其谷宜稻;青州,其谷宜稻、麥;兗州,其谷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谷宜黍、稷;幽州,其谷宜三種(黍、稷、稻);豫州、并州,其谷宜五種(黍、稷、菽、稻、麥)”。

社樹崇拜
植草育木,保土固沙
漫山遍野的花草樹木,上承陽光雨露,下植良田沃土,納山川之靈氣,奪天地之造化。植物與土地相生相伴、相輔相成,土地為植物的生長提供了營養和水分,而植物也反過來改變著土地的生態與環境。
古人很早便認識到植樹種草對于保持水土、鞏固堤岸的重要性。西周設有“掌固”一職,專門負責“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向齊桓公建議興修水利工程,提出:“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沿河兩岸種植柳樹,被唐代詩人白居易寫入詩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至黃河東至淮,綠蔭一千三百里”,追憶當年的壯觀場景。
有清一代,朝廷更加重視水土治理。康熙皇帝為了治理運河,詔令“栽柳蓄草,密種菱荷蒲葦,為永遠護岸之策”。乾隆皇帝多次巡視永定河堤防,并以《堤柳》為題寫下五言詩一首,總結植柳護堤的經驗和作用,成為帝王詩中少有的“接地氣”之作:“堤柳以護堤,宜內不宜外。內則根盤結,御浪堤弗敗。外惟徒飾觀,水至堤仍壞。此理本易曉,倒置尚有在。而況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經過命補植,緩急或少賴。治標茲小助,探源斯豈逮。”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植物對土壤的保護與改良是多方面的。每當秋風蕭瑟,脫離了植物本體的枯枝、敗葉、落花、殘果,在完成了造物者賦予的使命之后,重新回到大地寬厚的懷抱,化作肥沃的泥土滋養新一代的花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白駒過隙。在這一秋一春之間、一枯一榮之際,植物有了土地的根,土地有了植物的魂,草木回到了它最初的起點,生命實現了又一次的輪回。
春華秋實,寄情天地
植物孕育于土、生長于土、凋零于土、銷殞于土。在古人的心目中,植物與大地根脈相連,以至于常常將自己對土地、家鄉乃至親人的情感,寄寓于植物身上。因而,在漢語的語境中,一些植物便被賦予特殊的地域或人格意義。
桑梓之地。“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桑樹和梓樹是古代最常見的樹種,與人們的衣食住行關系密切。桑葉可養蠶,桑果可食用和釀酒;梓樹的嫩葉可食用,梓皮可入藥;桑木、梓木既可制造器具,也可用來燒制薪炭。“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人在房前屋后植桑栽梓,子孫懷念先輩,對其所栽植的桑樹和梓樹心懷敬意。桑梓之地遂成故土的代稱,后世也常以“造福桑梓”“功在桑梓”來形容對家鄉的貢獻。
椿萱并茂。椿樹為一種落葉喬木,相傳壽命很長,“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古人以椿來比喻父親,期盼父親如大椿一樣長壽。萱草為一種草本植物,又名忘憂草。“萱草生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古人出門遠行前,在母親居住的堂階下種幾株萱草,以免其惦念游子,故以萱比喻母親。“椿”“萱”合稱代指父母,常以“堂上椿萱雪滿頭”形容白發蒼蒼的父母,而將雙親健在稱為“椿萱并茂”。
桑榆非晚。“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田間地頭、村落農舍,桑樹和榆樹十分常見。每當夕陽西下,長長的日影斜照在桑樹、榆樹之間,與晚霞輝映的地平線構成一幅炫美的圖畫。古人感于此情此景,遂以桑榆借指日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東隅與桑榆相對,分指日出和日落。“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桑榆一詞由物及景、由景及時、由時及人,后成為晚年的別稱。
“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無私草木春。”遍覽中華文明史,品味華夏風物卷,感悟菊梅之凌霜傲雪、蘭竹之淡雅高潔、松柏之堅韌挺拔、蓮荷之冰清無瑕……冀神州沃土如春風化雨、欣欣向榮,如草木之興、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