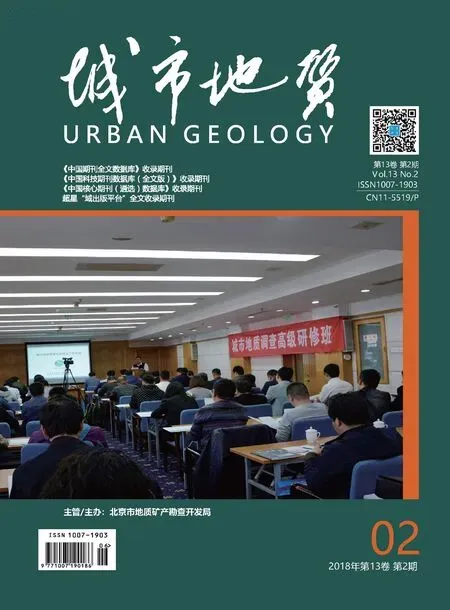城市地質學理論研究
鄭桂森,衛萬順,劉宗明,王繼明,于春林,徐吉祥,李小龍
(北京市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北京 100195)
0 引言
當今世界城市發展朝向都市經濟帶、城市群、經濟發展帶等新的城市空間組織形式,歐美發達國家城市發展已達到后期(竇金波,2010)。根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公報,我國城市化率已達57.35%,城市發展進入中后期,城市區域化發展形成城市群、城市帶,內部職能明確、分工合理、互為補充、協同發展。2015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了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人口最多的地區,要以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為目標,繼續在制度創新、科技進步、產業升級、綠色發展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加快形成國際競爭優勢,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發揮其對全國經濟社會的重要支撐和引領作用。
幸福、和諧、宜居、低碳是世界城市發展的新理念(陳維民等,2015),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提出城市發展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和自然規律,特別是城市建設要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中共中央批準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年)要求,北京建設政治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和諧宜居之都。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城市發展要體現五位一體的高標準要求。城市快速發展為人們帶來了美好生活,同時也引發了多種環境問題。在可持續發展理念引領下,我國城市發展在迅速崛起的同時,更加注意生態環境良好、和諧、宜居,城市功能由生產城市型向生產、生活、生態和諧“三生城市”轉變,城市與鄉村、人與環境進入共生、共享、共榮的“三共”和諧可持續發展狀態(竇金波,2010)。為此城市發展各階段都注意對地質資源環境供給與約束能力水平的考量,保證城市發展地質安全成為主題,形成以資源環境承載力作為規劃科學的核心依據。以地學為平臺的基礎支撐作用更加突出,城市地質學理論研究尤顯緊迫。本文旨在拋磚引玉,提出城市地質學理論體系,與大家共同探討。
1 城市地質學定義
“城市地質”一詞最早由加拿大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80年代引入我國,定義為“研究在城市地區或潛在城市化地區資源環境對城市發展的保障與約束以及城市發展對資源環境的負作用,為城市規劃、建設服務的學科”(孫培善,2004),由此而引發的各項工作稱為城市地質工作。
城市地質學是研究城市與地質環境關系及互相作用的學科,是地質學與城市科學交叉而產生的邊緣學科(中國地質學會城市地質研究會,2005)。20世紀90年代末,全世界城市地質工作內容、領域、服務對象發生了深刻變化,涉及地學、社會、規劃、建筑、管理、生態等多專業領域,城市地質工作服務于城市發展全過程。站在城市發展地質安全高度,城市地質學可歸納為在城市發展影響的地球淺層系統特定范圍內,系統研究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為城市發展提供的地質資源、環境保證與約束程度以及城市發展對地質資源環境的影響程度,提高城市發展地質安全保證程度的學科,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工作,更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精準表達。
城市地質學自建立伊始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國內外蓬勃發展,對城市規劃建設、運行、防災減災、優化環境起到了支撐作用,成為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地位。
2 城市地質學國內外發展
2.1 國外發展
城市地質學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至60—70年代以美國地質學家C.A.Kaye 在1969年所著的《Geology and Our City》和國際公認工程地質學家R.F.Legget 在1973年編著的《Cities and Geology》為代表的城市地質學著作,創立了城市地質學科。
美國高度重視地質填圖工作,城市規劃區域一般開展1∶2.4萬基礎填圖,地質填圖突出表示巖土的物理性質,對于特殊地段采用1∶4800填圖,在居民區采用1∶1200~1∶480比例尺填圖,用以解決城市資源利用、環境問題和地質災害防治(楊新孝,1986)。美國在上世紀末開展了1∶2.4萬國家地質填圖合作計劃;建立了“城市整體化決策支持系統”,將最新數字化的國家滑坡概略圖與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國家氣候概圖疊加,編制出國家滑坡災害態勢。通過互聯網,將顯示有降水高異常區和潛在滑坡發生區的綜合研究成果公布于眾,為政府和公眾減災防災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歐洲多數國家都十分重視環境地球化學調查工作,這是環境研究的基礎工程。英國在20世紀90年代開展了城市三維結構研究,支持尋找地下水資源和地鐵工程建設(Johnson et al,2008)。特別是對London clay的研究工作為倫敦地鐵運行保證了地質安全(Clayton et al,2001)。德國20世紀90年代將城市地質工作重點轉向環境調查研究,在城市及其周圍地區開展環境地球調查、污染調查評價、監控及治理等項工作,建立了地學與行政管理綜合數據庫,支持政府決策。Alaimo等(2000)用松針作為生物指示劑來研究意大利巴勒莫市土壤環境中金屬污染情況。意大利羅馬地區用電阻率層析成像技術探查未知地下空間或隧道(Fasani et al,2013)。
亞洲國家開展城市地質工作相對較晚。日本由于地質背景條件特殊屬地震火山災害多發國家,政府高度重視地質災害防治,日本在20世紀60—70年代將地質災害防治列入法律條文,使國民對災害防治有高度認知和行為自覺,同時政府對污水處理高度重視。印度政府為解決德里地區土地重金屬污染問題,研究了區域內重金屬污染的空間分布、范圍和類型,為政府決策提供支撐(Kaur et al,2006)。Chae等對韓國首爾市地鐵隧道滲漏水的水文地質條件和地下水化學進行調查評價,研究地下隧道對城市當地地下水水位及水質的影響(Chae et al,2008)。
國外城市地質工作已延伸到水土環境調查評價、地質災害監測,在工作方法向精準、定量發展,GIS、RS、GPS,地質方法信息技術融合使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歐美大多數國家已將地質工作列入法規層面予以保證,國外城市地質工作在調查、評價、機理研究和實際應用上開展的十分突出,取得大量實用性成果,在保障城市可持續發展中,城市地質工作發揮了基礎支撐作用。
2.2 國內發展
1985年天津地礦局翻譯出版美國萊格特《城市地質學》,將城市地質學概念引入我國;2004年孫培善(2004)出版了《城市地質工作概論》,提出了城市地質工作定義和主要工作任務,指出了城市地質作用的特點;2005年王秉忱、王學德主審,李明朗、劉玉海主編的《中國城市地質》(中國地質學會城市地質研究會,2005),對城市地質主要任務、研究內容、城市地質與其他學科關系做了概要論述,搭建了城市地質學的合理框架;2008年北京市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出版了《北京城市地質》系列叢書,提出了“城市地質為核心,保障城市地質安全”的城市地質工作方針和建設地質資源環境安全系統和地質安全信息平臺的戰略布局,建立了淺層地溫能學科理論;2013年中國地質調查局程光華等系統總結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天津、廣州6個城市地質工作試點成果,出版了《國家城鎮化地學保障——中國城市地質調查叢書》,系統詳細地闡述了城市地質與可持續發展關系,城市地質工作的主要思想、工作任務、工作方法和技術要求,對城市地質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衛萬順(2007)根據北京城市工作的實際,提出了城市地質工作要堅持理念發展模式,保障城市運行安全必須建立非正常情況的地質安全防控機制。鄭桂森等(2016)對城市建設過程中城市地質進行了研究,認為城市地質工作是城市規劃建設中的基礎支撐。李烈榮等(2012)闡述了中國城市地質工作的主要進展,認為在理論體系上逐步完善,逐步形成以保證城市地質生態安全為主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論目標,推崇尊重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實現社會經濟在地質環境容量允許質量良好前提下的加快發展,特別要加強地質結構三維建模、地質災害風險管理理論研究,建立地下水、土壤污染評價理論體系。呂敦玉等(2015)研究了國外城市地質工作的主要成果,提出城市地質學已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具有特定的任務和工作內容,以城市區域地質結構為主要研究對象,將獲得的資料用以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提出在基礎調查、主題填圖、綜合研究三個層面開展城市地質工作。姬廣義等(2005)對城市地質工作與基礎地質工作關系進行了闡述,提出了基礎地質是核心,城市地質是具體應用的理念。金江軍等(2007)認為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重大地質問題研究,應用現代技術方法信息手段使城市地質學從“定性”向“定量”轉變。韓文峰等(2001)對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地質作用做了闡述,認為城市發展中引發的各類地質環境問題是城市地質作用的表現形式。羅攀(2003)認為人為物質流已經成為引起地殼物質運動的一種重要地質營力,深刻地改變著地球的表層系統。羅勇(2016)闡述了我國城市發展中引發了一系列地質環境問題,探討了綠色發展的對策建議。徐一帆等(2010)認為城市地質工作在生態城市建設要加強環境地質與地質災害監測,從根本上協調城市空間、經濟開發與地質環境的矛盾,實現可持續發展。武強等(2007)將我國城市地質環境劃分為五種類型,“三廢”問題、地質災害、水資源問題、氣象問題以及地震問題。
張秀芳等(2004)指出我國城市環境的主要問題,是地面沉降、地裂縫、巖溶塌陷和水資源短缺、城市固體廢棄物處置、特殊土等問題。李友枝等(2003)認為城市發展帶來地質環境問題主要是巖土體位移與邊坡失穩,水資源短缺、地面沉降、巖溶塌陷、地裂縫、城市廢棄物處置。魏子新等(2009)對上海城市地質環境主要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地質環境容量評價理論框架。彭衛平等(2005)從廣州市可持續發展、優化規劃、防災減災、地下空間開發、水土污染和綠色農業多方面論述了城市地質研究的重要性與現實意義。可見國內從大量的城市地質工作實踐中,提出諸多城市地質學理論觀點(衛萬順等,2016;李安寧等,2011;衛萬順等,2017),為城市地質學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綜觀國內外城市地質學及城市地質工作發展歷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重要論斷:城市地質工作是保證城市發展各階段的地質安全的重要基礎工作,城市發展地質安全是城市地質學研究的主題和根本任務,城市地質學理論研究尤為緊迫。
3 城市地質學理論的科學命題
城市地質學,是一門為城市發展服務的應用學科。城市地質學創立以來的國內外發展經歷,都體現著鮮明的應用性特征,同時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理論探討,而系統梳理城市地質理論工作較少。在當前城市地質工作良好機遇到來的時刻,用可持續發展理念考察城市地質工作,圍繞城市發展地質安全,主題明確城市地質學工作理念、方法、體系、工作內容、基本理論顯得十分重要。所謂城市發展的地質安全是指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因地質資源環境因素的變化或人類活動影響下發生變化造成的地質資源與地質環境安全問題,保證地質安全是規避問題和處置安全危機事件的行為。
3.1 城市地質學基本理論概述
可持續發展理論是城市地質學的指導理論,可持續發展是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的全面發展是要義。城市的發展是實現人的發展時空載體,城市地質工作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是保證城市發展的全過程地質安全,這不僅是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精確表達,更是城市地質學理論研究與城市地質工作永恒主題,城市地質學所有研究工作都圍繞這個主題展開。城市發展依賴于地質資源和環境提供物質、能量、空間和納污保證,實現城市地質安全命題要回答三個科學問題,一是城市選址區域的安全性、可行性,這是生存發展的基本依據;二是城市選址區域發展的規模上限問題;三是幸福、和諧、宜居、低碳發展的平穩性問題。這三個問題只有在地學平臺上開展研究工作才能做出科學答案,以地學為平臺開展區域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回答選址可行性、安全性問題;開展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研究工作,回答城市發展規模上限的約束問題;開展城市地質作用研究,回答城市向幸福、和諧、宜居、低碳發展,在發展中規避自然災害,實現城市安全發展問題。
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三個科學問題催生了城市地質學理論。城市地質學研究的三個科學問題是貫穿于城市發展的初期、中期、后期、反城市化時期全過程,不同時期研究內容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城市地質學研究的核心內容是地球淺表層巖石圈、水圈、氣圈、生物圈一定范圍內的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的基本特征、變化規律、成因機理、發展趨勢;經典地質學和現代地質學理論方法是城市地質學的基礎理論和基本方法。城市地質學研究需要不斷創新城市地質工作方法手段,提高獲取地質要素數據的速度、精度與可靠程度。
城市地質學研究成果服務于城市發展全過程。將城市地質對各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的研究成果融入城市發展整體決策支持系統之中,提供自然因素變化,危機信息防治、防災減災、趨利避害,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發展。城市地質學研究要從對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的調查評價、分類研究向成因機理、演化規律、發展趨勢轉變,研究地質要素發展突變的臨界閾值,在結構模型的基礎上建立預測模型,演繹分析城市發展過程中地質資源環境發展趨勢,實現危機預警并達到預報的程度,為城市發展中的危機預測、危機處置提供可靠支撐,提高地質安全保證程度。城市地質學需要綜合性、動態性、即時性的大數據,研究地質資源環境要素變化趨勢,預測并防范地質安全風險問題,提高城市發展安全保證程度。獲取數據的可靠方法是通過RS、GPS、inSAR、物化探、地質、實驗測驗,信息技術等各種方法手段實施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的監測工作,建立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監測系統是最基礎、最可行、最可靠、最有效的工作,綜上所述建立城市地質學理論體系如圖1所示。

圖1 城市地質學理論體系圖Fig.1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urban geology
3.2 可持續發展與城市可持續發展
1992年6月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環境發展大會上十幾個國家首腦共同簽署的《21世紀議程》中形成的全新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觀的核心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發展,其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是指發展過程中不破壞環境的平衡;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發展則是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和諧和區域人群的共同發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2001,設計了一個由58個指標15個主題和38個子題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為國家層面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和目標提供了一個健全的啟動平臺(李天星,2013)。中國科學院提出可持續發展關注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四個方向。根據系統論原理,將可持續發展的本質要素構成為整個可持續發展系統的“五個子系統”(牛文元,2012),即生存支撐系統—可持續發展臨界閾值,發展支持系統—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牽引,環境支持系統—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約束上限,社會支持系統—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組織識別,智力支持系統—實施可持續發展的調控能力與選擇能力。任何一個系統產生非合作性制約,都將直接破壞可持續發展,即突變的產生。其中與城市地質密切相關的是生存支持系統和環境支持系統,生存發展是臨界下限,環境支持系統代表可持續發展上限,這是具有基礎性作用的兩個約束系統。沒有地球淺表層環境系統不可能有人類存在,沒有人類存在根本不用談任何發展,所以地學是自然環境研究的基礎平臺,人是可持續發展的主體。
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指在一定時間、空間尺度上城市的增長及其結構變化,既滿足這代人現實需要,又滿足未來發展需求。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城市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人類發展與環境生態系統可持續性(楊振山等,2016),其中后兩項內容是城市地質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城市地質學引入可持續發展理念,圍繞城市發展地質安全主題,在城市發展的時空域內,從三個方面開展研究工作,一是研究地質資源環境為人類的發展提供的物質,能源,空間(土地)的數量、規模和品質;二是研究環境對人類活動產生的廢棄物的吸納能力,即環境自然恢復功能的能力;三是研究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引發城市區域地質作用規律和引發災害的風險。這三個研究方向構成城市地質學的核心研究內容,由此可建立城市地質理論:即城市區域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理論,重點研究區域資源環境對城市選址、功能布局的可行性;城市區域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理論,研究資源環境對城市發展規模、發展質量的供給程度和環境納污能力;城市地質作用理論,研究城市發展中城市表生地質作用的特征、規律,研究人類活動與自然和諧平衡協調程度,減少環境問題和災害發生,提高城市發展地質安全保證程度,實現可持續發展。
城市地質學的理論基礎是地質學理論,城市地質學三個研究方向上的各項地質因素研究的原理方法都是地質學理論和方法。三個研究方向本質內容都是以資源與環境要素為目標,區別是在城市發展不同階段對資源、環境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對資源環境評價研究指標、內涵、手段方法、數據形態、功能作用均不相同。城市地質學在實際工作中選擇適用的方法獲得實時的數據,研究地質因素的變化;對各項地質要素追求定量的描述,以提高成果可靠性、實用性,由此意義上講,城市地質學是對地質學理論的定量化發展與實踐應用的典范。
4 城市地質學基本理論
城市地質學是以地質學理論為基礎,以保證城市發展地質安全為目標,以地殼淺層巖石圈、水圈、氣圈、生物圈疊加區域為研究對象的應用學科,目的是提高城市發展地質安全保證程度。城市地質學要研究三個科學問題:一是城市選址可靠性、可行性問題,即人類生存底限問題;二是選中區域內地質環境容量的極限保障能力,確定城市規模上限問題;三是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保障問題。解決好這三個問題,保證了城市發展地質安全,城市就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三個問題必須站在地球淺層系統內統一考量,用地學理論為基礎方法手段開展城市地質工作予以解決,為此城市地質學必須開展以下研究工作。
4.1 城市區域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理論
城市區域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理論指在城市規劃區及影響范圍內對地質資源、環境主要因素開展系統性評價,確定區域資源環境對城市選址的安全性、可行性支持程度。該評價方法需要建立一套綜合性、定量化的評價指標體系,內容涵蓋地質資源條件和地質環境條件,其中地質資源包括水資源、能源、原材料資源、土地資源;地質環境條件包括區域地殼穩定性,巖土環境、水環境、工程地質條件和地質災害等。
我國已頒布的國家、地方、行業標準中對各項地質要素的評價主要以定性評價居多,指標定量化程度較低,而且部分評價指標不能全面反映評價對象演化趨勢,因此該項工作一是將評價體系中不夠完善的部分新設置了定量化指標,二是將部分指標評價由定性轉化為定量,三是修訂了部分定量化指標的定量分級標準。該評價指標體系體現出實用性、適用性原則,既能滿足對某地質要素的性質、特點、發展趨勢描述的要求,又能滿足各種功能應用需求(劉輝等,2017;鄭桂森,2017a)(圖2)。

圖2 城市區域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內容體系圖Fig.2 The evaluation content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for urban region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1)淺層地溫能資源理論
該理論屬于地質條件適宜性的能源專科理論,科學系統地回答了地殼淺層<200m深度的巖土體內的熱能是否為資源,受哪些因素控制和能否持續利用的問題。目前制定的技術標準、工作規范指導了這部分資源的評價與應用,取得了顯著的經濟、社會、環境效益。
(2)地下空間資源理論
該理論從地學角度定義了地下空間資源概念,是土地資源的向下延伸,具有資源的全部屬性。依據實際工作成果,系統建立了不同區域評價體系、評價方法以及安全監測體系,為地下空間資源科學利用奠立了基礎(鄭桂森,2017b),屬于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理論的專科理論。
(3)土地質量綜合地質評價構想
土地是地表某一地段包含地質、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多種自然要素在內的自然綜合體(黃宗理等,2005),土地的質量特征是這些要素的具體體現。從地質的角度對土地質量開展評價是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地質條件對土地質量影響表現在土地的基本組成的土壤成分,包含礦物成分、化學成分、養分;土地中含有地質資源包括水資源、能源、礦產資源等保證性資源;土地的地質環境條件包括水環境、土環境以及地質災害特征。將這些特征研究透徹,對土地劃分質量等級,確定土地的使用功能,以此作為土地利用規劃的基礎。具體實施由先進行單因素評價,再將各項單因素評價結果以一定方法疊合形成綜合評價結果,北京市正開展土壤地球化學組分評價試點工作。
這項工作中關鍵點是設置評價要素指標,這是此項工作可操作性、成果實用性的關鍵問題。在單因素評價中,評價指標包括決定性指標和輔助性指標。決定性指標對土地使用功能的區劃具有重要作用,輔助性指標可提高土地附加值。正確設置這兩項指標要經過深入的研究分析、高度的概括提煉,據目前經濟技術條件,活動斷裂的破壞力是不可抗拒的,規避是首要原則,因此活動斷裂發育地段不可用作建設用地,活動斷裂是土地質量評價的決定性指標。對建設用地具有一定性限制作用的因素,稱為限制性指標,利用經濟技術手段可以控制,如地面沉降、土壤污染等,必須研究這些要素的提取內容和表達方式,用于土地資源評價中。
在土地質量綜合地質評價中設置保障性指標和約束性兩大類指標。保證性指標是對土地使用功能具有支撐保障作用的指標,比如有益地球化學成份、優良的資源、優質的能源、充足的水資源等;約束性指標指對土地使用功能具有限制作用的指標;如有損人身健康的地球化學元素;人類活動形成的污染物,活動的地質構造,廣泛發育的地質災害等。在單因素評價基礎上,用適當的方法疊合形成綜合性評價結果,這個方法與程序正在研究中。
4.2 城市區域地質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理論
地質資源環境是城市發展的物質能量基礎和空間場所,科學評價地質資源環境對城市發展的承載能力是城市地質學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內涵包括兩大方面,一是物質基礎供給能力,重點是原材料生產能力和能源保障能力,包括土地、水、礦產、能源、食品、空氣等;二是空間場所的安全性,包括土地質量、水環境、地質生態環境的容量或環境納污能力,這是城市發展的前提條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普遍認可的資源承載力定義,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承載力是指在可預見的期間內,利用本地能源及其他自然資源和智力、技術等條件,在保證社會文化準則的物質生活水平下,該國家或地區所能持續供養的人口數量。
環境承載力是指在為維持一定生活水平前提下,一個區域能永久承載的人類活動的強烈程度,主要關注的是環境的納污能力和人類不損害環境前提下的最大活動限度(封志明等,2017)。資源環境承載力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涵蓋了自然資源、環境容量、社會發展強度、人的需求,以我國高吉善提出的生態環境承載力為典型,指生態系統自我維持、自我調節能力、資源與環境子系統共容能力及其可持續的社會、經濟活動強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數量。
資源環境承載力實質上是在一定背景條件下的極限能力問題。世界上多個國家、組織機構在開展研究工作(高湘昀等,2012;秦成等,2011;經卓瑋等,2014;汪自書等,2016;周璞等,2017;郭軻等,2015,劉明等,2017),但依然沒有取得統一的、公認的、可靠的、實用的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此項工作涉及的要素龐繁,指標動態變化復雜,在指標設定、統一量綱、評價方法等方法的選擇上也存在眾多難點;可以認為這是一項在復雜系統內、具有多個變量的方程組,無固定解,只要社會發展需求設定一個目標,就可得出一系列自然因素取值。只有人們能客觀的認識自然規律,根據科技發展水平能力設立需求,就可以達到資源環境與人的發展和諧統一。
城市地質學必須研究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城市發展提供定量化決策支持。在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研究評價中(圖3),關注以下方面才可取得適用結果。首先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是城市發展中涉及某一方面或幾方面的極限能力問題,必須與當地發展需求相結合;其次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是在開放的、復雜的、動態的系統中運轉的,必須運用系統的、動態的方法來研究;第三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既反映了人們對資源環境現狀的認識,又反映科技創新進步對資源環境利用新認識,隨著科技的進步,資源種類功能、環境容量是不斷變化的,必須用發展的觀念來研究;最后城市地質研究在區域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研究中要用創新的理念、動態的數據、系統論的觀點開展此項工作,重點在于適合區域發展的指標設定,可行的獲取方法和采用可靠評價流程,以獲得最終可靠數據支撐城市發展地質安全。具體說就是將地殼淺表層人類強烈活動區域的地質要素實施監測,建立監測站點,形成多個監測系統,運用實時的、動態的大數據結合判別方法獲取地質資源環境要素隨城市發展的變化規律,預測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變化趨勢,調控發展使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變化,使其始終在人類可控范圍之中,規避地質環境問題風險,提高城市發展地質安全保證程度,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

圖3 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內容體系圖Fig.3 The evaluation content of ge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4.3 城市地質作用研究
地球系統在不斷地運動著,地質作用無時不刻都在發生著,它是塑造自然的原動力。然而在城市區域的地質作用與自然環境中地質作用大相徑庭,城市區域的地質作用與人類活動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人類活動對地質作用產生著巨大影響,不但可造成環境問題,甚至引發地質災害,考慮到人類的特殊性,有文獻中將此類地質作用稱為人類紀地質作用(程光華等,2013;孫培善,2004)。所謂城市地質作用是指地質因素在自然營力與人為活動共同影響下的演變行為。
城市地質作用是在人類活動參與下的表生地質作用,主要包括人為影響下的風化作用、剝蝕作用、搬運作用、沉積作用、成巖作用等。城市地質作用表現在導致地質環境變化,引發地質環境問題,包括城市熱島效應、區域酸雨、霧霾、水體污染、土壤污染、礦山地質環境問題、地裂縫、地面沉降問題等。
城市地質作用顯著的特征之一是物質的人工搬運作用,羅攀稱之為人為物質流,它已形成地質營力,深刻改變著地球淺層系統。據統計數據,全球人為物質流35km3/a,主要搬運了的是化石燃料、礦產、建材的開采,而且全球每年平均有550 km3的地下水開采量。我國固體礦產開采造成了1150 km2地面塌陷(羅攀,2003)。城市地質作用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廢棄物排放,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是世界上城市建設規模最大的國家,據估計我國每年城市產出垃圾約為60 億t,其中建筑垃圾為24 億t 左右,已占到城市垃圾總量的40%(李平,2007)。物質的人工搬運造成了地形地貌改變,形成了“水泥森林”,廢棄物的排放導致了城市周邊環境污染和人為災害。
城市地質作用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人類活動改變了地質環境的物理化學特征,進而改變了自然的地質作用過程。城市化區域內城市建設使路面硬化,導致雨水向地下入滲屏障,在地表水匯流后沿設定的排水管道排入主泄洪渠,形成了人工河道;河流的剝蝕、搬運作用在城市地區不復存在;城市化區域內工業化加速發展排放的CO2、SO3、NO3等氣體在空中遇水氣形成酸與雨水降落;城市周邊人類廢棄物處置使水體、土壤遭受污染;城鎮人類污水排放使水體中有機物顯著高于鄉村;城市抽取地下水形成區域型地下水漏斗,使水位下降,表層土砂化,地下水超采嚴重時形成地面沉降、地裂縫災害;城市區域內人、機械排熱、地面反射等多因素形成城市熱島效應,造成市區內平均氣溫高于郊區3℃~5℃。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地質要素的變化超過一定閾值時,就會引發地質環境系統突變,形成地質災害。
由表1可知,在城市區域由于地表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導致了地質作用速度加快的特點,目前此項研究剛剛開始,尚未有確切數據證實加快的速率和形成產物的結構、特征,顯見的是形成了一系列的地質環境問題(韓文峰等,2001;羅勇,2016),這些問題的形成機理、演化趨勢、風險程度正是城市地質學研究的又一項主要內容。
5 城市地質學在城市不同發展階段中的研究內容
城市發展按城市化率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初期階段,城市化率10%~30%;中期階段,城市化率30%~60%;后期階段,城市化率70%~90%;反城市化時期,城市化率>90%(周毅等,2009)。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建設速度逐步加快,始終存在著對地質資源供給和對地質環境保證的需求,即資源、能源持續地為城市建設提供原材料和能源支持,環境持續地為城市建設提供空間、納污容量支持,這是城市地質學的兩個主要研究方向。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城市地質作用也開始悄然發生變化,逐漸演變為各種環境問題,影響城市地質安全。在地殼淺表層巖石、水、大氣、生物四圈構成的復雜系統中,各項地質因素在一定的閾值內對自身存在的系統運轉起著各自作用,處于相對平衡狀態,當其中一項因素產生突變時,就會造成子系統的崩潰,進而引發整個系統變化而帶來災害。城市地質工作就是及時掌控地質因素變化情況做出適當調整,保持整體平衡運轉,保證系統安全運行,實現城市發展地質安全的目標。
5.1 城市化初期
城市選址規劃可根據已有的區域地質調查數據開展選址布局。在城市化初期,工業化水平較低,人口聚集較慢,各項基礎設施建設處于起步階段,選址規劃工作是重要環節,選中區域的地質安全是核心要求,對研究區內地質結構、地殼穩定性、地質災害易發性及危險性做出評估,對建設用地安全性做出評價,對地質資源種類、品質、數量做出現狀評價和潛力評估,1∶5萬精度的地質成果即可滿足需求。
5.2 城市化中期
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空間規模擴張迅速,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功能布局逐步完善,需要準確可靠的地學數據,特別是地質資源、環境的保證能力和建設安全性保證程度,此時必須開展比例尺大于1:2.5萬的基礎地質調查和比例尺大于1:1萬的專項地質調查,并對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開展研究評價工作。對以土地、礦產、水、能源、地質環境等為主要方面的承載力閾值做出評價,同時對各種地質災害開展風險評估,對地質環境要素發展趨勢進行預測,為規避地質災害提供可靠支持,為政府規劃城市人口規模的上限、功能布局和產業結構布局提供參考依據。
5.3 城市化后期
城市發展趨于穩定,人類活動對城市區域的地質作用影響逐漸明顯,此時會發生各類環境地質問題,比如工業排放出CO2、SO3、NO3等氣體會形成區域酸雨;工業化過程中產生土地污染,人類生活、生產排污會形成水體中有機物持續增高至超標,形成劣質水體,形成水質污染;生產生活用水過度依賴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水壓降低形成泉水斷流,加快松散沉積物壓實作用,造成地面沉降,這一階段的研究重點在于人類活動引發的地質作用特征、成因機理、演化規律的研究,判斷發展趨勢,預測地質環境問題發生的時空規律,提出預警預報,減少或避免災害發生,重點開展對各類地質因素監測、模擬和試驗工作。
5.4 反城市化時期
在城市發展最高階段,城市鄉村基本無差別,人們對環境的需求程度極高,開始追求優美恬靜的田園生活,城市由區域集聚向四周分散發展。城市地質工作主要研究地質作用對環境的影響,趨利避害。重點開展各種環境問題的修復治理,創建優美資源環境。
5.5 城市地質學服務于城市發展全過程
城市地質工作貫徹于城市發展全過程,在不同的城市發展階段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發展各階段的建設工程實施與城市地質工作關系已有論述(鄭桂森等,2016)。
城市發展初、中期,城市選址、重大基礎設施選址、重大工程規劃建設必須以地質資源環境條件為基礎,根據適宜性級別和資源環境承載力約束確定城市功能布局、產業布局、人口規模和生活方式;城市區域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和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研究是主要工作。
城市發展后期,隨著城市化程度提高及工業化程度減緩,建設速度日趨平穩,城市安全運行和創造和諧宜居環境成為管理者主要工作目標,對自然因素變化特征、變化規律、變化趨勢的掌控和風險預測是保證城市運行安全的重要基礎支撐;城市地質學及城市地質工作主要是建立各項地質要素的監測體系,獲得即時的數據,運用數理分析方法和建模技術取得地質要素的變化趨勢和預測模型,設定臨界閾值,達到預警和預報的精度,為政府提供決策依據。
當城市化高度發展,進入反城市化時期,城市與郊區已無差別,人們追求環境優美、生活舒適成為最廣泛的需求,城市管理者的工作目標是創建和諧宜居、環境優美的城市生活空間,城市地質學研究重點理所當然地轉化至對由人類活動形成的各種環境問題的解決上來,主要是對環境修復與治理。具體工作是環境污染機理、趨勢的預測預防與克服方法的研究與實施,如對水環境污染修復、土壤環境的治理、大氣環境的改善等。
可見,在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城市地質學研究都是圍繞城市發展地質安全展開的,成果始終是城市管理者決策的最重要的依據,在城市整體決策支持系統中占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是保證城市發展安全的基礎性工作。
6 結論
(1)城市地質學誕生近百年來,各國開展了大量工作,為城市規劃建設、防災減災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國內外大量實踐證實城市地質學的根本任務和永恒研究主題是保證城市發展全過程的地質安全。
(2)在當代可持續發展論指引下,城市地質學是在地球淺表層巖石圈、氣圈、水圈、生物圈交織空間內,綜合研究各類地質要素對城市發展的保障能力與約束程度和城市發展對地質資源環境的負作用,提高城市發展地質安全保證程度的學科,是地質學理論的典范實踐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精確表達。
(3)城市地質學從保證城市發展地質安全出發,明確了城市地質學研究的三個科學問題,即城市選址安全底限問題、城市規模上限問題、城市發展可持續性問題,由此構建了區域地質條件適宜性評價、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城市地質作用研究三方面的城市地質理論體系。
(4)城市地質學三個研究方向支撐理論是地質學理論;城市地質學理論研究平臺是地質資源環境承載力要素監測預警平臺,基礎數據是變化的、動態的,數據的獲取是靠對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的監測來實現的;城市地質學理論方法手段和成果表達方式必須不斷創新,適應城市發展需求;因此城市地質工作在城市發展中期和后期必須建設地質資源環境監測體系,研究地質資源環境要素的變化規律、發展趨勢,創新生態環境修復技術,實現城市在幸福、和諧、宜居、低碳的良好環境中平穩發展。
(5)城市地質工作是貫穿于城市發展全過程的基礎性工作,是城市整體決策支撐系統重要的環節,具有無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