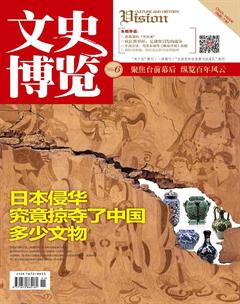“工人老大哥,吃飯用缽缽”
李鵬程
“工人老大哥,吃飯用缽缽”,這是孩提時傳唱的歌謠。歌謠中包含有兩個信息,一是工人們盛飯用的器皿是缽子,二是那個時代的工礦企業、機關學校,乃至農村都建有食堂。食堂大多采用甑子蒸飯,蒸飯的器皿就是缽子,或是大鍋煮飯,分飯時也用缽子來盛。
所謂缽子,其實均是些“瓦貨”,初期的缽子為黝黑色,非常粗糙,后期的缽子有些改進,感觀呈深黃色,再后來也有陶瓷的缽子,質地相對細膩了不少。缽子的容積有大有小,機關學校的缽子容量,一般為二兩、三兩,鮮有四兩的,而工礦企業一般為三兩、四兩,甚至半斤,鮮有二兩的,這與職業定額供應的糧食有關。
“四天八餐”的農村缽子飯
自1958年開始,中國農村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全國人民一個勁朝著共產主義的目標闊步邁進,旋后就是以隊為單位辦起了公共食堂,其口號是“吃飯不花錢,努力搞生產”。生產隊集體行動,社員們下工后統一就餐。隊辦食堂一般設在人口集中的自然村落,在堂屋里壘大灶,大灶上放置大鐵鍋,鐵鍋上疊甑子,甑子里放缽子。取下幾塊門板當案幾,灶里燒大柴,利用鐵鍋蒸汽煮飯。
做飯的過程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用竹甑、木甑蒸,甑子分若干層,用升子量米,依次倒入缽子里;一種是先煮大鍋飯,飯熟后根據定量的多少用秤稱好放入缽子里。分群體配額(16兩一斤),老人每天大約8兩米,婦女兒童12兩米,壯勞力接近16兩米。吃飯要登記,普遍實行兩餐制,一般早飯定在9點左右,晚飯定在下午3點左右,社員自嘲為“四天八餐”。大家一邊進行著集體勞作,一邊享受著食堂的缽子飯,熱熱鬧鬧過了近一年。

可是好景不長,因上年度政府號召搞建設,青壯年社員大多被抽去煉鋼鐵、修水利了,沒有精力及時收回糧食,翌年又遭受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口糧顯然就青黃不接了,全國開始進入“過苦日子”的時代,缽子飯隨之嚴重縮水。區區二三兩米飯何以抵擋住強體力勞動的折磨,何以填飽轆轆饑腸呢?于是有人便發明了“雙蒸飯”,即初次飯熟時,米粒不夠膨脹,于是在熟飯里再加些水,第二次蒸發飯粒膨脹,體積增大,成了滿滿一缽子。然而,吃下不久,肚子仍然空空如也,不得不上山找些野菜、挖些能吃的樹根來充饑。
“三兩米,用甑蒸,肚子餓了刨樹根,小孩吃了黃哼哼,婦女吃了不懷孕,農民吃了鼓干勁,干部吃了拉豬糞”,就是當年的真實寫照。從中也不難看出,當時社員對隊干部的意見不少,因為他們掌握糧食,且大多將親屬安排在食堂工作,雖然沒條件吃香喝辣,但“天旱三年,餓不到伙頭軍”,填飽肚子還是沒問題。其他社員就沒有這般福氣了,請假外出要停飯,偷懶違命要扣飯,忍饑挨餓過日子,乃至發生餓死人的事件。
因食堂缽子飯實在無法填飽肚子,于是挖的挖野菜,刨的刨樹皮。我祖父為了求生存,也發明了用鹽水湯來充饑的土方法,幾碗鹽水湯下肚,暫時緩解了饑餓。孰不知這是一種慢性傷害,不多久就遍體浮腫,直到腿肚子腫得有小水桶那么粗,醫生看了無奈,只能用銀針放水,不久祖父就離世了。
中央鑒于全國的實際情況,在1961年上半年宣布解散農村公共食堂,農村的缽子飯就此消失。
單位缽子飯
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國家對干部、工人的口糧實行定量供給。機關干部和教師、醫務人員一般每月27斤,鄉鎮干部每月32斤,工礦企業分工種定額糧食,一般在32斤以上,那些從事體力勞動的煤礦工人等,定額在45斤左右。機關、學校、工礦企業等單位,大多建有食堂,由司務人員統一到糧站購買大米回來,再由炊事員整成缽子飯。縣直機關一般實行三餐制,鄉鎮機關采取二餐制。雖然沒有農村那么轟轟烈烈,但持續時間長,并經歷過“過苦日子”、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三個階段。
在“過苦日子”的時代,機關干部的糧食指標縮減至24斤,那時,我跟隨父母生活在縣城,一起渡過了那個艱難的歲月。母親回憶說,因為大家吃不飽,干部也褪卻斯文,變成了“餓老蟲”。一次外婆來縣城看我這個大外孫,特意帶來幾個雞蛋,父親刻意放在角落邊,期為牙牙學語的我補充一點營養,不料被幾個“狗鼻子”叔叔發現了,繼而一搶而光,如果不是餓得不行了,他們絕對不會在孩子口里奪食的。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經常到父親供職的縣委、縣革委食堂蹭飯吃。那時的食堂,采用鍋爐蒸汽煮飯,聞著飯香,不由得垂涎欲滴。6人一桌,憑票就餐,一色的缽子飯,用的是公筷,舀湯用調羹。生活條件開始改善,桌子上有了兩菜一湯,每餐都還有點肉末。桌子旁邊雖然置有條凳,一些干部還是習慣站著吃,或靠近大門蹲著吃。吃完晚飯后,居住在縣委大院的叔叔們,一般圍著食堂對面的那蓬大竹林,看林中的鶯歌燕舞。當時感覺食堂飯菜美滋滋的,可惜在20世紀90年代機關食堂消失殆盡了。
我上中學時,學校有寄宿生,他們自帶大米和缽子,有些同學吃不飽,便悄悄通融炊事員,在缽子上放個紅薯什么的,后來被更多的同學所知曉,每到上甑時分,便有魚貫的隊伍去加餐。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工廠,吃的就是典型的食堂缽子飯。幾口大灶上,一排的方型木甑子,疊著有近一個人高,甑子寬有1.2米,每層0.2米,灶口燒著煤。一班小青工,自備筷子,捧著缽子飯,就著一菜一湯,吃得風卷殘云,有時心血來潮,煽動伙伴敞開肚皮吃他三四缽,害得炊事員莫奈何。每到星期六打牙祭,一小缽蒸肉肉香四溢,需要多出一角五分錢。
改革開放后翌年我上大學了,每月34斤米,在司務處兌換成飯票,其實還是吃的食堂缽子飯,只是盛飯的缽子換成了自帶的洋瓷碗,筷子變成了金屬叉子或調羹而已,從窗口排隊領飯菜。這時的菜肴漸漸豐富起來,一排排地擺在案幾上,有時還眼花繚亂,不知如何取舍,有段時間為了攢些生活費,還與同學合購五分錢的湯。校園生活幾年了,就是弄不明白“辣椒炒肉”和“肉炒辣椒”的真正區別。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工業材料的改進,工礦企業、學校食堂大多采用電力蒸飯,甑子已被鋁合金飯盆所取代。鋁合金飯盆分成多個小格子,蒸飯盛飯便不再使用缽子了。就餐人員不是自帶的精致碗筷,就是食堂提供的瓷碗,或金屬托盤,缽子飯就此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政府于20世紀90年代取消了口糧計劃供給,縣直機關的食堂隨之基本解散了,縱使那些沒有解散的食堂,也進行了改革,一般實行個人承包,每餐配有多個菜,有葷有素,講究營養搭配,菜肴花樣翻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缽子飯了。
進入新時期,不知是對過去生活的懷念,還是對自身營養的需要,大街小巷的酒家飯鋪又復現了缽子飯。雖然是缽子,但缽子質地考究,飯香菜美,與當年食堂時期的缽子飯相比,已經有了質的區別。
到了2012年,中央出臺了“八項規定”,大多數機關單位又恢復了內部食堂,采取鋁合金盆子蒸飯。年長的人卻發覺,雖然還是食堂,但沒有當年缽子飯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