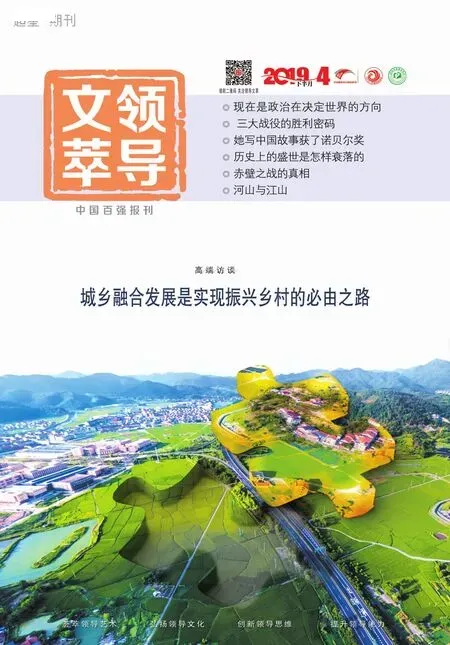中國為聯合國秘書長選舉“立規矩”始末
從秘魯的德奎利亞爾到埃及的加利、加納的安南、韓國的潘基文,再到古特雷斯,聯合國秘書長人選一般在各大洲間輪流出人擔任。世界各大洲都有份,而且一般不超過兩屆。鮮為人知的是,這一“規矩”是中國人創立的,它源于1981年聯合國秘書長選舉……
曾長期由西方小國占據
從聯合國成立直到1981年,共產生過4位秘書長。他們是挪威的賴伊、瑞典的哈馬舍爾德、緬甸的吳丹、奧地利的瓦爾德海姆。其中,緬甸的吳丹是因哈馬舍爾德飛機失事身亡,以副秘書長資格先任代理秘書長而后轉正的。由此可見,秘書長這個職位,長期以來一直由西方發達的小國占據著。35年間,他們占了24年,4任人選中,他們占了3個。
1981年,已擔任兩屆秘書長的奧地利常駐聯合國大使瓦爾德海姆宣布競選連任秘書長。這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不滿,他們認為這一職務不應老是由歐洲人擔任,并推薦時任坦桑尼亞外交部長的德·薩利姆競選聯合國秘書長。薩利姆是非洲統一組織推薦的候選人,他是一位年輕而有才干的非洲政治家,在非洲國家中威信很高,而且對中國十分友好。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時候,當年的薩利姆高興得在會場帶頭跳舞。
中國臨時更改投票策略
1981年第五任聯合國秘書長競選期日益臨近,我們是不是應該援引過去的慣例,對發達國家競選人先投兩次反對票,再轉而投贊成票?
對此,我(注:本文作者凌青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考慮了很久,下不了決心。但在聯合國秘書長的選舉中,中國必須及時表態,沒有時間拖,而中國的一票又很有分量,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看著中國怎樣做。
經過反復衡量,我逐漸形成了一些想法:競選人之一的薩利姆是中國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重要人物。他此次出來競選不僅代表他個人,而是受到非洲統一組織的支持,代表整個非洲。毛澤東曾經說過,是非洲國家把我們送進聯合國的,如果中國只支持兩次就轉向,顯得我們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國家,態度不夠真誠,不夠朋友。再說,聯合國秘書長的職位,已連續三屆為西方發達國家占有,而發展中國家屢屢競選失敗,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如不站出來說話,恐怕也不得人心。
當時,正是中美第三個聯合公報在進行緊張談判的時候,而談判進展并不順利,我們甚至準備在必要時,將大使館級別重新降格到聯絡處,因此,這時同美國鬧點矛盾,似乎也并無不可。
基于以上認識,我大膽設想:此次似乎可以反對到底,至少逼出第三人來競選,而此人一定來自第三世界國家,這就很有利。我把自己的想法在代表團黨委會上提出,有些同志有點遲疑,但沒有反對。我就給外交部寫了報告,后來外交部終于批準了,還具體指示對各個競選人應當如何投票。事后,聽說鄧小平也有“一否到底”的指示。這樣,中國的投票態度就定下來。
中美“角力”勢均力敵
西方媒體就紛紛預測,瓦爾德海姆會得勝,因為他得到美國和蘇聯的堅決支持。但是,中國方面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歷史的慣例已不適合今天的形勢了。第三世界國家再也不能容忍美蘇操縱聯合國最高行政人選的局面繼續下去。1981年10月27日和11月4日,安理會就秘書長人選問題進行了8輪投票。兩人分別遭到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美國否決薩利姆,中國否決瓦爾德海姆。選舉陷于僵局。
最初曾流傳一種說法,即認為中國對薩利姆的支持是有保留的,在看到薩利姆提名無望通過后便會相機行事,轉而放棄支持,使瓦爾德海姆“柳暗花明”。11月17日,安理會一天之內進行了8輪投票,由于兩人還是各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否決,因而都未能當選。
在經過20天的16輪投票之后,人們終于明白,中國這一回否決瓦爾德海姆動了真格。因而安理會大多數成員國再也不是死心眼地待在會場里,而是離開表決機器,到會外進行更多的活動,尋求打破僵局。
9名新候選人都來自發展中國家
12月3日,瓦爾德海姆首先宣布退出競選。5天后,薩利姆也作出了同樣的選擇。幾天之內,秘書長候選人如雨后春筍,紛紛登臺亮相,最熱鬧的時候竟達到9人之多,包括秘魯著名職業外交家德奎利亞爾在內,9名候選人的籍貫清一色屬于發展中國家。
12月11日,安理會舉行秘密會議,就候選人舉行第17輪投票,德奎利亞爾獲得了10票贊成票,因無否決票當選。
中國在聯合國的這一行動創造了一個先例。從此,聯合國秘書長人選就在各大洲間輪流出人擔任。發展中國家候選人也可和發達國家候選人一樣,涉足聯合國秘書長這一最高國際組織的最高職務,在此以前是很困難的,這應該說是中國的貢獻。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