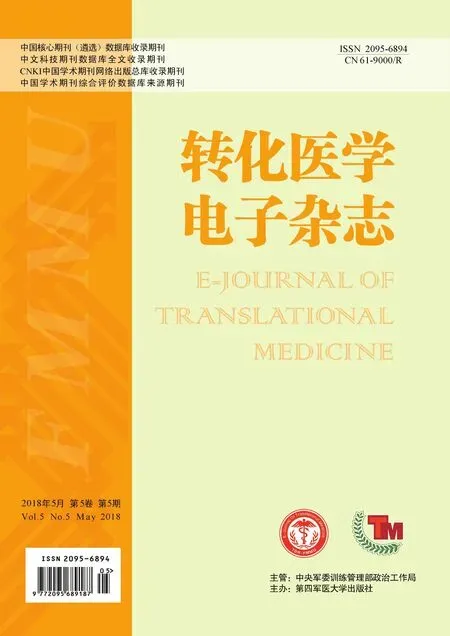椎基底動脈擴張延長癥中的CT與MRI表現
趙 輝,丁長青,余 磊 (江蘇省豐縣人民醫院:神經內科,影像科,江蘇豐縣700)
0 引言
椎基底動脈擴張延長癥(vertebrobasilar dolichoectasia,VBD),既往也曾命名為椎基底動脈迂曲、巨大延長擴張病、巨大基底動脈變異、梭形動脈瘤、動脈瘤樣畸形等[1]。VBD為椎動脈和(或)基底動脈血管異常延長、擴張、迂曲或成角為主的血管畸形,可伴或不伴動脈瘤的形成,文獻報道其發病率為0.05%~18.00%[2]。VBD起病隱匿,臨床表現復雜多樣且無特異性,主要由CT、MRI或DSA等獲得診斷,單憑臨床極易漏診、誤診[3-4]。 隨著 CT及 MRI成像設備在各級醫院的逐漸普及,對該癥診斷的文獻報道越來越多。現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至12月江蘇省豐縣人民醫院影像學診斷的28例VBD患者的臨床和影像學資料,旨在探討CT及MRI在VBD診斷中的應用價值。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至12月江蘇省豐縣人民醫院影像學診斷的28例VBD患者的臨床和影像學資料,其中男18例,女10例,年齡21~83(平均61.23±2.57)歲,其中<30歲 2例,30~40歲1例,41~50歲3例,51~60歲6例,61~70歲10例,>70歲6例。入院時主要臨床表現:頭暈20例,頭暈伴肢體麻木、步態失穩6例,頭痛18例(其中睡眠性頭痛1例),偏癱8例,面肌痙攣或面癱7例,飲水嗆咳6例,耳鳴5例,三叉神經痛4例,復視伴眼震3例,癲癇1例。部分患者有1種以上前述表現。既往史:高血壓14例,腦梗死13例,高脂血癥11例,冠心病6例,糖尿病6例,腦出血史4例,長期吸煙史5例,酗酒史3例。本組患者主要采取對癥治療。
1.2 影像學檢查及評價方法所有患者均有MRI及MRA資料,16例患者有多層螺旋CT資料(其中4例有CTA資料)。MRI使用飛利浦Achieva1.5T MRI設備,行軸位 T1WI、T2WI、FLAIR、DWI,矢狀位 T2WI序列,3D TOF法 MRA掃描;CT使用飛利浦 Prospeed16層及64層多排螺旋 CT機,平掃采用軸位5 mm薄層螺旋掃描,4例同時以4.8 mL/s的注射流率高壓注射器、肘靜脈靜注碘海醇行CTA檢查。由1位神經內科及2位影像科高年資醫師共同讀片,重點觀察異常擴張延長的血管累及區域,CT平掃所見,MRI各序列所見,MRA或CTA病變形態、寬度及長度,病變區域對周圍的壓迫及伴發病變等。
1.3 影像學診斷標準本組均符合目前廣泛接受的VBD診斷標準[1]。(1)擴張:椎動脈直徑≥4 mm,基底動脈直徑≥4.5 mm;(2)延長:基底動脈上段超過鞍上池或床突平面6 mm以上,或基底動脈長度>29.5 mm,椎動脈顱內段長度>23.5 mm;(3)迂曲:基底動脈橫向偏離超過起始點至分叉間連線1 mm或位置在鞍背或斜坡的旁正中至邊緣間以外;椎動脈任意一支偏離超過椎動脈顱內入口到基底動脈起始點之間連線10 mm。
2 結果
2.1 分布、形態及管腔大小28例VBD中,25例病變位于椎基底動脈系統,3例椎基底動脈及頸內動脈系統同時累及。CT平掃11例顯示基底動脈增粗、迂曲,其中7例表現為橋前池及橋小腦角區梭形或類圓形塊狀影(圖1A),局部可呈瘤樣擴張,4例基底動脈壁可見鈣化,其余CT平掃未見明確異常表現。CT增強(圖1B、1C)及MR所有序列(圖1D~1F)均可見基底動脈增粗、延長及迂曲,呈管狀或粗帶狀高密度或不同程度的流空信號(流空程度與血流速度、血流狀態、有無血栓形成等相關),2例伴附壁血栓者可見充盈缺損或附壁中高信號。本組15例向左右方向側方迂曲呈橫行“V”字形或“S”形,CT或MRI軸位圖像表現為血管側方移位超出鞍背或斜坡的側緣,可達橋小腦角池之內;本組上下方向折曲走行10例,表現為軸位圖像上在同一層面可見多個椎基底動脈血管斷面,基底動脈末端超出鞍上池,至第三腦室底部或以上,三腦室及腦實質可受壓;本組3例VBD同時可見側向及上下方向迂曲走行。CTA(圖1C)及MRA(圖1G)可全程顯示椎基底動脈的擴張、延長、迂曲或瘤樣擴張,本組擴張基底動脈直徑為4.8~13.5 mm,長度為30.2~34.0 mm。

圖1 VBD患者的CT圖像(男,46歲,以“頭暈”就診)
2.2 鄰近腦干受壓及腦神經受累改變CT及MRI上VBD所致的鄰近腦干受壓表現為腦干正常圓隆外形消失,變扁平,甚至內凹(圖1)。常規CT多難以直觀顯示顱神經的受壓。在MRI諸序列上,顱神經多呈中等信號,常規MRI序列結合MRA,可較為準確評價VBD所致的顱神經壓迫情況。本組7例與面神經較為密切,5例與聽神經較密切,5例與三叉神經密切。
2.3 伴發病變本組20例伴后循環供血區梗死灶,部分病例為多處、多發梗死(急性6例),其中位于腦干15例,小腦11例。伴丘腦梗死4例(急性1例),兩側基底節多發腔隙性梗死12例(急性3例);兩側放射冠、半卵圓中心白質區小血管病7例;伴枕葉陳舊性梗死3例;基底節區陳舊性出血、后遺軟化灶形成3例;合并腦積水2例。
2.4 CT及MRI平掃診斷率本組16例有CT平掃資料者初診準確率為69%(11/16),MRI平掃初診準確率為93%(26/28)。
3 討論
VBD的病因尚不明確,與動脈彈力層發育不良相關的先天性代謝性、遺傳性異常,以及男性、高齡、肥胖、高血壓、高脂血癥、糖尿病、長期吸煙及酗酒等后天因素可能參與其中[1]。本組年輕患者可能與先天因素有關,年長者合并腦血管動脈硬化的危險因素較多,臨床合并梗死者(71%,20/28)多見。有作者[5]應用軟件對VBD患者的MRA進行流體力學分析,推測VBD最先累及部位可能為椎基底動脈匯合部及基底動脈下段,低壁面切應力所致的管壁退化及相應區域存在的高壁面壓力可能與VBD的發生及發展有關。一組對 VBD血流動力學的研究[6]提示,VBD病變血管出現血流速度減慢、血管硬化加重,可能為該類患者卒中高發的原因。另有對后循環缺血患者椎基底動脈走行異常的研究[7-8],提示椎動脈顱內段優勢動脈的存在與基底動脈迂曲具有相關性,且基底動脈迂曲方向與優勢椎動脈相反,VBD可引起后循環缺血。
目前,較為廣泛接受的VBD臨床分型,多根據臨床表現、受累血管的分布范圍、形態大小及對鄰近組織器官的壓迫情況而分以下諸型[9]:①無臨床癥狀型,多見于年輕患者;②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型,可表現為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10];③腦梗死型,主要為后循環供血區梗死,本組最多,與文獻報道的腦干最多、腔隙性者多,且延長擴張不伴迂曲者更易單發梗死相近[11];④腦干受壓及腦神經綜合征型,以第Ⅴ、Ⅶ對腦神經最易受累,其次為第Ⅲ和第Ⅷ對腦神經。本組神經受累也較多,年輕患者無癥狀或癥狀相對年長患者較輕。文獻報道面神經受壓明顯者可致半面痙攣[12];近期報道的顯微血管減壓術治療VBD所致的三叉神經痛取得較好效果,也證明VBD可致神經卡壓[13];⑤出血型,以蛛網膜下腔出血最為多見[14];⑥腦積水型。但臨床上,部分患者可見2型以上表現。另外,近期有文獻[15]報道VBD可致睡眠性頭痛(本組1例)。
目前,DSA仍是診斷VBD等顱內血管病變的“金標準”,但其有創、風險相對較大且費用較高[16-17]。 多層 CT 血管造影(CTA)可應用最大密度投影(MIP)、容積再現(VR)、多平面重建(MPR)等后處理技術全面觀察椎基底動脈,對其起源、數目、行徑、窗式等,并對病變區域長度及寬度進行精確測量[18]。目前1.5T以上MRI設備的MRA成像已經比較成熟,其應用于顱內動脈成像清晰,無目前常規CT的后顱窩偽影影響,無需使用含碘對比劑、無電離輻射等優點,成為目前診斷VBD較好的檢查手段。但血管壁鈣化在MRI及MRA上無信號而難以顯示,且當病變血管走行過于迂曲,MRI常規圖像及MRA血管內局部渦流形成,MRI上可呈混雜信號,MRA可為無信號區,有時難與血栓形成鑒別[19]。 有學者[20]根據椎基底動脈全程血管走行將VBD分為S型(全程2次反方向轉折)、U型(一側椎動脈跨越至對側匯合成基底動脈,基底動脈迂曲,偏離中線走行)及螺旋型(呈螺旋狀轉折,程度多較重),其中S型多無癥狀或表現為腦干壓迫癥狀,U型以神經卡壓為主要表現,螺旋型常致后循環缺血癥狀。本組結果也與之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各級配備CT設備的醫院,每天均有較高比例的患者行顱腦CT檢查。因此,認識CT平掃征象對提示進一步檢查及診斷均非常重要。CT平掃顯示基底池內有等或稍高密度的擴張基底動脈,部分較大者可呈梭形或類圓形塊狀影,局部可呈瘤樣擴張,部分管壁可見鈣化。本組16例有CT平掃資料者初診準確率為69%(11/16),診斷率并不太低,與注意病史、重點觀察有關。部分患者因顱底偽影、軸位狀態下難以準確觀察基底動脈形態的變異及血管與周圍腦組織相近的密度,故經常不能提示病變[21]。而動脈血管在MRI多數序列上呈不同程度的流空,因而MRI平掃較CT平掃對VBD的診斷率高。
總之,VBD有多種多樣的臨床表現,尤其對臨床上有相關神經卡壓綜合征為主要表現,CT或MRI平掃未見明確非血管病變的影像,應重點觀察有無VBD的可能,一旦考慮該病,進一步行CTA或MRA檢查是必要的。
[1]師艷芳,武 劍,黃小欽.椎基底動脈擴張延長癥的研究進展[J].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2014,14(5):534-537.
[2]Samim M,Goldstein A,Schindler J,et al.Multimodality imaging of vertebrobasilar dolichoectasia: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imaging spectrum[J].Radiographics,2016,36(4):1129-1146.
[3]王 政,邵寶富,王 超,等.椎基底動脈延長擴張癥的CT與臨床分析[J].醫學影像學雜志,2015,25(10):1727-1730.
[4]俞 曄,鄧麗影,張 明,等.椎-基底動脈擴張延長癥的臨床和影像學特點(附2例報告)[J].臨床神經病學雜志,2010,23(2):133-134.
[5]韓金濤,喬惠婷,韓 旭,等.椎基底動脈延長擴張癥的計算流體力學分析[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15,47(2):302-304.
[6]王國卿,封麗芳,孫明東,等.椎基底動脈迂曲擴張癥的相關影響因素及其血流動力學變化的臨床研究[J].中華神經醫學雜志,2012,11(8):827-831.
[7]閆呈新,張顏波,趙 雷,等.椎-基底動脈的形態與后循環缺血關系的MRI/MRA研究[J].實用放射學雜志,2013,29(10):1558-1561,1565.
[8]張福洲,陳華平,母其文,等.應用MRA評價基底動脈迂曲與椎動脈優勢間的關系[J].西部醫學,2012,24(4):684-687.
[9]閆呈新,張顏波,朱建忠.椎基底動脈迂曲擴張癥的MRI診斷及臨床價值[J].實用放射學雜志,2012,28(7):995-998.
[10]Najafi MR,Toghianifar N,Abdar Esfahani M,et al.Dolichoectasia in vertebrobasilar arteries presented as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s:A case report[J].ARYA Atheroscler,2016,12(1):55-58.
[11]高鳳彤,郭 陽.基底動脈延長擴張影像學特點與MRA診斷標準探討[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5,41(1):20-25.
[12]AbdelHamid M,John K,Rizvi T,et al.Hemifacial spasm due to vertebrobasilar dolichoectasia:a case report[J].Radiol Case Rep,2015,10(4):65-67.
[13]Arrese I,Sarabia R.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trigeminal neuralgia secondary to vertebrobasilar dolichoectasia.Case report,literature review,and pooled case analysis[J].Neurocirugia(Astur),2016,27(6):304-309.
[14]Sokolov AA,Husain S,Sztajzel R,et al.Fat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following ischemia in vertebrobasilar dolichoectasia[J].Medicine(Baltimore),2016,95(27):e4020.
[15]Moreira I,Mendonca T,Monteiro JP,et al.Hypnic headache and basilar artery dolichoectasia[J].Neurologist,2015,20(6):106-107.
[16]甄英偉,南 陽,郭紅寶,等.椎基底動脈延長擴張癥的治療體會[J].中華神經外科雜志,2015,31(7):716-718.
[17]李碩豐,高志勝,魏冬冬,等.CT平掃對椎基底動脈擴張延長癥的診斷價值[J].實用放射學雜志,2011,27(4):479-482.
[18]裴昌軍,王 琨,裴 敏,等.MSCT診斷椎-基底動脈先天變異的價值及臨床意義[J].醫學影像學雜志,2015,25(12):2114-2117.
[19]龍光宇.常規MRI聯合MRA對椎基底動脈迂曲擴張癥的診斷價值[J].醫學影像學雜志,2014,24(2):176-178.
[20]黃益洪,林 菡,曾煥忠,等.椎-基底動脈延長擴張癥的臨床及影像學特征分析[J].嶺南急診醫學雜志,2014,19(6):475-476.
[21]陸敬民,劉金有,唐廣山,等.椎-基底動脈延長擴張癥的磁共振診斷價值[J].中華臨床醫師雜志(電子版),2013,7(3):1269-1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