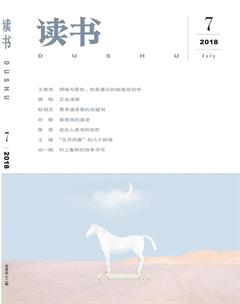正本清源
傅剛
一
《玉臺新詠》最早著錄于《隋書 ·經籍志》,署名徐陵撰,這與現存《玉臺新詠》署題一致。至于徐陵署陳銜,當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 “殆后人之所追改 ”。全書共十卷,收錄漢代至南朝梁有關女性題材的詩歌六百多首,許多優秀詩歌賴此書得以保存。與詩文并收的《文選》相比,此書專收詩歌,且專收與女性有關的詩歌,既顯示其特色,也為這一類詩歌作品的存世做出了貢獻。在編輯體例上,由于本書古今作品并收,所以執行兩種體例:古代(已故詩人)作品按作者的卒年先后編排,主要體現在前六卷中,時代則跨漢、魏、晉、宋、齊及梁,梁代是編者徐陵生活的時代,在體例中屬于今(當代),但徐陵編集時,有些入梁的詩人已經故去,所以也列入古代(已故),如第五卷的江淹、丘遲、沈約、何遜等,這些人的作品全部按照卒年先后排列。雖有身為一代帝王的詩人,也不逾越這個體例,如第二卷的魏明帝,就排在曹植之后。又如第十卷中宋孝武帝,也排在謝靈運之后。第八、第九兩卷收錄當代作品,體例則按照爵位高低排序。第七卷收錄蕭氏父子作品,梁武帝自然排在首位,其次是蕭綱,因為他當時是太子身份,所以題銜稱為 “皇太子 ”。又因蕭統以太子身份故世,謚昭明,世稱昭明太子,如果也收錄他的作品,導致一個集子中有兩個太子,無論從政治層面還是從閱讀層面看,都極不方便,所以本書未收蕭統作品。當然,蕭綱與蕭統的文學觀完全不同,蕭綱命徐陵編《玉臺新詠》,有與故太子蕭統抗衡的目的,這樣就更不能收錄蕭統的作品了。再如蕭繹的身份為藩王,是梁武帝第七子,所以排名就需在其兄邵陵王蕭綸之下。第九、第十兩卷按文體編,第九卷收雜歌,第十卷收絕句,體例仍據前八卷,即屬于已故詩人的按卒年先后,見存的詩人按爵位高低。如第九卷自古歌辭至費昶,都是已故詩人,自皇太子蕭綱始,則為見存詩人。徐陵編集后為本書寫了一篇序,即列在卷首的《玉臺新詠集序》,徐陵在《序》中說明他編集的目的是選錄 “艷歌 ”及“當今巧制 ”,這說明了本書的特色,但本書是按照什么體例編輯的,徐陵沒有明說,以上解釋的體例是當代學者研究的結果,經過驗證,完全可以成立。
為什么要編這部書?徐陵在《序》中明確說是選錄 “艷歌 ”及“當今巧制 ”,但為什么要選錄艷歌和當今巧制呢?徐陵沒有說,唐人劉肅《大唐新語》為之做了解釋說:“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 ‘宮體 。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據劉肅的說法,蕭綱晚年對自己為太子時好作艷詩且流行朝野很后悔,故命徐陵編《玉臺新詠》,表明艷詩的寫作自古就有。這個說法中關于蕭綱為太子時命徐陵編《玉臺新詠》是可信的,但說是晚年就不可信了。蕭綱生于梁天監二年(五0三),卒于梁大寶二年(五五一),不滿五十歲,且他自侯景之亂(五四九)就受困于侯景,其時徐陵已于前二年(太清二年,五四八)北使魏,直到蕭綱被侯景殺害也沒回歸南方,所以徐陵只能在太清二年之前有可能幫蕭綱編《玉臺新詠》。因此,根據蕭綱的生平,并不存在 “晚年”的說法。事實上,已有的研究表明,蕭綱命徐陵編《玉臺新詠》,時間在梁中大通六年(五三四)前后,下限在大同元年(五三五),因此,《玉臺新詠》的編纂不能用蕭綱晚年的說法。蕭綱在中大通六年為什么要命徐陵編《玉臺新詠》呢?這與他此時入宮繼其兄蕭統為
太子的政治形勢以及他的文學觀有關。蕭統是梁武帝蕭衍的長子,天監元年(五0二)被立為太子,中大通三年因病去世。他在太子期間,養德東宮,組織東宮學士做了很多與文學有關的工作,最著名的便是編纂了一部流傳至今的《文選》。蕭統的文學理想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在他的引導下,梁天監、普通年間便形成了崇尚典雅平正的文學風尚。這種風尚顯然與蕭綱的追求不同。蕭統為太子的時候,蕭綱位為藩王,歷任南兗、荊、江、雍等州刺史。蕭綱曾在自序中說自己七歲便有詩癖,但所好是艷體,長而不倦。他的這種愛好受他老師徐摛的影響,《南史》本傳記徐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他在蕭綱七歲時便作為文學侍讀陪伴左右,因此蕭綱的寫作和文學觀都受到徐摛的影響。普通四年(五二三)至中大通二年的雍州刺史之任,是蕭綱艷體詩寫作的高峰期,《玉臺新詠》收錄了不少寫于這一時期的作品。雍府時期的文學寫作使蕭綱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文學觀,其與在京城的蕭統所推行的典雅的、文質彬彬的文風大不相同。因此,當蕭綱入宮繼位太子時,他顯然是躊躇滿志的。他在《與湘東王書》中充滿豪情地批評了當時京城流行的文風說:“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顯然是針對蕭統所倡導的文風。蕭綱入宮之后就將他在雍府推行的艷體也帶到了京城,形成了所謂的宮體。不過,這種寫作引起了朝中群臣的反對,本來梁武帝選他為太子就充滿了爭議,而他又推行艷體詩風,朝野的議論就更多了。侯景在軟禁了梁武帝后,上書批評梁武帝政治之失,其中便有對蕭綱的指責:“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輕薄,賦詠不出《桑中》。”侯景這個批評應該是當時朝野的普遍意見。《梁書 ·徐摛傳》記載有梁武帝聽聞東宮寫作艷詩的事后大怒,遂召徐摛責問的事,雖然史書說徐摛應對得體,蕭衍沒有進一步追究,但就在這件事發生后不久,徐摛便被外放為新安太守,不能不說是受了這件事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說蕭綱命徐陵編撰這樣一部《玉臺新詠》,表明此體自古便有,以此挽回蕭衍對他的不利看法,應該大體不錯。
這部編輯目的是 “大其體 ”的詩歌總集,卻收集了自漢代以來有關女性題材的詩歌,流傳至今。除了第七、第八兩卷所選基本以艷情題材為主外,其余作品內容大多健康,風格明快,多為名篇佳作,不可一概以艷情而否定之。尤其當我們從文學文獻角度審視,其價值更無可估量。即使是第七、第八卷的艷情詩,也是我們研究南朝文學非常寶貴的材料。而艷情詩中也不乏佳作,其聲色之美也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南朝詩人巧妙的構思和工麗的筆觸,也都在艷情詩里得到很好的表現。《玉臺新詠》與《文選》一樣,作為現存最早的兩部文學總集,保存漢魏六朝時期文學作品有功,其對后代搜集整理和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具有重要的價值。
二
《玉臺新詠》編成于梁,編者徐陵由梁入陳,正是南朝最后兩個朝代,五八一年,陳被隋所滅,后人總結陳人滅亡的教訓,自南朝宋以來流行的華麗綺靡文風也為原因之一,因此,作為宮體詩代表的《玉臺新詠》一直受到批評,這也是《玉臺新詠》流傳不顯的原因。
《玉臺新詠》的流傳有些不絕如縷,我們目前能夠見到最早的《玉臺新詠》版本,也就是明本,事實上,宋代已經刻印過,而在敦煌出土的卷子中,也有《玉臺新詠》殘卷。而自隋唐以來的公私藏書目錄亦著錄不闕,但流至當代,竟然不見明以前版本,還是說明這部總集的尷尬地位,這與《文選》的盛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傳世的明、清《玉臺新詠》版本可歸為兩大系統:一是明代通行的版本,主要有明嘉靖十九年鄭玄撫刻本、嘉靖間徐學謨刻本、嘉靖二十一年張世美刻本、萬歷七年茅元禎刻本、天啟二年沈逢春刻本,以及不明年代的陳垣芳刻本等;一是明五云溪館活字本、明末趙均覆宋陳玉父本,以及清康熙五十三年馮鰲所刻二馮(馮舒、馮班)校本、康熙四十六年孟氏刻本,以及民國時期徐乃昌翻趙氏小宛堂本等。
明代通行本底本來源已不明,而趙均覆宋本的底本則明確為宋陳玉父刻本。因此,《玉臺新詠》這兩個版本系統略可分為明通行本系統和宋陳玉父本系統。五云溪館本出現在趙均覆宋本之前,但在明代似乎流行不廣,所以沒有多少影響,以致明人對五云溪館本了解不多,所以盡管對明通行本的體例不理解,也沒有引證五云溪館本。宋陳玉父刻本是趙均的父親趙宧光得到的,當時即在學林引起震動,馮舒隨即帶人去趙均家里鈔寫四天,后又細加校定,其校本后由其裔孫馮鰲刊刻印行。陳玉父本解決了明人對通行本的疑惑,趙均《玉臺新詠跋》說:“馮己倉(舒)未見舊本時,常病此書原始梁朝,何緣子山廁入北之詩,孝穆濫擘箋之詠?”關于《玉臺新詠》編于梁時還是編于陳時,學術界最近有所討論。明通行本合于編于陳時的體例,陳玉父本則合于編于梁時體例。其實,《玉臺新詠》編于梁時有充分的證據,不知為何還會被視而不見。《玉臺新詠》編成后,對唐人還是有影響的,唐李康成模仿《玉臺新詠》編有《玉臺后集》,明確說收錄詩人的時間體例是從太清以后開始。《玉臺后集序》說:“太清之后,以迄今朝,雖未直置,簡我古人,而凝艷過之遠矣。”這是明言上接《玉臺新詠》集的意思。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 “玉臺新詠十卷 ”條引李康成《玉臺后集序》稱:“昔 (徐 )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及“玉臺后集十卷 ”條所記:“《玉臺后集》十卷,右唐李康成采梁蕭子范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序編謂名登前集者,今并不錄,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所言更為明確,即謂李康成編《玉臺后集》,時代繼徐陵《玉臺新詠》之后,采蕭子范以下至唐張赴共二百零九人,其中庾信、徐陵二人雖已收錄在《玉臺新詠》中,但二人后來分別仕周和陳,其仕于周、陳時的作品與二人在梁代所作不同,既為異代,故亦收錄在《后集》中。論者或許強辯說,雖然據李康成的《序》證明徐陵《玉臺新詠》收錄作家作品限于梁太清之前,也并不影響徐陵在陳時編此集就是如此體例。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要問:徐陵在陳時編此集,為什么要采取僅限于梁太清之前的體例呢?這樣做的目的何在?至于李康成說《玉臺后集》的性質是樂府歌詩,有研究者據此論徐陵《玉臺新詠》亦是樂府歌詩,我們認為李康成的《玉臺后集》已佚,不好討論,但徐陵的《玉臺新詠》絕不是樂府歌詩集,集中所收詩多為不能入樂者,如阮籍《詠懷詩》、張協《雜詩》、陸機《擬古》、江淹《雜體詩》等,從未有材料證明其為樂府。
《玉臺新詠》除明版以外,再早的版本已經難以見到了,但是我們在宋人所引《玉臺新詠》中證實了宋人所見與陳玉父本完全相合。這些材料可見宋初晏殊組織門客所編《類要》,我在《由〈類要〉見玉臺新詠原貌》中討論過這個問題 ,主要從兩個方面見出。一是《類要》所引作者署名與陳玉父本相合。《玉臺新詠》這兩個系統的本子,最大的區別有兩個:一是對蕭綱、蕭繹的不同題名,一是梁武帝父子作品所置卷的不同。明通行本將梁武帝父子作品排在第五卷,并對蕭綱和蕭繹分別題作 “梁簡文帝 ”和“梁元帝 ”,陳玉父本則將梁武帝父子列于第七卷,對蕭綱和蕭繹分別題作 “皇太子 ”和“湘東王”。此外部分詩人入卷不同,如陳琳和徐干,明通行本入于第二卷,陳玉父本則入于第一卷。又如傅玄,明通行本入于第三卷,陳玉父本則入于第二卷。這兩個版本系統的不同,哪一個才是徐陵原貌呢?我們曾對這兩種不同的體例做過細致的研究分析,證明陳玉父本是合于徐陵原貌的,即陳本的體例可以貫穿全書,但明通行本的體例卻不能。當然,這些都是理論研究,如果能夠找到明以前,甚至宋
以前的《玉臺新詠》版本,這個問題自然就解決了。目前宋版是不可能見到的,但若宋前有引用《玉臺新詠》的材料,且能夠見到版本特征的,也同樣可以解決問題,很幸運,我們在宋初晏殊所編《類要》里發現了材料。《類要》引《玉臺新詠》材料有不少,涉及版本特征的材料有十余條,略引幾條于下:
關于蕭綱、蕭繹的題名材料:
(一)《類要》卷二十八 “馬腦鐘 ”條:“(《玉壺(臺)》湘東王《棲烏曲》云:‘掘申 (當作 “握中 ”)清酒馬腦鐘,(裙 )邊雜佩琥珀龍。”(二)同卷 “雕胡 ”條:“《玉臺》皇太子《紫騮馬》云:‘雕胡
幸可薦,故心君莫違。當考。”(三)卷二十九 “挽強用牛螉”條:“《玉臺》皇太子詩曰:‘左把蘇合弭,傍持大屈弓。控弦因鵲血,挽強用牛螉。 ”
以上湘東王詩見趙均覆宋本卷九,題作《樂府烏棲曲應令》,蕭綱詩均見趙本卷七,前題《和湘東王橫吹曲三首》,后題《艷歌篇十八韻》。這些足以說明徐陵原本確是題 “皇太子 ”和“湘東王 ”。
關于《玉臺新詠》所錄詩人入卷的材料:(一)《類要》卷二十二 “墮地自生神 ”條:“《玉臺新詠》二傅玄曰:
‘若恨(今本作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案,此最能證明趙均覆宋陳玉父本合于《類要》所引,因為趙均覆宋本以傅玄詩置于卷二,而明通行本如徐學謨本、鄭玄撫本皆置于卷三。
(二)《類要》卷三十六《總敘邊情》“獨不見,長城不(下),死人骸骨相撐柱 ”條:“《玉臺新詠》一陳琳《飲馬長城窟侍(行)》: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腑。”案,趙本以陳琳此詩列于卷一,與《類要》引用本合,徐本、鄭本則列于卷二,與《類要》引用本不合。以上證據充分表明陳玉父刻本最合徐陵原貌,明通行本當是后人改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