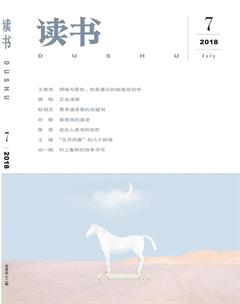舊日無常
朱靖江
法國人奧古斯特 ·弗朗索瓦(Auguste Fran.ois,1857-1935)在中國擔任領事的時候,曾為自己取了一個頗為風雅的中文名字:方蘇雅。從一八九六年駐節廣西龍州,到一八九九年赴昆明轉任云南府名譽領事,再到一九○四年任滿之后輾轉離開中國,這位襄理法國在中國西南地區事務的領事大人,和大多數旅華的歐洲外交官員一樣,盡管也曾遭遇些政治風雨,經辦些通商事務,甚至在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涌時還要武裝自保,一時間惹得天怒人怨,被指為 “昆明教案 ”之首惡,但也著實談不上多么位高權重,依然只是法蘭西帝國龐大外交機器中一枚小小的齒輪。當他回到巴黎,歸隱田園之后,人生的后三十年波瀾不驚,除了少數幾位親人后裔還記得這位偶爾穿上清朝官服懷舊的老人,并為他編纂了一本書信札記《白皮膚的滿大人》(Le mandrin blanc,中譯本名為《晚清紀事 —一個法國外交官的手記》),方蘇雅逐漸在歷史的煙云中銷聲匿跡。
時隔將近百年之后,方蘇雅在其昔日旅居五載的昆明城再度聲名鵲起,不是因為他曾參與的帝國政界往事,而是緣于他當初一個私人癖好:攝影。作為一名技藝精良的業余攝影師,方蘇雅在外出旅行時,通常隨身攜帶數架照相機與幾箱玻璃底版,每見不同尋常的風俗景物,便拍照記錄,或做地理勘探之參照,或滿足他博物愛好者式的獵奇心理。這些照片在方蘇雅返回法國之后并未交公,而是封存于他位于昂熱的私宅里,直到其壽終正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云南人殷曉俊在法國獲得了部分方蘇雅照片的版權,并先后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昆明云南陸軍講武堂舊址舉辦展覽。其后十余年間,方蘇雅在云南、廣西、四川等地拍攝的照片更多地進入中國公眾視野,其早期攝影家的聲望也已遠超過他作為外交官的歷史地位。
盡管方蘇雅的攝影作品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但他依然只是十九世紀后期至二十世紀初葉在中國留下圖片遺產的眾多攝影者之一。真正奠定方蘇雅在中國影像史上重要地位的,并非其圖片攝影,而是他另一個更不為人所知的業余愛好:拍電影。如果說誕生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靜態攝影術在發展了半個多世紀之后,早已是那些有所追求的旅行者異域旅行的采風工具,那么由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于一八九五年發明的電影攝影機,才是影像達人方蘇雅帶到中國最尖端的高科技神器。電影攝制需要更復雜的操作程序與更高超的攝影技術,令人稱奇的是,這位法國駐云南府的名譽領事,居然也是拍電影的一把好手,他所攝制的動態影像穩定、清晰,其品質在同代電影作品中堪稱上乘。
方蘇雅拍攝的中國云南影片在其身后去向較為散亂,且較少進入電影史研究者的視野。目前所知最長的影像集錦(即未經剪輯的鏡頭組合)為英國皮特 ·里弗斯博物館收藏的版本,片長約四十二分鐘二十三秒;法國方蘇雅協會曾于一九九0年出版過一部三十二分鐘的影片《中國影像》(一九0一至一九0四),從內容介紹來看,有多個鏡頭不在前片的序列之內;此外,法國高蒙百代電影公司的資料庫中,也有部分方蘇雅拍攝的電影片段。粗略統計,這些影片材料總長至少超過六十分鐘。在他之前或者同一時期,盡管也有盧米埃爾兄弟公司的職業電影攝制組到中國拍攝,但多為匆忙獵奇之舉,且存世作品寥寥,偶見只鱗片爪的零散鏡頭。而方蘇雅在云南歷時數年所拍攝的電影素材,涵蓋城市街景、日常生活、舞蹈戲曲、案件審理以及官方活動等內容,達到了那個時代最為系統、多元且海量的程度,堪稱晚清中國社會一部前所未有的 “電影百科全書 ”。
方蘇雅之中國觀,與其長期擔任法國駐華使節的經歷至為密切,亦受十九世紀后半葉主導西方思想界的社會進化主義熏陶。方蘇雅輾轉履職于中國最邊遠、貧困的西南諸省,所見民生之凋敝,官場之腐朽,生存環境之惡劣困苦,社會風氣之保守排外,較之西風早已東漸的華東地區尤為不堪,他在旅行筆記與信件中,對身陷此等情境往往嗔怒憤懣,罵之不絕。方蘇雅雖然沒有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但他作為一名曾派駐法屬殖民地與遠東古國的官員,無疑是以法國價值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故其觀照中國的視角,自然不出歐洲文明至上的東方主義窠臼,又帶有些所謂 “拯救人類學 ”的熱忱 —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在所難免地被西方現代文明碾壓湮滅之前,撿拾、收藏一些遺存的碎片,作為人類社會階梯式發展的證據。方蘇雅的照片、電影,以及他煞費苦心搜集來的銅鼓、樂器、字畫,甚至墓地里掘來的頭蓋骨,都是這位業余人種志愛好者為法蘭西民族奉獻的誠摯禮物。
方蘇雅在云南拍攝的電影,描繪了他經年所見的中國圖景:“赤貧、陳舊、破碎,但仍舊不斷地向人展示其魅力,即使在今天,依然讓人感到驚訝、好奇與興趣盎然。”透過這些活動的影像,一百多年前昆明的市井百態、三教九流,甚至于難得一見的衙門事務、外交禮儀,都鮮活地呈現于當代人的眼前,如隔世重演的西洋鏡,抑或是在電影幕布上明滅不定的晚清浮世繪。
一
方蘇雅于一八九九年末赴昆明履職,次年即因 “昆明教案 ”被迫離境返回安南,待時局安定后,他于一九○一年再度回到昆明,四處游歷考察,籌備滇越鐵路的勘探與修建事宜 —電影攝影機大約是在這一時期被他帶到其領事官邸的。對于這座邊遠閉塞的云南省府,他一方面抱怨其凋敝與污穢,另一方面,又慶幸城中的傳統生活未被西洋新潮所染。他曾寫道:“我生活的這座城市是不開放的,除了我帶來的一些東西外,它尚未受歐羅巴的影響。我是一名觀眾,我能觀察到中國社會中十足地道的東西,我力圖深入下去并得出某些觀點看法。我認為,一個存在了如此多年的泱泱大國,它迄今仍不為人知的現象很快就要結束了。”正是這種與后世民族志作者相近的思考付諸行動,讓這位尊貴的法國領事大人親身出沒于昆明大街小巷,拍攝了城墻內外多個區域的生活圖景。
“方城的三面,城墻外便是郊區農田,最重要的南門方向有條商業大道延伸一公里多長,通往蒙自和東京。”方蘇雅將鏡頭對準昆明的標志性建筑 “金馬碧雞牌坊 ”以及坊間臨街鋪面:“未經雕琢的街石不嚴縫地鋪在地面,街中心滑溜溜的地面上,不時有一凼凼的積水。在這些水凼兩邊,一排樣式相同、低矮破爛的擋雨屋檐由蟲蛀了的柱子支撐著,為小攤販的攤子遮雨,大小相似的小攤子一個接一個在自家的屋檐下擺著,自城市建設以來便是如此。”
方蘇雅更喜歡拍攝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街上,一群群臟兮兮的塵土滿面、泥漿滿身的行人,穿著寬大的齊膝棉褲,腳蹬草鞋,頭戴帽子,不過絕大部分帽子都像被捅破了底的蓋子。在嘈雜的人群中,有時也會碰上個把穿天藍色棉布長衫的先生,或者碰上難得一見的著綢穿緞的闊佬,有時還會遇上盛裝的婦人。”在方蘇雅的攝影機前方,往往猬集很多好奇的民眾,緊緊盯著這個有護兵拱衛的洋人和他搖動手柄的奇怪機器。隔著一百多年的時光,祖先的目光透過鏡頭與我們對視,既有古老血脈的傳承,又有文明嬗變之后的陌生與錯愕。
與二十世紀前葉大多數浮光掠影的旅華電影不同,方蘇雅的影片記錄了很多晚清昆明市井細節,至今仍可感受濃郁的生活趣味。他曾完整地記錄了一組晚清男子理發的鏡頭,為今人研究清人辮發的日常打理留下了珍貴的影像材料。在影片中,兩名剃頭匠站在街邊,各備一高一低兩把圓凳,且共用一個木架上的水盆。兩位顧客先是坐在矮凳上,上半身伏撐于高凳,由剃頭匠為其捏肩捶背,刮頭剃須。在下一個鏡頭中,剃頭匠已坐在高凳之上,順著光線為顧客“采耳 ”。此后顧客付費,皆大歡喜。這段影像將剃頭攤高低凳的多種用途清晰展現,可見設備雖簡陋,服務有巧思,“匠人精神 ”可謂千古不磨。
方蘇雅以他府邸的中國管家夫婦為對象,拍攝了兩組休閑飲食的場景。在第一組鏡頭中,這對衣著體面的夫婦坐在庭院里,面對攝影機,手中端著碗筷。男子坐姿端正,泰然就餐,女子露出三寸金蓮踩在凳子上,不知是慣常如此,還是方蘇雅特地要求她展示 “國粹”。另一組同景別的鏡頭,展現了管家夫婦吸水煙的情景。兩人各持一副黃銅煙具,吞云吐霧,間或端起茶碗,啜飲一口茶水。管家行為自若,顯然是對領事大人的拍攝活動司空見慣,夫人的舉止較為扭捏,神情略有不滿,很不習慣被攝影機與洋人直視其姿容舉止,昆明街頭理發攤屠宰生豬時進行簡單的祭祀卻遭到了管家的斥責,只得無奈地繼續對鏡表演。這兩組擺拍的影像,意在呈現中國人的日常起居,卻在無意中體現了攝影機兩造不平等的權力關系。
或許是出于獵奇的心理,方蘇雅還拍攝了兩組屠夫殺豬的鏡頭,在電影搖籃時期,這可算是生猛 “重口 ”的攝像之舉。第一組影像中環境優雅,黛瓦白墻,殺豬者衣著體面,應是大戶人家的仆役在操刀屠宰;第二組影像中的屠夫衣服破爛,背后的土房墻壁破裂,村童環伺,或是普通村民在屠宰年豬。有趣的是,無論貧富如何,在殺豬的過程中都有人燒香燃紙,進行簡單的祭祀,或為告慰豬靈,庇佑投胎之舉。這一儀式今日已不可見,屠宰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成為遠離公眾視野的死亡流水線,先人基于輪回往生的樸素信仰,為生命之犧牲燃起的火燭,也早已悄然寂滅,只余星點流落在異國他鄉的影像殘片中。
二
在晚清混亂的政局中,偏居云南一隅的方蘇雅雖有較高的職銜,在政治上卻無足輕重,因此,他有大把的時間和精力用來觀賞昆明本地的曲藝,甚至做些堂會,將藝人請到宅邸演出。在方蘇雅的電影中,有相當多的內容與戲曲、武術、雜耍或其他江湖演藝相關,以動態影像的形式直觀地存留下清末云南民間表演藝術的時代風貌。
方蘇雅通常在一座宅院門內的空場拍攝他感興趣的演出活動。如果參考他對于領事官邸的一番描述:“在這個院子的左邊,有一條中國式的長廊,有孔透光的建筑物,掛著薄薄的絹紙,既可當墻,又可作窗。這條長廊被一個寬敞的過廳式的玩意兒分成了兩部分。”這個地點應該正位于領事館內部,便于他不受干擾地進行電影拍攝。在高蒙百代電影公司收藏的資料當中,存有兩組戲曲演出的場景,其中既有以武丑為主角滿場打鬧的武戲,又有兒女祝壽、金玉滿堂的文戲,每一場戲均有十名左右的演員上場表演,人頭攢動,場面相當熱鬧。在皮特 ·里弗斯博物館收藏的電影版本中,同樣有兩場戲曲表演。首先是一位男性旦角的舞蹈,他身材頎長,舞姿舒展,在琴師的伴奏下,舉手投足頗具風韻,應是未上戲裝前的一套戲曲舞段。在隨后的戲曲演出中,這位演員身著刀馬旦戲服,與另三位男演員在鏡頭前表演了一出武戲,手舞足蹈,令人眼花繚亂。有趣的是,刀馬旦在與一名武生演對手戲時,忽然親吻了對方的臉頰,不知這是某部戲文的橋段,還是那位男旦演員的即興發揮。
此類 “雜耍百戲 ”入方蘇雅影片者,還有一堂猴戲。四人一猴的戲班子鳴鑼開演,兩人手持一方白色幕布立于后場,耍猴人一邊敲鑼唱戲,一邊指揮操控著拴在繩子上的小猴翻跟頭打把式。幕布前方還有人坐在道具箱旁,猴子蹦跳一會兒便會跑到箱前,打開箱蓋,此時,道具師會為它換一頂戲帽或面具,有時還遞給猴子一根短棒,以配合耍猴人說唱的戲文。猴戲在中國傳承久遠,自清代以來多為河南新野縣籍藝人行走江湖的傳統技藝。這段影像雖沒有聲音,無從判別耍猴者究竟是何方來客,但若參考有關新野猴戲之描述:“玩猴人手中的鑼鼓,又叫 ‘報君知 ,猶如指揮棒,鑼聲一響,猴戲開場,在輕、重、急、緩提示下,猴子就會心領神會,做起妙趣橫生的動作。當玩猴人口唱 ‘打開柜子調開了箱,裝一個三關的楊六郎 ,猴子聞聲,就跑到箱子里拿一頂盔帽戴上,而后按鑼聲信號,一會兒戴包公面具,一會兒戴關公臉具,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其描寫的內容與該段影片情狀如出一轍。又考新野猴戲藝人在清末、民國時期有前往緬甸、越南耍猴謀生之傳統路線,則方蘇雅所拍到的,或許正是幾名途經昆明沿街賣藝,被領事大人邀來府上演出的河南耍猴人。
三
晚清中國社會孱弱窮困,民眾亦陷入煙毒與赤貧的惡性循環。方蘇雅曾在其與友人的書信中寫道:“昆明全城籠罩在鴉片的麻木之中。空氣中還飄著昨晚抽的鴉片的余味,這些氣味打那些關閉不嚴的破房子里冒出。這種香味在中國城鎮中司空見慣,這種煙味盡管尚未毀滅當地的百姓,但卻已牢牢地控制并主宰著他們了。”
在方蘇雅拍攝的影片當中,有兩組鏡頭表現了中國男子吸食鴉片的鏡頭。第一組是一名頭戴瓜皮帽的男子橫倚在一張煙榻上,煙榻臥具繡花,十分精美,男子對著攝影機展示了填充煙土、點燃煙槍以及吸煙享受的全部過程。而在接下來的鏡頭中,該男子與另一位年齡、身份相仿的同伴分享煙榻,并頭而臥,于煙云之下談笑風生。
在社會的最底層,昆明的乞丐們也得到了方蘇雅特別的關照。他曾用了六七個鏡頭,頗為詳盡地記錄了一次在領事館舉行的施舍活動。一群衣衫襤褸的乞丐(云南人稱為 “花子 ”)魚貫而入,在一位管家的指揮下,先是向攝影機 —也就是方蘇雅所在的方向下跪叩拜,隨后便迅猛地撿拾灑落在地上的糧食。下一個鏡頭中,管家與一名助手將幾串銅錢拆散,依次遞給排隊等候的乞討者。領到錢糧的“花子 ”們再一次向主人叩謝,隨后,約有六名青年乞丐赤裸上身,相互推搡打鬧,以娛樂主家。因這段影像缺乏歷史語境,乞丐們成群上門乞討的原因不詳,但云南省內由于宗教氛圍濃郁,傳統上有逢節日、廟會或紅白喜事布施行乞者的習俗,如迄今大理在每年農歷三月二十八日東岳廟會期間,都有所謂 “花子會 ”,云南乃至外省的大批乞丐云集于此,集體接受進香祭祀者的施舍。方蘇雅所拍攝的這段 “丐幫影像 ”,或與晚清昆明地方的此類風俗有關。
方蘇雅拍攝鴉片癮君子與乞丐之影像,當然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獵奇行為,以華人的鴉片毒癮和尊嚴淪喪的乞討行徑,反襯歐洲文明之健康、文明與高尚。他曾在一封信件中寫道:“骨瘦如柴的行人、乞丐、蠢貨、殘疾人等,構成一幅行尸走肉的奇妙圖畫。這些人在垃圾堆中擁來擠去,實際他們自己就是一堆堆垃圾。”其鄙夷與刻薄之色溢于言表,無須今人強加粉飾,非要稱其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這幾組令人不安的影片存續至今,也如被一道道目光撕裂的傷痕,讓我們看到一百多年前 “東亞病夫 ”之真容,以及在歷史深處揮之不去的不堪 “國故 ”。
四
方蘇雅身為法國駐云南府領事,在當地官場地位頗高,凡中法兩國在西南地區的交涉,大都有其參辦。借此官方身份,方蘇雅亦尋機拍攝了一些外國平民難得見到或不可拍攝的公務活動。這也為今人感知、研究清末的司法、政務與軍事提供了直觀的材料。
在留存至今的方蘇雅電影資料中,唯一著有標題的影片是一部名為《中國的審判》的短片,系方蘇雅拍攝的一起清末案件審理過程。不知是否為照顧拍攝時的光線,審判的場所設在官衙的庭院里。主審官落座之后,衙役用鐵鏈牽引犯人上前,跪在官員的桌前。簡單對答之后,官員敲擊桌面,作呵斥狀,便有衙役上前,令犯人俯臥于地,以木棍擊打臀部數十下。待官員繼續訓話之后,犯人復被衙役以鐵鏈引走。這部短片雖然只有一分四十秒的時間,卻相當完整地記錄了中國傳統司法體制的基層運作方式:審判者擁有獨大的裁量權,審判過程中肉刑的普遍使用,以及受審者人身權利毫無保障的狀況。本片或可作為列強在中國要求治外法權的一項視頻證據。
方蘇雅還在其領館庭院內,拍攝了一組接待清朝官員的影像資料,展示其外交活動禮儀。影片開始時,一些低級別的官吏排列在內墻的走廊里,大門口似有喧雜之聲,以至于身著禮服的方蘇雅需提前走出來探查情形。到訪的第一位中國官員(前有兩名引導官,后有一名撐起傘蓋的侍從)走進領館門廳之后,方蘇雅與他互相抱拳行禮,并向其介紹另一位法國官員,三人隨即向內院走去。第二個鏡頭展現了另一位中國高官來到領事館的情景: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夾道恭候,方蘇雅及其同僚以更為舒緩莊重的姿態表達了對這位白須長者的敬意。當他們進入內庭之后,列隊歡迎的下級官僚才解散,一部分尾隨長官赴會,另一部分則返身向門外走去。影片的第三個段落是外事活動結束之后,方蘇雅送客的場景。高官的大轎早已抬至院內,八名轎夫候駕多時。方蘇雅再度和那位白須官員抱拳寒暄后,目送他坐入轎中,離開了法國領事館的大門。
方蘇雅在一九0一年底與友人的一封書信中,曾描述過一場與云南地方官員在官邸的歡宴,似可與這段影像互相佐證:“進門的順序是按級別由低到高排定的 ……在石階上,我們抱拳作揖,鞠躬唱喏。這種禮節在大廳內再一次重復之后,我便把賓客引上榮譽席,用雙手恭恭敬敬地奉上茶碗。……又是三聲炮響,宣布總督的來臨。所有的官員都站起身來,趕到他們的頭兒必經的路旁,按官階順序躬著身子,一動不動地排成一行。跟我互致敬意后,魏大人閣下(此指云貴總督魏光燾)才像檢閱儀仗隊似的穿過他手下人的隊伍,
莊重地晃著他裘皮大衣的下擺,以及冬季帽子上的孔雀羽毛走進了客廳。”考清朝禮制,直省總督、巡撫配轎夫八人,在影片中乘坐八抬大轎來去的老年官員,或正是時任云貴總督的魏光燾,而方蘇雅用電影與文字描述的,大抵是發生在一九○一年歲末的同一場宴會。透過影像,我們看到了晚清官員們與法國外交官的往來交際,透過方蘇雅非常細致的文字描寫,這場宴會的飲食與社交細節歷歷在目,兩者互相參照,將一場禮儀僵化、貌合神離的中法外交晚宴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
“有些時候,一些非凡之人見證了歷史的關鍵時刻。這些人或許并不廣為人知,但他們卻為我們留下了非同凡響的歷史遺產,方蘇雅無疑是其中的一員。”法國的方蘇雅協會如此評價這位曾經旅居中國十年有余的法國領事。盡管在多數時候,方蘇雅影像中與筆下的中國人都顢頇落后,但他并未徹底蔑視這一歷史悠久的東方文明,甚至常因在云南的所行所見,反思高舉科學進步主義而行侵略殖民之道的法蘭西母國。
方蘇雅于一九0一至一九0四年在云南拍攝的電影,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年代最早、內容也最為豐富的中國題材影片,其珍稀性不言而喻。方蘇雅超越其時代之處,在于他非常前衛地將誕生僅五六年的電影攝影機用于他的日常生活當中,以一種參與觀察式的熱忱,用影像記錄下如此豐富的晚清社會圖景,如一部琳瑯滿目的 “電影百科全書 ”。方蘇雅的電影將我們帶入那個早已消逝的中國帝制時代,親眼得見昆明老城喧囂的市井以及在這座城市里生生不息的男女老幼。這些電影素材與他拍攝的大量照片、書寫的筆記體文字,以及收集的眾多標本、實物,構成了一整套描述清末中國西南邊疆社會的民族志材料,亦是中國電影史上極被忽視又亟須補寫的重要篇章。
三十年前,讀到李何林先生談論鄭欣淼的魯迅研究文章時,記住了鄭欣淼這個名字。那時候鄭欣淼在陜西工作,業余時間寫出《文化批判與國民性改造》一書,一時成為魯迅研究界關注的人物。我最早思考魯迅的思想,也參照過鄭欣淼的觀點,印象深的是他行文中的溫潤。他的那本書,背后有多種知識背景,并未有今天所謂學科劃分的痕跡,各種精神線條的盤繞,讓論述有了立體之感。那些談吐中,有彼時文化熱的痕跡,也看得出走出禁區的知識人的某些渴念。
多年后,我們同在國家文物局系統工作,他分管的單位就有魯迅博物館。文物系統乃史學研究者聚集的地方,文學研究者介入其間,就有一點闖入者的意味。鄭欣淼的愛好跨越幾個學科,故打量歷史的眼光就多了幾種參照。我注意到他后來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視點在多個領域移動,魯迅所云的 “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 ”的情懷,日趨濃厚起來。他提出了 “故宮學 ”的概念,且出版了《故宮學概論》等書,學問的空間增大。他的文物研究有不同于他人的地方,舊體詩詞的寫作亦多成就。但是在內心深處,魯迅情結最重,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他對于魯迅的感情,超出了歷史中的所有的人物。在古董的世界出出進進,沒有染上匠氣,也與此大有關系。
我覺得這 “故宮學 ”的背后,是有 “魯迅學 ”的支撐的。其間有著一般博物館人沒有的思維。將不同學科的精神匯合的時候,思想便溢出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