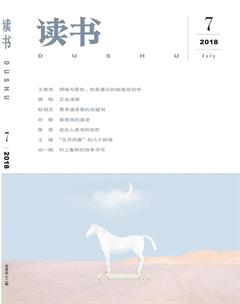暴力的歡愉,終將導致暴力的結局
嚴飛
科西嘉是地中海上的一座島嶼,自從十八世紀晚期被熱那亞割讓之后就一直隸屬于法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后,科西嘉正式成為法國的一個省,在國民議會中擁有代表權,并且和其他省一樣都擁有自己的地方治理機構,但和法國的其他地方相比,科西嘉的居民更加傾向于講近似于意大利語的科西嘉方言,在經濟上也始終以農牧業為主。
科西嘉島上的大部分男性都對槍械道具習以為常,這也造成了該地區整個十九世紀異乎尋常的暴力。這一時期,每十萬居民中每年死于暴力沖突的人數多達幾十人。相較而言,法國整個國家的兇殺率卻持續低于每十萬人一人。這一數字也大大超過了二十世紀晚期和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最為暴力的城市,到一九一○年才下降到與美國當代的總體兇殺率相當的水平。而導致暴力死亡的起因,卻皆來自一些瑣碎的小事,譬如財產的損失、打牌時的口角、有關邊界的爭議等等,甚至其中有一成是報復性仇殺,還有一成是由于拒絕迎娶一個因不貞潔而有損名譽的女人而發生的兇殺。更耐人尋味的是,科西嘉暴力沖突的峰值,恰恰對應于法國的幾次重大政治變革。譬如,一八三○年波旁王朝覆滅;一八三四年七月王朝在里昂工人起義之下搖搖欲墜;一八四八年巴黎人民起義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一八五一年共和國又被路易 ·波拿巴的政變終結;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爆發 ,波拿巴第二帝國垮臺,建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幾乎在每一個類似的關鍵歷史轉捩點上,科西嘉的兇殺率都呈現出急劇上升的態勢。
為什么科西嘉綿延一個世紀之久的暴力浪潮卻常常發端于看似微不足道的瑣碎小事?為什么法國的每一次政權更迭都會加劇遠離巴黎這個政治中心的島嶼上的暴力沖突?最容易導致暴力沖突的 “火藥桶 ”又在哪里?
這些問題引起了美國社會學家羅杰 ·古爾德(Roger Gould)的強烈興趣,并在《意愿的沖撞:社會等級的歧義如何孕育沖突》(Collision of Wills: How Ambiguity about Social Ranks Breeds Conflict)一書中指出,暴力是人際關系的產物,“因為糾紛并不如其表面所示,它們的焦點其實是社會關系 ”,并發展出一套用社會關系的變動及行動者因變動而采取的迥異的因應策略來詮釋暴力行為的解釋框架。
古爾德是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的學術明星,擅長挖掘第一手檔案資料,并利用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去解讀歷史事件。他一九九五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作《反抗者的認同:巴黎的階級、社區與抗議 —從一八四八年到巴黎公社》(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早已成為修讀這兩大方向的博士生的必讀書目。然而遺憾的是,古爾德的學術才華戛然而止于二○○二年。彼時他才三十九歲,剛從芝加哥大學轉到歷史社會學研究重鎮耶魯大學,開始對運動中的抗爭沖突進行理論上的闡釋。在逝世前兩周,古爾德完成了這本書稿。提交給出版社時,書稿里還缺少前言、致謝和獻詞,文獻部分也由好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家彼得 ·比爾曼所完善。
一
長期以來,有關暴力話題的討論一直是西方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熱點,因為暴力從某種角度來說是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的象征,反
映著權力的作用機制。對暴力的討論直接關系到對權力性質的論述,進而對關于政治和社會性質的理解產生本質性的影響,正如漢娜 ·阿倫特在《論暴力》一書中特別強調的那樣:暴力是權力的表現和工具,是人治的產物,而權力則是統治的工具。也因此,西方社會學和政治學界有關暴力的理論十分全面詳盡。由于社會的龐大性和復雜性,暴力事件和暴力行為多如牛毛,不同學者、不同流派對暴力的理解和定義也各不相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蘭德爾·柯林斯在《暴力: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就寫道:“暴力分為許多種,有些短促而偶然,如一記耳光;有些大型且計劃周詳,如一場戰爭。”但不可否認的一個基本共識是,暴力源自社會宏觀層面的社會制度、文化生態與階級結構和社會微觀層面的情緒、互動的共同作用。在宏觀層面上,暴力呈現出群體之間的沖突形式,暴力性社會沖突的規模越大、程度越深,就越受到關注,所以那些局限于小范圍或者未導致血腥暴力的沖突就很容易受到忽視。但事實上,集體的暴力行為終究還是發生在個體之間的。群體、社會、國家的沖突包含著個人間的沖撞,而且某種程度上是由集中爆發的私人間對抗和矛盾組成。因此從私人社會關系變動的層面探討 “沖突 ”是什么,
沖突形成的原因和解決的機制,都會對更深入了解社會群體和結構的沖突有所幫助。
什么是沖突?在古爾德看來,沖突顯然不僅僅是表面化的言語和動作沖撞,甚至這些內容都應該算作沖突之結果,即“暴力 ”的一部分。他用 “collision”一詞作為這本書的主標題,顯然把其中比 “conflict”程度更低的含義,即“碰撞 ”“抵觸 ”“傾軋 ”也作為沖撞、沖突的含義之一。的確,引發暴力的沖突只是冰山一角,在水面之下,在能被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斗爭之外,更多的是在日常關系中意愿的沖撞、是對二人關系結構中支配地位的競爭,這些更是私人關系沖突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古爾德的分析,在支配標準清晰且無可爭議的不對稱性社會關系中,譬如有組織的競賽、正式的等級制和君主繼承制,由于地位等級的懸殊,沖突反而較不容易發生。在這樣的社會關系里,處于精英地位的個人或者群體因為在支配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在事實上支配著不違抗主流地位等級的非精英個人或者群體,并讓這一部分群體覺得能夠被精英們納入他們的支配范圍而感到幸運。在這一點上,支配包含了社會影響的所有機制:“權威、強制、不對等交換、操作、欺騙、說明、展現優勢能力等。”
那么沖突什么時候容易爆發呢?古爾德首先指出,當雙方均處在明顯對稱的等級關系體系中的時候,暴力沖突更有可能爆發。這種對稱的社會關系,也可以稱之為平行的抑或相鄰的社會關系。在對稱性關系中,由于缺乏具有權威地位的仲裁人或者領導者,從而導致不同的個人或者群體在資源平均分布的情況下形成一種競爭支配地位。按照古爾德的分析,“所有社會等級體系中的支配地位(而不僅僅是財富或收入的高低),對其擁有者來說都有內在價值 ”,因此人們也會對追求更高的榮譽以及維護自己既有的榮譽和支配地位產生需求。更高榮譽者所擁有的心理優越感和話語及行動的支配權力,半強制半引誘著低等榮譽者向往更高。由此,雙方都秉承獲勝的不服輸的信念,爭取支配權的最大化、絕對化,從而更加需要通過公開的 “硬碰硬 ”沖突乃至暴力達至目的,形成一種所謂的競爭型暴力(competitive violence)。古爾德的實證研究均證實,在十九世紀的科西嘉、在二十世紀的三大美國城市(芝加哥、圣路易斯、邁阿密)、在中印度地區偏僻的原住民群體,比起更容易產生和平互動模式下的非對稱關系,往往是相對對稱的人際關系更容易引發致命的暴力紛爭。
第二種情況,暴力沖突更有可能會在等級關系模糊的關系體系中爆發。在等級關系不夠清晰明確的時候,行動者對其相對社會地位的理解具有含糊性,相對地位越模糊,這類沖突就越頻繁,且越具有破壞性。在個體層面,由于雙方均存在著認知上的不對稱,到底是順從還是挑戰,到底對方的等級優于還是低于自己,并沒有一個非常確定的信號。這種認知不對稱就有可能受到對方的挑戰,從而爆發沖突。而在群體層面,當處于模糊的相對關系中,每一方都在打賭對方的群體團結性只是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對抗群體又極力想要表達他們的統一性。當雙方都不確定對方的團結是否更加牢固的時候,兩方往往選擇對抗到底,以此來檢驗對方是否如標榜的那樣更具有組織的統一性和凝聚力。譬如在科西嘉,古爾德詳細搜集了二百二十一件殺人案件,并發現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一方的地位、影響力或社會網絡發生變動從而改變了雙方清晰界定的關系的時候,日常的糾紛就會升級為致命的暴力。
與此同時,在一方單方面要求占據支配地位改變現有對稱關系的時候,另一方選擇順從或者競爭還取決于雙方地位變動前后的差異程度。如果即使選擇在某一具體事件中順從,兩方實際的支配關系還不會形成實質的改變(或至少被動方認為產生了實際的改變),即仍會處在微小的量變階段,那么被動者更有可能選擇順從。而某一方的對支配地位的競爭如果會直接導致二人對稱關系地位的徹底改變,就很有可能引發另一方的強烈反彈和激烈競爭。
第三種情況,暴力沖突更有可能會在等級關系經歷調整動蕩的時期爆發,并帶來沖突的連鎖反應。在一個政治與文化秩序分崩瓦解的時候,過去行動者之間已經明確確定的既有關系就會發生變動,這種變動會反過來進一步導致行動者對其相對的社會地位產生迥然相異的詮釋。持續的不同的詮釋會產生新的利益訴求、新的模糊不清的從屬關系,從而導致新的沖突隨之而來。此外,由于人際關系網絡的交錯性,上層層面的社會關系必然與基層的社會關系通過恩庇、代理人等紐帶間接相連,也因此伴隨著全國性的政治動蕩和等級制中心權力關系的瓦解,地方層面的社會關系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動,在基層累積起暴力沖突的導火索,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發現,科西嘉的暴力高峰在法國政治結構的每一次大型調整時越發加劇。甚至當政治動蕩本身并非特別暴力,而是推行憲法改革的時期,科西嘉島上的兇殺率也直線上升。一段關系中的動蕩,就如同石頭扔進水里泛起的漣漪一般,必然會改變相鄰的社會關系或至少削弱其穩定性。被削弱后的社會關系等級模糊不清,就帶來了前面所分析的雙方產生出改變現狀的強烈意愿,從而形成一股 “意愿的沖撞 ”。
二
古爾德在社會關系互動的基礎上展開對暴力沖突的研究和討論,既新穎有趣,又別具一格。意愿的沖撞或者說對雙方關系中支配地位的競爭,是沖突的廣義定義,而內外因素導致兩方產生認知歧義則是沖突的火藥桶所在 —外部的政治波動常常會連帶導致在地的內部本已有著清晰支配標準的關系被打破,雙方從而陷入模糊的關系位置中,對模糊性的不同詮釋大大增加了從糾紛升格為沖突的概率。由于多種不同中間因素的分野和聯動,沖突雙方的應對選擇也不一樣,從而決定著沖突的下一步走向。
在歷史社會學的學科視野里,我們會發現,暴力不再是一個靜止的呈現,或者由人們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所影響,或者由單一的社會結構性變量所決定。相反,暴力是一種產生于社會互動過程中的行為或現象。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思路,就此即從 “關系 ”入手,對“過程”分析,目的在于還原 “機制 ”因果。
在“關系 ”的構建上,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家查爾斯 ·蒂利在《集體暴力的政治》一書中指出,集體暴力是社會互動的一個片段。暴力的具體產生機制是:社會關系的互動產生出社會身份的邊界,邊界在不斷受到刺激和傷害的前提下一般由暴力專家進行
邊界激活,在不斷強化 “我們 —他們 ”二元對立的身份邊界時,暴
力情景被建構,進而引發沖突和集體暴力。
這其中,身份認同起到了重要的動員和催化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 ·森在《身份與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里就明確指出:“身份認同可以殺人 —甚至是肆無忌憚地殺人。在世界范圍內,因身份沖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對立的身份認同至少包含三個形成因素:結構性因素、認知性因素和類別化因素。結構性因素指集體層面的 “相對剝奪感 ”或“同胞剝奪 ”,當人們將自己所屬的群體與其他群體比較時,就有可能因為剝削和機會積累導致的不平等狀況而產生對立和相互怨恨的身份認同。認知性因素指人們在事件中遵循社會烙印下的特定模式,當特定的意識形態、價值、目標等通過諸如社會運動的方式與運動對象的利益與怨恨聯系起來時,對立的身份認同就容易形成。類別化因素則指人們具有單一身份的幻象,從而通過身份塑造使一部分群體 “非人化”,引發歧視或偏見,甚至滅族屠殺。在這三種因素的作用下,人們對立的身份認同被強化,“我們 —他們 ”的身份邊界被激活并不斷被強調,從而促成了傷害性的互動,集體暴力被引爆。這個過程中,個體相互協作引起更大規模的暴力,并能從集體中得到保護,進行違反日常規范的侵害活動。個體被集體控制并將自身的利益與集體的利益掛鉤,最終在情緒的作用下參與集體暴力,成為施暴者。
在“過程 ”的挖掘中,暴力究竟是否發生,取決于一系列事件的進程在歷史的關鍵轉捩點上將會往哪種方向塑造人們施行暴力時的緊張和恐懼,并如何重新將在場所有人的情緒組織為一個互動過程,包括對抗的雙方、觀眾及至表面上完全不相干的旁觀者。
大多數個體之間的暴力除去開始的言語攻擊與最后的收尾,只能持續很短的時間。然而,如果有觀眾在場的話,一切就變得迥然不同。譬如,蘭德爾 ·柯林斯在暴力互動理論基礎上提出 “暴力隧道”(tunnel of violence)的傳遞之路的說法,即暴力大多發生得十分短暫和有限,如果有足夠的社會支持,暴力就有可能會在時間這一進程中得以延展,在這種情況下,觀眾實際上轉變成為隧道的建設者。
當有觀眾圍觀時,處在暴力舞臺上的演員會變得騎虎難下,從而愈加激動、斗志滿滿,抓住表演展示的機會。同時,處在聚光燈之下的矚目感會吸引更多觀眾不甘心只做配角,而主動參與到暴力之中。 “文革 ”時期的暴力行為就有這樣的特征,如電影《霸王別姬》中對程蝶衣和段小樓的批斗場景,就是在廣場中心、眾多觀眾的矚目下進行的。革命小將的批斗更像是激烈的表演與暴力行為的展示,伴隨著觀眾的高呼與應和而越發高漲,并逐漸有人加入到暴力之中,體驗站在舞臺中心享受話語權與關注度的優越感。暴力隧道也可能會從一個情境延展到另一個情境,誠如蘭德爾 ·柯林斯所言,“沒有暴力的個體,只有暴力的情境 ”。人們對暴力的發生充滿了緊張和恐懼,這種恐懼和緊張塑造了暴力情境,處于暴力情境中的人們最主要的情緒也是恐懼,而不是憤怒,因此人們面對暴力的第一反應不是渴望,而是逃離。但群體共同情感、目標和文化取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這種對暴力的緊張。娛樂型、榮譽性暴力表演就是將暴力限制在一定秩序里從而將其轉變成有組織的暴力儀式,使暴力雙方的注意焦點轉向周圍觀眾,從觀眾的圍觀和支持中吸取情感上的力量,從而化解緊張和恐懼情緒。這種暴力表演的觀點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擬劇論理論(dramaturgical theory)不謀而合。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巨大的舞臺,社會角色根據社
會規范的設定穿梭于前臺與幕后進行著自己的表演。
三
與歷史學者強調每一段歷史的獨特性、唯一性不同的是,歷史社會學者的研究旨趣不僅停留在對于歷史事實的還原或者社會現象的描述,更多的會希望去探尋與之相關的現象在歷史維度中的重復,以及事實和現象背后的 “機制 ”因果律問題。《意愿的沖撞》從私人之間的沖突推演到群體、社會的矛盾和沖撞,所勾勒出的暴力多發軔于相對地位的不確定的核心觀點,不僅適用于解釋十九世紀科西嘉的暴力沖突,在其他的歷史時空和政治場域里也同樣有所彰顯。
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楊 ·格羅斯(Jan T. Gross)在其代表作《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中,描繪了 “二戰 ”時期波蘭小鎮上的一段暴力歷史。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的一半居民謀殺了另一半居民 —小鎮一千六百名猶太人中僅有七人幸存,他們被以溺斃、燒死、棍打等各種殘忍的方式所殺害。而殺害他們的,不是二戰中 “罪惡 ”的納粹,而是真真實實與他們有過交集的熟人,他們的鄰人。
在屠殺發生以前,波蘭人和猶太鄰里之間關系友好,“鄰里之間的互動和聯系十分頻繁 ”。然而這種被描繪為 “田園牧歌 ”式的景象,卻被德國納粹和蘇聯交替控制的動蕩局勢所打破,在不同的軍隊武力控制時,兩個民族人民的權力對稱關系突然發生導致不對稱的變化,原本長期潛伏的民族情緒異化地發泄,群體沖突集中爆發,便演變成了不可逆的種族屠殺和民族情感傷害。雖然格羅斯認為 “大屠殺過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有其獨特的情景動力學;在每一個片段情節中,其場景中的不同演員都會做出許多特定的、獨立的判斷 ”,但我們不難在其中找到促使普通居民共同完成一場大屠殺的法則:在政治信號瞬息萬變、相對地位可能不斷波動的大背景下,過往穩定平衡的人際社會關系被打破而變得混亂模糊,雙方群體之間對關系的歧義認知促使沖突增多和加劇。而當鎮長號召所有波蘭人在廣場集合清剿猶太人時,無論這些波蘭人過去對于他們的鄰人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立場,他們在當下已經身處于波蘭人的共同體中,“波蘭人 ”的身份認同在廣場上得到穩固,沒有一絲重新認識 “鄰人 ” 身份的余地 —在以 “滅亡猶太人 ”為目標的群體行動中,沒有人會試圖拯救 “我們的鄰人 ”。
相比集體選擇的理性化,個人選擇更易顯現出機變性。在動蕩的政治環境中,原有秩序的崩壞無法彌合在不對稱性社會關系的順從模式下和平共存的身份和角色,造成了模糊的身份認同,行動者從而走入了小徑分岔的花園:出身好的人希望通過獲得更高的政治身份來得到政權的庇佑,獲得更多的資源;出身不好的人則希望通過脫離不好的出身以避免受到歧視甚至打壓。而要想在政治身份上更進一步,就需要表達忠心和熱情,政治運動中的積極表現便是表忠心的重要方式。在這種激勵制度的驅使下,暴力被視作正確。我們因此看到,在《受苦人的講述》一書中,社會學家郭于華深刻描繪出在陜北驥村的受苦人們如何參與到暴力之中,對地主及其家人進行刑罰。這種是否參與暴力成為界定群體邊界的關鍵標準,共同批斗地主加深了受苦人們作為被剝削被壓迫者的身份認同,也進一步使暴力得以扎根。
然而,歷史圖景并非永遠能夠形成清晰的對立,可選方案之間也并非永遠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很多時候存在于口號、標語、名稱等形式層面的差別實質產生于人為的建構與選擇。當暴力還埋藏于萌芽期的時候,一旦久已確立的既有關系發生變動,或者對社會地位的正當性基礎產生出有歧義的界定,深處歷史情境中的人們便開始做出回應性的選擇,選擇引向行動,行動塑造歷史。在這層意義上,古爾德對暴力及其內因的精妙分析,更加印證了莎士比亞的名言 —這些暴力的歡愉,終將導致暴力的結局。
(《意愿的沖撞:社會等級的歧義如何孕育沖突》,[美 ]羅杰 ·古爾德著,吳心越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 [美 ]楊·格羅斯著,張祝馨譯,中央編譯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