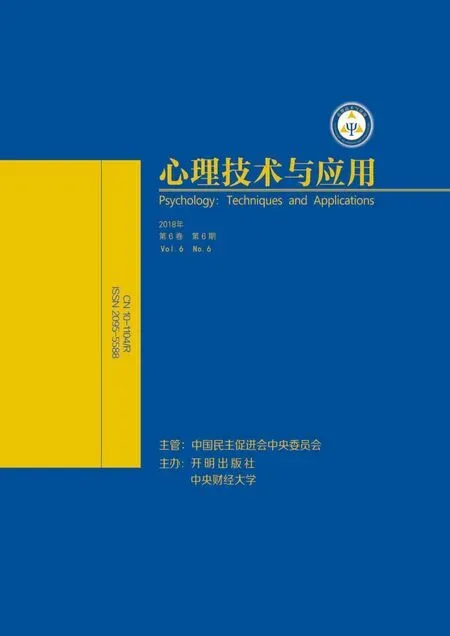性別刻板印象的激活對風險決策的影響
紀 薇
(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南京 210097)
1 引言
現實生活中,風險無處不在,我們總是面臨抉擇。根據A.H.威雷特(1901)在《風險與保險的經濟理論》一文中的觀點,風險是關于不愿發生的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之客觀體現。風險的出現通常意味著損失,或是未實現預期的目標值,而這一切往往是一種不確定性的隨機現象。不可否認,在有風險的情境下進行有效決策是我們的必備生活能力。風險決策是在損失或贏利、損失或贏利的權重及損失與贏利聯系的不確定性這三個要素中進行最優化的選擇(畢玉芳, 2006)。
早期的風險決策理論認為理性是客觀的,但是隨著新觀點的提出,可以發現在決策中人們并非只是簡單追求利益最大化,情緒情感因素、人格因素都可能對決策產生影響,這使得人們開始逐漸認識到心理因素在風險決策中的重要性(王曉利,2016;Cooper, Agocha, & Sheldon, 2000; Levin, Gaeth, Schreiber, & Lauriola, 2002; Nicholson, Soane, Fenton, & Willman, 2005)。研究表明,人類的決策行為是一種復雜的認知活動,包括對信息進行編輯、評價、采取行動、結果評估等各個階段,需要感知、記憶、問題解決等各種能力協同作用(Fellows, 2004)。已有研究都表明人格(氣質、性格、自我調控系統)與風險決策有關。比如,人格特質與不同的損益條件、框架效應類型中的風險決策有關,不論在正性框架還是負性框架下,具有低外傾性、高開放性、低責任心、高直覺性的被試都更傾向于冒險(Levin, Gaeth, Schreiber, & Lauriola,2002);此外,人格與情緒交互作用影響風險決策,神經質的人傾向于以冒險行為來處理負面情緒,而外向型的人傾向于以冒險行為增強積極情緒體驗(Cooper, Agocha, & Sheldon, 2000)。這些研究都表明人們對于自身的態度和行為風格與決策行為有關,但是具體影響機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探索。
關于風險決策的測量,研究者推出一種仿真氣球冒險任務(BART,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因為該任務是一個動態的風險決策過程,所以更接近現實生活中真實風險決策的認知任務模式(Lejuez, Read, Kahler, Richards, Ramsey, Stuart,... & Brown, 2002)。在該任務中,仿真氣球將呈現在計算機屏幕上,被試需要通過按鍵逐漸吹大這個氣球,每吹一次氣球都會有一定的收益,但與此同時也有氣球爆破的風險。被試可能獲得的收益會隨著氣球增大而增大,但氣球被吹爆的風險也會增高,如果該氣球被吹爆,則其收益就為零或負值。被試可以選擇隨時停止吹氣球來接受目前的收益。該任務需要被試連續地決策是選擇繼續冒險還是停止冒險以獲得當前的收益。BART任務能提供多個行為指標來測量個體的風險決策行為,比如在BART任務中未爆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和吹爆氣球的個數,這兩個指標可以用來測量被試的偏好水平,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越多,吹爆氣球的個數越多,個體的風險偏好水平便越高(Baker & Maner, 2009; Bornovalova, Cashman-Rolls, O’Donnel, Ettinger, Richards,... & Lejuez, 2009; Dean, Sugar, Hellemann, & London, 2011; Lejuez, Aklin, Zvolensky, & Pedulla, 2003)。
性別刻板印象是社會生活中被人們所廣泛接受的對于男性及女性的固定看法,往往會對人們的認知和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徐大真, 2003),這種影響總是在無意識狀態中產生(Devine, 1989)。人們傾向于選擇與自己的性別相符的行為,避免與自己性別不符的行為。更進一步的證據顯示,人們會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受到被廣泛接受的刻板印象的影響(Devine, 1989; Nosek, Banaji, & Greenwald, 2002)。然而,性別刻板印象常常與客觀事實不符,這會導致人們對于性別群體的認知過于簡單化,從而引發偏見,或使某一群體受到不公正對待,或在自我證言中失去個性的色彩(Hilton & Hippel, 1996)。在以往研究中,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證據表明當人們被他人驅使意識到普遍的性別刻板印象時,他們往往以同性別刻板印象相似的方式行動(Banaji & Greenwald, 1995)。
但是一些最近的證據顯示,人們可能不會接受刻板印象并甚至會以刻板印象相反的方式行為(Dijksterhuis, Spear, & Lépinasse, 2001; Moskowitz, & Skurnik, 1999)。 具體說來,刻板印象的激活增加了人們對于刻板印象組群的認知(Wheeler, Javis, & Petty, 2001),從而影響了人們對于相關任務的態度和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人們不認為屬于他們組群的刻板印象是真實的情況下,刻板印象的激活都會影響他們的態度和行為。例如,在一個困難的口頭測試中,即使測試沒有被指出是對智力的評斷,也會使黑人被試的行為受到影響。研究通過呈現刻板印象創造出自我威脅的困境,被試的表現可以證明刻板印象的自我特征(Steele, & Aronson, 1995)。
在過去的研究中,人們普遍形成關于風險決策行為的性別刻板印象,在進行決策時,男性較為獨立,有主見,更為勇敢,傾向于冒險,而女性較為被動,依賴性大,易受暗示,決策更加保守和膽怯(Cummings & Melanie, 1997)。所以可以推定在沒有接受相應的刻板印象的激活的情況下,男性的風險偏好水平會大于女性。
根據刻板印象激活的方式(或內隱激活或外顯激活),人們要么會確認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同化),要么會否定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對比)(Shih, Ambady, Richeson, Fujita, & Gary, 2002)。曾有研究表明,性別刻板印象的激活方式會影響人們對于性別刻板印象的反應,內隱的激活方式會使人們按照性別刻板印象行動,但是外顯的激活方式會使人們采取相反的方式(Kray, Thompson, & Galinsky, 2001; Shih, Ambady, Richeson, Fujita, & Gray, 2002)。例如,在性別刻板印象影響談判表現的研究中,當談判被暗示與性別特征(男性更優秀)有關時,男性的表現會優于女性,即刻板印象被隱形激活時被試會確認刻板印象,但是當刻板印象被明確提及時,人們會表現出對刻板印象的抗拒,或者表現出與刻板印象不一致的行為傾向(Kray, Thomson, & Galinsky, 2001)。
內隱刻板印象激活會使人們被刻板印象同化,因為人們對他們完成這項任務的能力的期待往往和所屬群體對這項任務的期待聯系在一起(Brown & Day, 2006; Cadinu, Maass, Rosabianca, & Kiesner, 2005; Steele & Aronson, 1995; Stone, Lynch, Sjomeling, & Darley, 1999)。根據角色一致性理論,當任務特征與他們群組的性別刻板印象相符時人們傾向于表現的更好(比如,男性在數學領域),同時當任務特征與他們群組的性別刻板印象不符時人們傾向于表現的更差(例如,女性在數學領域)(Eagly & Karau, 2002)。然而,當人們被直接呈現刻板印象的信息時,當人們將他們自己與刻板印象進行比較并表現的與激活的態度不符時,它會導致心理上的不適(Festinger & Hutte, 1954; Martin, 1986)。具體來說,當人們直接意識到他人對自己的行為保持高度期待時,他們會感到心理壓力因擔憂如何滿足高標準而增加,從而導致他們的表現變差(Baumeister & Showers, 1986)。例如,當一種關于數學的性別刻板印象(男性擅長數學,而女性并不適合數學)被隱性激活時,相比于性別刻板印象沒有被激活時,男性表現的更好,而女性表現的更差(Brown & Josephs, 1999; Keller & Dauenheimer, 2003)。而且,當人們明確地意識到別人對他們的期望值較低時,他們會強烈地反對負面的刻板印象,以證明這種成見是不真實的(Kray, Thompson, & Galinsky, 2001)。因此,根據上述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刻板印象激活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的反應,刻板印象的內隱激活導致人們會接受其影響做出相應的行為,而外顯激活則會產生相反的作用。過去有學者指出需要在同一研究中比較性別刻板印象的內隱激活(在社會中相當常見)和外顯激活(相對來說不常見)的影響(Brown & Day, 2006; Shih, Ambady, Richeson, Fujita, & Gary, 2002),但這種研究還比較稀少。盡管如此,Kray等人(2001)發現當男性刻板印象被內隱激活時男性在競爭性談判任務中表現的更好,但同樣的刻板印象被外顯激活時,女性比男性表現的更好,在模擬銷售中可以得到更高的報價。
所以根據過往研究中不同激活方式帶來的不同反應類型,可以認為風險偏好水平在面對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時會有相似的反應模式,因此假設男性在接受了性別刻板印象時,如果以外顯的激活方式,其風險偏好水平可能會低于內隱激活方式。而女性在接受性別刻板印象時,如果以外顯的方式,其風險偏好水平可能會高于內隱激活方式。
內隱刻板印象的激活主要是通過使用具有刻板印象的形容描繪任務來進行。例如,Kray、Reb、Galinsky和Thompson(2004)描述了一位理性和自信的高效談判者(男性刻板印象)。同隱形刻板印象的激活的區別在于,顯性刻板印象的激活更進一步明確的將刻板印象的特征和相應的組群聯系起來。研究認為,取決于刻板印象是以內隱或外顯形式激活,人們會或者接受或者拒絕刻板印象(Shih, Ambady, Richeson, Fujita, & Gary, 2002)。在研究中,Shih等人(2002)認為自我關聯在此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們通過明確的將亞裔美國人描述為“安靜”、“小氣”和“謙虛”來比較SAT成績的方法證明了這點,當刻板印象以隱性方式激活時,被試的SAT表現得到了提升,而當刻板印象被公然激活時卻沒有得到相同的效果。由此,本研究擬采用相似的方法,用具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形容描述任務的方法來完成激活。
綜上,本研究假設性別刻板印象的激活在一定程度上會對風險決策行為產生影響。進而提出相應的假設:(1)當男性和女性沒有接受性別刻板印象信息時,男性的風險偏好水平高于女性。(2)被試的性別和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會產生交互作用。男性在接受男性刻板印象的內隱激活時比外顯激活時的風險偏好水平高,女性在接受女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激活時比內隱激活時的風險偏好水平高。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被試共計本科生320名,男生160人,女生160人,年齡范圍在19~23歲之間。被試基本情況沒有很大差異,施測時均未吸煙和飲酒,無神經系統疾病。最終得到320份有效數據。
2.2 實驗設計
本研究采用2×5的被試間實驗設計。自變量為性別(男,女)和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情境(控制組、外顯男性性別刻板印象、內隱男性性別刻板印象、外顯女性性別刻板印象、內隱女性性別刻板印象)。因變量是未爆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吹爆氣球的個數。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越多,吹爆氣球的個數越多,意味著被試的風險偏好水平越高。
2.3 實驗材料
2.3.1 刻板印象激活情境材料
被試將被隨機分配五種刻板印象激活情境中的一種,他們將閱讀1篇300字左右的文章(注:材料見附錄1)。文章閱讀完畢后要求他們回答兩道問題,涉及文章的主要內容和讀后感,從而確保被試有認真閱讀此文章。
在控制組情境下,被試閱讀的文章是有一篇童話故事《跳舞熊》,沒有提及性別差異。在兩種男性性別刻板印象情境中,被試將閱讀關于施瓦辛格的介紹,提及男性具有這樣的性格特征——膽大的、冒險的、主動的。在兩種女性性別刻板印象情境中,被試將閱讀關于特瑞莎修女的簡介,提及女性具有這樣的性格特征——耐心的、細心的、團隊合作的。在外顯刻板印象中,明確指出這是具有哪種性別的特征,在內隱刻板印象不明確指出。
2.3.2 仿真氣球實驗任務(BART)
BART任務是由Lejuez等(2002)發明的,目的是測量個體的風險決策行為。在 BART 任務(見圖1)中,被試需要通過點擊氣球來吹氣球,每吹1 次盈利0.2枚金幣,每個氣球可吹的次數介于1~128 次之間,單個氣球最多可盈利25.4枚金幣,平均爆破點為64 次,被試在吹氣球過程中,可以隨時停止按鍵并保存收益。如果被試吹氣球的次數達到了氣球的爆破點,氣球會爆,并伴隨有爆破聲,當前氣球的臨時收益變為零,并從之前的累計收益中扣除與當前氣球臨時收益相同的金額。本任務使用Java語言在安卓系統上編制。

圖1 BART任務示意圖
2.4 實驗程序
實驗者將被試引入實驗室,被試被告知實驗的目的是為了了解被試的性格特征,全部實驗均在安靜的環境中完成。被試坐在桌前,首先會發給被試一篇文章(隨機分配),要求被試閱讀,讀完文章后要求被試完成一道關于文章內容的題目以確保他們有仔細閱讀(通過檢查被試題目的回答質量判斷全部被試均已認真閱讀)。然后給被試裝有安卓系統的平板電腦,令其完成BART任務。
在BART中,共包含30個氣球。要求被試點擊氣球來吹大氣球, 按氣球下方的“save”鍵累積收益,氣球的下方將顯示當前氣球的點擊次數和盈利,在程序界面的左下角會顯示氣球的總盈利。正式實驗開始前,給被試呈現指導語和5個氣球用來練習,保證被試完全理解實驗任務。實驗還告知被試實驗中的盈利是虛擬的金錢獎賞,要求被試將其想象為真實金錢,并盡可能盈利。在實驗結束后為被試提供相同的禮品。
3 實驗結果
3.1 不同性別、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情境下的風險行為
為了驗證實驗假設,采用了2(性別)×5(實驗情境)的兩因素方差分析比較了不同性別下,采用不同的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情境時,未爆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和吹爆氣球的個數這兩個BART分數指標的差異。表1、表2呈現了不同情境下男生和女生在風險行為上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表1 不同情境下吹爆氣球的個數的統計結果(M,SD)

項目無刻板印象情境男性刻板印象外顯情境內隱情境女性刻板印象外顯情境內隱情境男性(N=32)13.15,3.5415.45,2.9212.62,5.2510.59,3.3015.08,3.70女性(N=32)9.61,4.7912.15,6.4610.70,4.578.79,3.5410.58,3.17
表2 不同情境下未爆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的統計結果(M,SD)

項目無刻板印象情境男性刻板印象外顯情境內隱情境女性刻板印象外顯情境內隱情境男性(N=32)41.91,10.7851.53,34.1141.21,10.8334.33,13.3446.08,10.15女性(N=32)33.20,12.3234.11,11.1941.21,11.9234.35,13.2046.17,11.83
通過計算,我們可以看出性別的主效應十分顯著,男性的未爆氣球被吹的平均個數比女性高(42.3 vs. 34.0),且差異顯著,F(1,319)=41.20,p<0.01,η2=0.12;男性吹爆氣球的個數也比女性高(13.2 vs. 10.4),且差異顯著,F(1,319)=34.64,p<0.01, η2=0.10。這表明男性的風險決策傾向普遍高于女性。
結果還發現,不論是吹爆氣球的個數(F(4,319)=10.12,p<0.01,η2=0.12)還是未爆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F(4,319)=7.12,p<0.01,η2=0.08),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情境的主效應均顯著.但是關于未爆氣球氣球被吹的平均次數,兩者的交互效應顯著,F(4,319)=7.14,p<0.01,η2=0.08;可是關于未爆氣球的個數,兩者的交互效應并不顯著。因而假設沒有完全得到支持,但是刻板印象的激活情境的確對風險決策行為產生了影響,而且性別和刻板印象的激活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
此外,我們在每一個性別組內進行了進一步的檢驗。
對因變量的兩個指標分別進行簡單效應檢驗后發現:關于氣球未爆的個數,在男性樣本中,不同刻板印象激活的情景差異顯著,F(4,310)=9.18,p<0.01,而女性樣本中差異顯著性較低,F(4,310)=2.68,p=0.032<0.05。其中,男性樣本在男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情境下普遍高于女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情境,同時在女性刻板印象的內隱情境下普遍高于外顯情境,且差異均顯著,(p< 0.01);關于未爆氣球的平均被吹次數,在男性樣本中,不同刻板印象激活的情景差異顯著,F(4,310)=14.15,p<0.01,而女性樣本中差異并不顯著,F(4,310)=0.11,p>0.05。其中,男性樣本在男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情境下普遍高于女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情境(p<0.01),在接受外顯的男性刻板印象時比內隱的風險偏好水平高(p<0.01)。但是在女性樣本中,各種激活情境均不顯著。這表明,激活性別刻板印象的類型會影響被試的風險行為,但存在較大的性別差異。男性在接受不同類型的性別刻板激活時風險決策行為存在顯著差異,男性的風險偏好水平在顯性激活男性性別刻板印象時要比在隱性激活男性性別刻板印象時更高。但是在女性被試中并沒有發現相似的結論。
此外,可以從表1和表2中看出,女性在接受內隱的女性刻板印象時比外顯的風險偏好水平高,但差異均不顯著。
4 討論
在以上研究中,我們探討了性別刻板印象的激活(顯性和隱性)對于男性和女性的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實驗結果基本符合預期,但部分未達到顯著性差異,可能導致此現象的原因很多,比如被試人數過少,因為在研究中發現隨著實驗的進行,被試越多結果越趨近于顯著。
首先,總體上男性的風險偏好普遍高于女性。曾有一系列研究證明個體對風險的知覺、對受傷風險的估計和對行為后果的歸因是造成冒險行為性別差異的主要原因(Hillier & Morrongiello, 1998)。具體來說,男性、女性對于不同的風險情境的認知是一樣的,但是女性對于風險的知覺更為細膩,并且對于風險的估計也更為謹慎。此外,相關研究表明男女兩性的人格特征及行為反應方式存在明顯差異。男性較為獨立,有主見,更為勇敢,傾向于冒險,而女性較為被動,依賴性大,易受暗示,決策更加保守和膽怯(Cummings & Melanie, 1997)。這些觀點與我們的研究結果相符,在仿真氣球冒險任務中男性的風險偏好水平顯著高于女性。
其次,總體上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情境的主效應是顯著的,但是在男性被試中,不同情境引起的差異是顯著的,而女性被試中并沒有顯示出相似的結果。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刻板印象,在這種現象上男女兩性之間存在著差異(Stangor & Duan, 1991)。其中一種解釋是提取理論認為團體內部成員掌握本團體的信息多于其他團體,提取也更快,這是因為他們與本團體成員的交往多于其他團體成員,另一種解釋是,自尊理論認為團體的成員為了保護自尊認為本團體比其他團體具有更多更好的特征(徐大真, 2003)。同時,當今社會仍然由男性掌握著核心的生產力,所以社會普遍對男性寄予更高的期望,他們必須承擔起家庭、社會的重擔,社會給予了男性更多的壓力,這導致他們在社會發展中害怕、擔憂的更多,擔心自己沒有成功展現出社會期待的“男子漢”氣質,從而限制了他們的發展,所以,他們會更傾向于服從性別刻板印象的形象,在自我報告時表現出相應的冒險傾向。而女性隨著社會的開放,發展的更為自由,有著中性化發展的趨勢,這使她們開始逐漸突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因此女性在不同的實驗情境下差異不如男性顯著。而且在本研究中,需要注意到的一點是男性在男性刻板印象顯性激活條件下比隱性激活的風險偏好更大,這與假設并不一致,而且男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情境下普遍高于女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情境。這可能便是因為男性由于社會所賦予的壓力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更大,更傾向于符合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男性顯性刻板印象激活條件下,男性角色與高冒險傾向緊密相連,為了迎合社會期待,男性被試會在測試中表現出更高的風險偏好;而在男性刻板印象隱性激活條件下,男性被試所感受到的性別角色期待的壓力較小,相對而言風險偏好水平也就有所下降。這可能導致了結果與假設的差異。同時女性在接受女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激活時比內隱激活時的風險偏好水平高,但是差異并不顯著,這可以體現出女性的刻板化程度低于男性(Alpert & Breen, 1989)。
本研究的假設最初認為,性別刻板印象可能會在無意識間影響態度和行為(Steele & Aronson, 1995),然而沒有得到相同的結論。盡管刻板印象曾被認為是相對堅固和不可改變的,研究者們認為通過顯性地呈現有關刻板印象的形容可以中和刻板印象對與態度和行為的影響(Smith & Johnson, 2006)。 所以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添加中性性別組,將任務與男性和女性的中性特征相聯系,以探討被試自身所具有的刻板印象是否能在短期內被中和。而且,在本研究中結果是在情境激活后立即收集的,可以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該效應可以持續多長時間,以及如何維持激活效應。
除此之外,本研究存在一些問題可以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探討。首先,本研究的被試出于研究便利的考慮主要集中在在讀大學生上,知識水平、生活背景等較為集中,但是個體的刻板印象與本身的生活背景、家庭環境、文化程度等都是密切相關的,對于本次研究被試90后在校大學生來說,所體驗的性別角色和社會分工的體驗可能存在相應的限制,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希望可以擴大研究對象的范圍,如可以涉及到文化知識匱乏者或者不同年齡階段的被試等,以觀察他們是否遵循著同樣的行為模式。在本研究中結果是在情境激活后立即收集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該效應可以持續多長時間,以及如何維持激活效應。此外,在之前的研究中學者們認為刻板印象的激活并不會對所有人產生同樣的影響(Brown & Pinel, 2003),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進一步調查個體差異對刻板印象激活結果影響的調節作用。
5 結論
研究發現,男性在接受不同類型的性別刻板激活時風險決策行為存在顯著差異,男性在接受外顯的男性刻板印象時比內隱的風險偏好水平高。女性在接受不同類型的性別刻板印象激活時差異雖不顯著,但是在接受女性刻板印象的外顯激活時比內隱激活時的風險偏好水平低。
畢玉芳 (2006). 情緒對自我和他人風險決策影響的實驗研究. 碩士學位論文, 華東師范大學.
王曉利 (2016). 情緒和情緒調節對風險決策的影響及其神經基礎. 心理技術與應用, 4(2), 97-101.
徐大真 (2003). 性別刻板印象之性別效應研究. 心理科學, 26(4), 741-742.
Alpert, D., & Breen, D. T. (1989). "liberali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34(2), 154-160.
Baker, M. D., & Maner, J. K. (2009). Male risk-taking as a context-sensitive signaling dev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5), 1136-1139.
Banaji, M. R., & Greenwald, A. G. (1995).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ing in judgments of fa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68(2), 181-198.
Baumeister, R. F., & Showers, C. J. (1986). A review of paradoxical performance effects: choking under pressure in sports and mental tes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6(4), 361-383.
Brown, R. P., & Day, E. A. (2006). The difference isn’t black and white: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race gap on raven’s advanced progressive matric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4), 979-985.
Brown, R. P., & Josephs, R. A. (1999). A burden of proof: stereotype releva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th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76(2), 246-257.
Brown, R. P., & Pinel, E. C. (2003). Stigma on my mi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ence of stereotype threa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39(6), 626-633.
Bornovalova, M. A., Cashman-Rolls, A., O’Donnell, J. M., Ettinger, K., Richards, J. B., Dewit, H., & Lejuez, C. W. (2009). Risk taking differences on a behavioral task as a function of potential reward/loss magnitud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ulsivity and sensation seeking. Pharmacology Biochemistry and Behavior, 93(3), 258-262.
Cadinu, M., Maass, A., Rosabianca, A., & Kiesner, J. (2005). Why do women underperform under stereotype threat?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negative think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16(7), 572-578.
Cooper, M. L., Agocha, V. B., & Sheldon, M. S. (2000). A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on risky behaviors: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and affect regulatory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68(6), 1059-1088.
Cummings, B., & Melanie. (1997). Women who do too much (or feel guilty if they don’t). Herizons.
Dean, A. C., Sugar, C. A., Hellemann, G., & London, E. D. (2011). Is all risk bad? Young adult cigarette smokers fail to take adaptive risk in a laboratory decision-making test. Psychopharmacology, 215(4), 801-811.
Devine, P. G. (1989).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their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6(1), 5-18.
Dijksterhuis, A., Spears, R., & Lépinasse, V. (2001). Reflecting and deflecting stereotypes: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and automatic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7(4), 286-299.
Eagly, A. H., & Karau, S. J. (2002). Role congruity theory of prejudice toward female leaders. Psychological Review,109(3), 573-598.
Fellows, L. K. (2004).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human decision making: a re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Behavioral &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iews,3(3), 159-172.
Festinger, L. & Hutte, H.A. (1954).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unstab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a group.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4, Pt.1), 513-522.
Hillier, L. M., & Morrongiello, B. A. (1998).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chool-age children’s appraisals of injury risk.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23(4), 229-238.
Hilton, J. L., & Hippel, W. V. (1996). Stereotyp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47, 237-271.
Keller, J., & Dauenheimer, D. (2003). Stereotype threat in the classroom: dejection mediates the disrupting threat effect on women’s math performance. Pers Soc Psychol Bull,29(3), 371-381.
Kray, L. J., Reb, J., Galinsky, A. D., & Thompson, L. (2004). Stereotype reactance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the effect of stereotype activation and power on claiming and creating value.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0(4), 399-411.
Kray, L. J., Thompson, L., & Galinsky, A. (2001). Battle of the sexes: gender stereotype confirmation and reactance in negoti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6), 942-958.
Lejuez, C. W., Read, J. P., Kahler, C. W., Richards, J. B., Ramsey, S. E., Stuart, G. L.,... & Brown, R. A. (2002). Evaluation of a behavioral measure of risk taking: The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BAR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8(2), 75-78.
Lejuez, C. W., Aklin, W. M., Zvolensky, M. J., & Pedulla, C. M. (2003). Evaluation of the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BART) as a predictor of adolescent real-world risk-taking behaviou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6(4), 475-479.
Levin, I. P., Gaeth, G. J., Schreiber, J., & Lauriola, M. (2002). A new look at framing effects: distribution of effect siz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ndependence of types of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88(1), 411-429.
Martin, L.L.(1986). Set / reset: use and disuse of concept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1(3), 493-504.
Moskowitz, G. B., & Skurnik, I. W. (1999). Contrast effects as determined by the type of prime: trait versus exemplar primes initiate processing strategies that differ in how accessible constructs are us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76(6), 911-927.
Nicholson, N., Soane, E., Fenton-O’Creevy, M., & Willman, P. (2005). Domain specific risk taking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8(8), 157-176.
Nosek, B. A., Banaji, M., & Greenwald, A. G. (2002). Harvesting implicit group attitudes and beliefs from a demonstration web site.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6(1), 101--115.
Shih, M., Ambady, N., Richeson, J. A., Fujita, K., & Gray, H. M. (2002). Stereotype performance boosts: the impact of self-relevance and the manner of stereotype ac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83(3), 638-647.
Smith, J. L., & Johnson, C. S. (2006). A stereotype boost or choking under pressure? positive gender stereotypes and men who are low in domain identification. Basic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8(1), 51-63.
Steele, C. M., & Aronson, J. (1995).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of afr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69(5), 797-811.
Stone, J., Lynch, C. I., Sjomeling, M., & Darley, J. M. (1999). Stereotype threat effects on black and white athlet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77(6), 1213-1227.
Stangor, C., & Duan, C. (1991). Effects of multiple task demands upon memory for information about social 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7(4), 357-378.
Wheeler, S. C., Jarvis, W. B. G., & Petty, R. E. (2001). Think unto others: the self-destructive impact of negative racial stereotyp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37(2), 173-180.
Willett, Allan, H.(1901). The Economic Theory of Risk and Insurance. Ph. D. 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