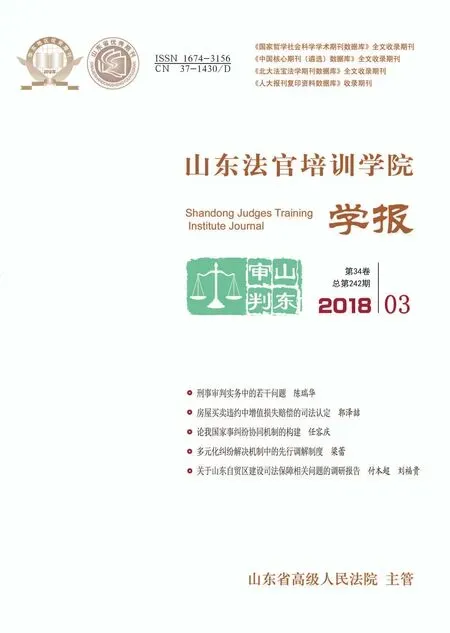論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保護規則的司法續造
——以《民法總則》第十六條為切入
文曉威
引 言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諸如“交通肇事”“醫療不當”“環境污染”等意外事故頻頻發生,侵害未出生獲得獨立生命的胎兒權益的情形也越來越多。由于在我國民事法律領域,除了《繼承法》第28條通過擬制胎兒為特定情形下的繼承主體外,對胎兒利益直接加以明文保護的規定幾乎趨于空白,導致審判實踐中對胎兒權益救濟不力的情形時有發生。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民法總則》第16條,是我國第一次從法律上對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作出規定,賦予了胎兒準人格權a楊立新:《〈民法總則〉中部分民事權利能力的概念界定及理論基礎》,載《法學》2017年第5期。,彌補了我國立法對胎兒利益保護的空白。然而此條文本身并不足以涵蓋胎兒利益保護之全部,對胎兒損害賠償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未予明文規定,存在諸多漏洞和法律適用上的困惑。這就需要法官在司法實務中,把握法律解釋的尺度,填補法律規則的漏洞,以提升裁判的統一性和可期待性,通過法之續造來完善和發展我國胎兒利益保護體系,切實保障胎兒權益,彰顯民法人文關懷。
一、實務考察:法律缺失情境下胎兒權益保護之探索
(一)經典案例評析
【案例一】王德欽與楊德勝等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b《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6年第3期(總第113期)。
2002年4月27日,楊德勝駕車將行人王先強撞到,經搶救無效死亡。王德欽之母牟萍系王先強多年同居生活女友。事故發生時,牟萍已懷孕。后經醫學鑒定,王先強確系王德欽的親生父親。牟萍生育王德欽后代其起訴,要求楊德勝等賠償撫養費及精神撫慰金。法院審理認為,王德欽與王先強之間的撫養關系因血緣關系客觀地、不可改變地存在,并不因胎兒出生的早晚或是否婚生而發生實質性變化,王德欽應視為死者王先強生前實際應當撫養的人,故對原告撫養費的請求予以支持,但對精神撫慰金主張未予認可。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胎兒出生后是否有權就其受孕期間遭受的不法侵害主張損害賠償。在本案審判當時,由于《民法通則》及其他民事立法的粗疏,沒有對“未出生胎兒的正當權益是否受民法保護”問題給予明確回答。然而,審判實務要求人民法院必須對胎兒群體的司法需求予以恰當回應。承辦法官基于原告與死者之間的撫養關系并不因“原告出生的早晚發生實質性變化”這一基本事實,對《民法通則》第119條中的“死者生前扶養的人”作了擴大解釋,認為其內涵不僅包括“生前實際扶養的人”,還包括“生前實際應當扶養的人”。這種解釋完全符合生命平等保護的民法精神,是司法實務中填補法律漏洞,探索胎兒利益保護路徑的有力嘗試。本案被作為指導性案例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其裁判方法在審判實務中被予以借鑒,為《民法總則》第16條的出臺積累了廣泛的司法實務經驗。
【案例二】裴紅霞等與錢明偉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c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法院(2001)濱馬民初字第129號民事判決書。
2001年7月27日,懷孕6個月的裴紅霞散步時被錢明偉駕駛的摩托車撞擊了腹部,雙方爭吵后相繼離開。第二日凌晨,裴紅霞突發不適被送往醫院,進行保胎治療,于8月8日早產下女兒吳佩穎,其因身體免疫力低住院治療14天。裴紅霞等訴至法院請求侵權損害賠償。被告抗辯,孕婦裴紅霞在碰撞發生一天二夜后出現情況異常,胎兒早產并非直接因其駕駛摩托車碰撞所導致。審理法院認為碰撞與早產之間有因果關系,但未出生胎兒不具有法律上“人”的身份,出于對胎兒的利益的保護,采用了變通辦法即通過支持其母親的醫療費等損失予以保護。
本案雖沒有承認胎兒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法官采用了“支持母體的主張來填補胎兒權益的損害”的變通辦法,達到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此外,侵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也是本案另一爭議焦點。因果關系是指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相互關系,理論上主要存在兩種學說。一是必然關系學說,主張只有此種“相互關系”是內在的、必然有聯系的,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二是相當因果關系說,由“條件關系”和“相當性”兩部分構成,前者是以“若無此行為,必不發生此種傷害”為認定標準,后者是指對行為人造成的客觀事實,依據一般人的知識經驗判斷,也具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的可能性。d王澤鑒:《侵權行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6頁。本案法官認為傳統的必然因果關系說縮小了責任的客觀基礎和范圍,基于保護胎兒利益的目的考量,利用法的價值判斷對案件事實進行適度的擴大,實現了因果關系認定的科學與公正。
(二)實證樣本評析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輸入“胎兒利益”檢索,12篇e數據來源: http://wenshu.court.gov.cn/list/list/?sorttype=1&conditions=searchWord+QWJS+++全文檢索:胎兒利益,2017年8月28日訪問。為直接涉及胎兒權益受到侵害的糾紛。筆者立足于此12篇裁判文書對當前胎兒權益保護現狀進行分析,發現司法實務中胎兒損害賠償糾紛呈現如下特性:
1.案件類型多元化。由于醫學的不斷進步,對于胎兒損害與出生前侵害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確定發展迅速,加之人們的權利意識逐漸增強,近年來涉及胎兒權益案件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12篇裁判文書中,從案由上來看:1件為繼承糾紛、2件為人格權糾紛、3件為物權糾紛、6件為侵權責任糾紛(如圖一) ;從侵害產生的事由來看: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案件為1件、因繼承和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的案件各2件、因提供勞務引起的案件為3件,因交通事故引起的案件為4件(如圖二)。

圖二:侵害事由整體情況
2.訴求支持單一化。通過對樣本的實證分析,筆者發現,盡管當前涉及胎兒利益的案件在類型上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但審判實務中對胎兒訴求的支持情況卻存在矛盾的單一化情形。12篇裁判文書中,支持胎兒請求主張的案件為8件,占比為67%;未支持的案件為4件,占比為33%(如圖三)。在胎兒請求主張獲得支持的8件案件中,均為涉及胎兒人身權益的案件,其中7件的訴請內容為被撫養人生活費;未獲得支持的4件案件則均為涉及胎兒財產性權益的糾紛。

圖三:裁判結果情況
為剖析造成上述特性的原因,筆者從胎兒請求主張獲得支持的8件案件中,列舉4件有代表性的案件加以分析(如表一);從未獲得支持的4件案件中,列舉2件加以分析(如表二)。

表一:胎兒主張獲得支持的案例

表二:胎兒主張未獲得支持的案例
從以上司法案例可以看出,在法律缺失的情境下,法官們做了大量積極而大膽的探索,他們借助法律解釋、類推適用、法益衡量、價值判斷等豐富的法之續造方法,填補法律漏洞,處理實務難題,完成法之續造,推動了我國胎兒權益保護的發展。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胎兒權益保護立法的空白是造成涉及胎兒利益糾紛案件類型多元化,但訴求支持單一化的根本原因。《民法總則》第16條的出臺終結了這一立法空白,但單一的法律條文尚不足以回應胎兒權益保護的全部問題,法律對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保護依舊存在諸多漏洞,體系完善之路任重道遠。
二、漏洞所在: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法律保護之困境
(一)立法模糊:未確立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權利
在《民法總則》制定過程中,雖然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對應規定胎兒權益保護條款無太大爭議,但對應采取何種立法模式存在不同觀點。新法拋棄了傳統的“總括的保護主義”和“個別的保護主義”,最終采取了折中模式,以“娩出時為活體”為條件,賦予胎兒部分民事權利能力。條文中列舉了“遺產繼承”和“接受贈與”兩項具體事項,同時在文字表述上又使用一個“等”字將保護范圍未予封閉。該種做法兼具了兩種傳統模式的優點,值得推崇。然而迫切需要加以保護的胎兒“損害賠償請求”內容未予以明確列舉,沒有寫進“權”字,表明法律對其保護就沒有達到理想標準。即使條文中的“等”字存在予以擴充解釋的可能性,也可能因為法官能力素養及經驗閱歷的個體差異作出不同的解釋,這無疑將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分歧。
(二)要件缺失:未構建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
請求權基礎是行使請求權的必然前提。司法實務中,尋找請求權基礎的過程通常被稱為“找法”。胎兒權益遭受損害時,如何能得到法律上的救濟,最關鍵就在于“找法”環節,即能否在現行民事法律規范中找到請求侵權人賠償之依據。關于胎兒遭受他人侵害之損害賠償,《民法總則》第16條不足以作為行使請求權的依據,需要結合《侵權責任法》中關于侵權行為成立的規定,才能構成請求權基礎。然而,由于胎兒本身的特殊性,造成侵害胎兒權益的行為與一般的侵權行為相比呈現其自身的特點。第一,侵害行為的間接性。一般侵害行為都是直接實施于受害客體,但是針對胎兒的侵害行為最初作用在胎兒的父、母,尤其是母,間接的影響胎兒。第二,損害事實的間隔性。一般侵權行為在行為發生后即造成損害事實,但針對胎兒的侵害行為發生在受胎過程中,需等到胎兒出生乃至成長一段時間后才能確定。第三,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因為侵害行為并不直接作用于胎兒本身,胎兒遭受的損害與侵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之認定,是司法實務中面臨的一大難題。由于缺少對胎兒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的特別規定,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尚未完全構建,將在司法實踐中制約請求權的行使,不利于胎兒權利的保護。
(三)范圍爭議:未明確胎兒應受保護利益的范圍
由于胎兒不同于自然人,不具有完整的民事主體資格,僅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情形下,享有部分民事權利能力。那么,胎兒在遭受何種利益損害的情形下可行使賠償請求權?王利明教授認為,在胎兒諸多利益中,僅身體健康屬于被保護的對象。f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典·人格權法編(草案)建議稿》,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頁。徐國棟教授列舉了“繼承、遺贈、贈與”三種財產性利益應受保護。g徐國棟主編:《綠色民法典草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楊立新教授認為,胎兒基于其部分民事權利能力所享有的權利應包括繼承權、遺贈權和受贈與權、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撫養損害賠償請求權、身份權請求權。h楊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要義與案例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94頁。對胎兒“部分”民事權利能力的范圍如何進行外延和內涵上的界定,新法中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參考,條文的“等”字也產生了法律適用上的困惑,甚至參與草案起草的專家也各執一詞,這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規則本身的生存危機。
(四)規則不明:未規范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行使
1.行使時間不明。對胎兒行使權利的時間問題,理論上一直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當下醫學技術對胎兒損害的鑒定,除了明顯的肢體缺陷外,多數損害只能在其出生后才能鑒別,故他們贊同權利行使的時間應該在胎兒出生以后;另一種觀點認為,為了不延誤索賠的時機,在胎兒出生前即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請求賠償,若胎兒出生時為死體的,賠償人可以不當得利為由要求胎兒的法定代理人返回之前取得的賠償。i成繼平:《淺議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載《法制與經濟》2013年總第339期。理論之爭是否可以因《民法總則》第16條的出臺得以休止。條文的規定是否可當然解釋為胎兒行使權利的時間應當在其出生以后。單一條文本身并不能對上述問題給予正面回答。
2.行使主體不明。涉及胎兒利益案件中訴訟主體的確定是司法實務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缺乏明確的規則對請求權行使主體予以規范。通常認為,以胎兒是否出生為時間界點,行使主體應當有所不同。胎兒出生前,無法行使權利,必須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行使;胎兒出生后,嬰兒可以以當事人的身份出現在訴訟中,因其民事行為能力的限制應由其親權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起訴或應訴。j沈德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209頁。此種通說對司法實務有指導意義,但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同樣面臨權利行使的諸多障礙。
例一:當胎兒的法定代理人即為其利益的侵害人或者侵害人之一,顯然適用監護人制度將使胎兒利益的保護遭遇瓶頸。
例二:胎兒出生后不久,因受胎期間的侵害行為致死的,由誰來提起損害賠償請求。
3.行使對象不明。胎兒在母體期間遭受第三人損害,胎兒活著出生后,有權就其損害主張法律救濟。那么,此時的“第三人”是否包含胎兒父親,胎兒母親又能否成為侵權主體。比如,妻子懷孕期間遭受丈夫家暴虐待致胎兒受傷害;母親因選擇終止妊娠未果造成胎兒損害;父母親因受胎將遺傳性疾病傳染給子女等均涉及父母侵害胎兒問題,法律對此未設特別規定。在家族觀念和親權文化濃厚的中國,倘若對父母侵害胎兒利益的情形不能準確定性,可能造成夫妻關系失和、親子關系緊張的不和諧狀態,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故該法律真空亟待法之續造來加以填補。
4.賠償范圍不明。對胎兒利益救濟的終極目標在于填補胎兒因遭受損害造成的損失。鑒于胎兒人格權上的特殊性,其享受主張損害賠償的范圍也與自然人有所區別。如何界定胎兒損害賠償范圍,尚無明確的法律依據,且學界和實務界也沒有同一共識。損害賠償一般分為財產性損失賠償和非財產性損失賠償。財產性損失包含直接性財產損失和間接性財產損失;非財產性損失通常指精神損害賠償。k王愛平:《胎兒權益損害賠償研究》,蘭州大學2016年碩士論文,第21-23頁。胎兒基于人身權或純獲利權受到損害請求的直接性財產賠償,可以在個案中精確的計算出來,審判實務中通常能得到支持。間接性財產損失通常指胎兒出生前,因其撫養人遭受他人侵害喪失撫養能力,產生的撫養費損失,通常也予以支持。但對胎兒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理論界爭議較大,實務中也判法不一。
三、路徑選擇:完善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保護之建議
為回應亟待解決的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保護問題,切實加強對胎兒權益的保障,筆者建議從價值、空間、規則三重維度完善保護路徑(如圖四)。

圖四: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保護路徑圖
(一)明確價值維度
對人格權利益的保護延伸到胎兒,符合生命平等原則的基本倫理價值理念,應當得到現代社會最廣泛的認可。從立法和司法上明確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保護的精神是引導社會倫理價值走向文明的有效途徑。
1.立法上。沒有將“侵權損害賠償”明確引入“胎兒權益保護”條款,實屬《民法總則》第16條美中不足。筆者建議,在《民法典侵權編》中增加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條款。可以借鑒日本民法立法經驗l《日本民法典》第721條規定:“胎兒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權,視為其已出生”。,結合前文案例二中審理法院的變通作法,將具體條文擬定為“胎兒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權,視為其已出生。但是胎兒娩出時為死體的,視為對其母體的損害。”m呂倩西:《胎兒權益損害法律問題研究》,西南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1頁。引“權”入法才是理想的法律標準,才是倫理價值的法律體現。
2.司法上。司法實踐是對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保護最直觀的體現,在存在制度漏洞的現實下,如何引導法官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積極探索法之續造,又能避免類案不同判的司法窘境是一直以來的重要課題。針對司法實務,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積極出臺相關司法解釋、發布典型案例來統一裁判方法,指導審判實務。建議最高院在出臺《關于適用〈民法總則〉的解釋》時,明確將“侵權損害賠償”列舉到胎兒具體保護事項中,避免法官在適用《民法總則》第16條時產生分歧。對司法實務中涉及胎兒利益的經典、疑難案例,最高院應當及時發布,為法官斷案提供參考。
第二,提升法官的司法素養。法律續造是法官的一種權力,更是一種能力。當前司法環境對法官如何發掘隱含在條文和秩序之下的裁判空間,全新的演繹法規范和法價值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法官要公正地堅守中立,衡平訴訟雙方利益,運用合理的邏輯思維,推論出妥當的心證結論,完成法律的補充續造,作出可被接受的個案裁判。法官能力素質的提升是一項長久而系統的工程,是司法不斷進步的核心要素。
(二)拓寬空間維度
如前文列舉的實務案例,實踐中對胎兒利益的保護空間過于狹窄,不利于胎兒利益的切實保護。筆者認為,對于胎兒利益保障的空間范圍,既要做到最佳利益保護,又要與自然人有所區別。建議主要從人身利益、財產利益、派生利益三個層次上拓展胎兒利益保護之維度。(如圖五)

圖五:胎兒利益保護范圍空間維度圖
1.人身利益。對尚未出生的胎兒來說,“生命的存續與保存”是其首要爭取的狀態,故與之相關的身體、健康、生命等人身利益處于胎兒利益的核心地位,法律理應為它們提供強大的護翼,重點加以關注。
2.派生利益。派生利益是基于親權、親屬撫養請求權利益和非婚生胎兒對生父的認領請求權利益。如前文列舉的司法案例,胎兒撫養費請求權糾紛出現頻率較多,多數得到支持。此種利益是人身利益的延伸,也應得到法律的保護。
3.財產利益。如前文論述,學者對胎兒財產利益的保護相對較為消極,這是有原因的。現實社會中,財產不單意味著利益,也如影隨形的伴隨著風險;財產享有者不僅享受一種利益,更是承擔一種責任和義務。n朱曉峰:《民法典編纂視野下胎兒利益的民法規范:兼評“民法典建議稿”胎兒利益保護條款》,載《法學評論》2016年第1期。胎兒的“準人格”性源于其只能享受義務,無法承擔責任。因此,筆者贊同原則上對胎兒的財產利益不予保護,但應當承認例外情形。比如在繼承、接受贈與、依契約受益等純獲利情形下,應當保護胎兒的財產利益。
當胎兒的利益保護空間遭到沖擊,法律保護的胎兒利益被不法侵害,胎兒便可以行使請求權,就其遭受的損害向侵權人請求賠償。
(三)構建規則維度
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如何具體行使,筆者認為,可以從行使時間、行使主體、行使對象、賠償范圍四個方面,構建具體行使規則。
1.行使時間。在前文案例五中,一審時胎兒并未出生,法官出于多角度考量,對胎兒的損害主張予以了支持。在立案登記制的當下,胎兒還未出生就已經進入到訴訟程序的類似情況可能會經常發生,法官則無法拒絕裁判。筆者認為,為充分保障胎兒利益,減少當事人訟累,可以允許在胎兒未出生前即可行使請求權。但為了保證糾紛的有效解決,法官可以在審理方法和裁判內容上作技術處理。比如,胎兒月份還過小的,可以先中止審理,待胎兒出生再作裁判;胎兒月份已經較大,可以先行裁判,但為避免因胎兒未能活著出生,產生不當得利返還,可以在判項中附條件執行,具體可為“胎兒損害部分以出生證明支付”。
2.行使主體。如前文論述,胎兒自身存在特殊性,且侵害胎兒的行為具有復雜性。筆者建議,針對胎兒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時間的不同可以對權利行使主體作如下規范(如圖六):

圖六: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行使主體擬制情形
3.行使對象。如筆者前文論述,關于胎兒之父、母能否成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行使對象問題,倘若處理不好,可能會對我國“家”文化帶來沖擊。在與內地有相同文化傳承的臺灣地區,該地區現行“民法”對此亦未明確,但學界多數持肯定態度,以王澤鑒教授為代表認為,關于父母對胎兒的侵害行為,原則上應適用一般規則,應負侵權責任。o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四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2頁。與臺灣地區不同的是,內地將計劃生育列為一項長期人口政策,提倡并鼓勵父母“少生優生”。在此情況下,肯定說似乎在內地水土不服。基于內地社會實情,筆者認為,原則上父母不能成為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行使對象,但也允許除外情形,比如德國著名的“生父傳染梅毒于子案”中生父惡意將梅毒傳染給胎兒的行為,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法律上都應受到譴責。為防止權利濫用成為傷害“家”文化的利器,對除外情形應適用限縮式列舉。
4.賠償范圍。前文案例一中,審理法院對胎兒的精神損害賠償未支持,這代表了當前審判實務中主流觀點。多數人認為,胎兒相比實際自然人是有差異的,特別是心智方面未成熟,對精神的感知不強,故不應支持精神撫慰金。筆者恰恰持相反的態度,認為縱然胎兒出生后,精神的感知很微弱,但嬰兒的心智是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在其剛有感知時,便能感受到侵害行為對其心靈的創傷,且隨年歲的增長一直存在。相比一般人后來遭受的精神侵害,這種創傷實際是自始存在,與日俱增。按照“舉輕以明重”原則,筆者認為胎兒的精神損害賠償理應得到支持。
結 語
法學家卡爾·拉倫茨說:“法官的法續造,有時不僅在填補法律漏洞,更在于采納乃至發展一些新的法律思想。”p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局2003年9月第1版,第246頁。在完善胎兒權益保護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新思想”;在中國法治發展的進程中,我們更需要“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