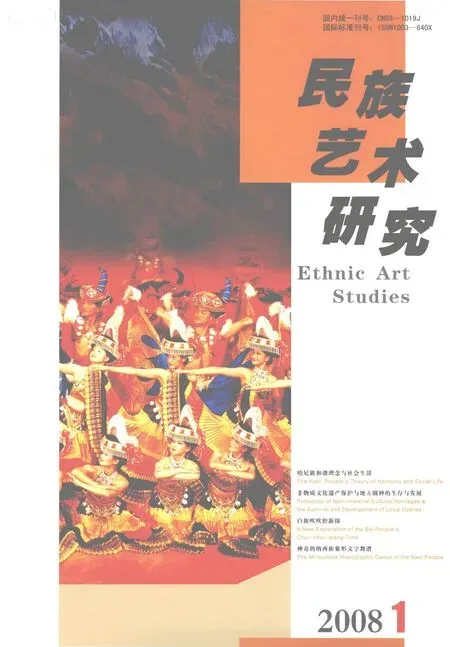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民族舞蹈學(xué)”學(xué)科建構(gòu)的若干思考
——從“非遺名錄”舞蹈“進校園”談起
于 平
一、“非遺法”與“國家級非遺名錄”中的“傳統(tǒng)舞蹈”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也即“非遺法”。該法在第一章《總則》中指出:“本法所稱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組成部分的文化表現(xiàn)形式,以及與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相關(guān)的實物和場所。”還指出:“保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應(yīng)當(dāng)注重其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認(rèn)同,有利于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jié),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在定義“非遺”后,這里的“三性”指的是保護“非遺”的原則,而“三個有利于”則是強調(diào)“非遺”保護的功效。
在“非遺法”的第三章,闡明了《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名錄》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務(wù)院建立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名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家級非遺名錄”。作為“非遺名錄”的最高層級,這個名錄的產(chǎn)生是由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從本級“非遺名錄”中擇優(yōu)、擇重推薦而成。也就是說“國家級非遺名錄”是自下而上、逐層推薦的結(jié)果。這項“推薦”工作,一要介紹項目的名稱、歷史、現(xiàn)狀和價值;二要介紹項目的傳承范圍、譜系、傳承人的技藝水平、傳承活動的社會影響;三要提出保護應(yīng)達(dá)到的目標(biāo)和應(yīng)采取的措施。
其實,“國家級非遺名錄”的推薦與核準(zhǔn),早在“非遺法”通過之前的2006年就公布了首批“非遺名錄”。這一批“非遺名錄”于該年5月20日公布,共518項;此后第二批510項于2008年6月14日公布,第三批191項于2011年6月10日公布,第四批153項于2014年7月16日公布。按照第二批之后三年一核準(zhǔn)的規(guī)律,今年早些時候就應(yīng)該公布第五批了;但現(xiàn)在第五批“非遺名錄”正在公示之中,這次是將“代表性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結(jié)合在一起公示的。這說明公布“非遺名錄”的目的不僅在于“保護”而且在于“傳承”,“傳承”才是最有效的“保護”。其中“非遺名錄”項目“進校園”就是這樣一項重要的工作。
上述四批共1372項“國家級非遺名錄”中,傳統(tǒng)舞蹈類共有131項,約占10%左右;在四個批次里分別是41項、55項、15項和20項。如果按地區(qū)分布來統(tǒng)計,排前三位的分別是云南省(24項)、西藏自治區(qū)(18項)和四川省(12項);接下來是廣東省(9項),然后是并列的湖南省、貴州省、青海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均為7項);均為6項的還有河北省、浙江省和甘肅省,另有山西省、陜西省和河南省均為5項。如果按民族屬性來統(tǒng)計,最多的是藏族——除西藏地區(qū)本身的18項外,云南迪慶、青海玉樹也共有“鍋莊舞”;四川芒康則共有“弦子舞”,另有“跳曹蓋”;青海省還有“藏族螭鼓舞”。云南省在“國家級非遺名錄”中的“傳統(tǒng)舞蹈”項目最多,且占這一類別的六分之一,這其中基本上是少數(shù)民族舞蹈——其中彝族有9項(銅鼓舞、葫蘆笙舞、煙盒舞、打歌、跳菜、老虎笙、左腳舞、樂作舞、三弦舞)之多,其余有傣族2項(孔雀舞、象腳鼓舞),哈尼族2項(棕扇舞、铓鼓舞)以及佤族木鼓舞、傈僳族阿尺木刮、基諾族大鼓舞、納西族熱美蹉、布朗族蜂桶鼓舞、普米族搓蹉、拉祜族蘆笙舞、怒族達(dá)比亞舞等。這其實意味著,“傳統(tǒng)舞蹈”作為“非遺名錄”的豐富性與多民族文化共存的豐富性是密切相關(guān)的。順便說一句,第五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公示的舞蹈方面的“代表性傳承人”共有124人。其中各種“龍舞”有14人,各種“獅舞”有7人,各種“燈舞”有6人,各種“鼓舞”有5人;另有“花鼓燈”5人,“秧歌”4人,“高蹺”4人,“竹馬”3人,儺舞“3”人;少數(shù)民族舞蹈的傳承人以藏族為最多,有18人;其余土家族有6人,維吾爾族有5人,蒙古族有5人,彝族有5人,瑤族有5人……
二、“原生態(tài)舞蹈”與“文化人類學(xué)”的視角
正是由于“非遺法”的立法和“國家級非遺名錄”的公布,通過課堂傳授、校園傳承成為“非遺”保護的一項重要工作乃至一條重要路徑。“非遺名錄”中的“傳統(tǒng)舞蹈”,在相關(guān)院校的專業(yè)教學(xué)中被稱為“原生態(tài)舞蹈”;而所謂“原生態(tài)”,指的是由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自發(fā)參與、自主傳承、自然變遷。既往的專業(yè)舞蹈工作者也深入民間直面“原生態(tài)”,直面這樣一種稚拙而樸素、率性而真誠、鮮活而生動的文化資源——或稍加整理呈現(xiàn)于舞臺,或借用“圖式”風(fēng)化于創(chuàng)作,或提取“舞動”適用于教學(xué)……在我們既往的民族民間舞蹈教學(xué)中,也把進入課堂的教材稱為“代表性”舞蹈——這既是從眾多“原生態(tài)舞蹈素材”中選擇出來的“代表性”舞蹈,也是未來用于“舞臺化創(chuàng)作”典型呈現(xiàn)的“代表性”舞蹈素材。
然而,對于當(dāng)下的“非遺名錄”舞蹈“進校園”,由于強調(diào)“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實質(zhì)上在于強調(diào)用“文化人類學(xué)”的眼光來審視。我們知道,人類把自身作為一門學(xué)科的研究對象來加以審視,迄今不過500年歷史。威廉·A·哈維蘭寫道:“1534年,雅克·卡蒂埃為法國實地考察圣勞倫斯河,使得他接觸了一些原住民群體成員。這種接觸引發(fā)了他對其他民族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導(dǎo)致了人類學(xué)的發(fā)展。”后來得到充分發(fā)展并得以不斷完善的“人類學(xué)”,使命在于“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時代的人,試圖形成關(guān)于人及其行為的可靠知識——既涉及使他們相區(qū)別的東西,也涉及他們共享的東西。”*[美]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xué)》,北京: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我們知道,“人類學(xué)”是“文化人類學(xué)”的上位學(xué)科。但一般認(rèn)為:“人類學(xué)被劃分為四個領(lǐng)域:體質(zhì)人類學(xué)和三個文化人類學(xué)分支學(xué)科——考古學(xué)、語言人類學(xué)和民族學(xué)。體質(zhì)人類學(xué)(Physical Anthropology)主要研究作為生物有機體的人;而文化人類學(xué)(Cultural Anthropology)研究作為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人類。”*[美]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xué)》,北京: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事實上,“文化人類學(xué)”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向“種族中心主義”挑戰(zhàn),因而大可不必過于將其與“研究生物有機體的人”的“體質(zhì)人類學(xué)”并置一處,盡管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人的“生物特性”與其“文化”會交互影響。“文化人類學(xué)”范疇中的“文化”,被設(shè)想為“通常無意識的準(zhǔn)則”,是作為初級社會形態(tài)的“族群”運行的“準(zhǔn)則”。所謂“挑戰(zhàn)種族中心主義”,是指“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在各個不同的地方之間可能有相當(dāng)大的差別,但卻沒有任何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文化’。”*[美]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xué)》,北京: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就“文化人類學(xué)”的三個分支學(xué)科而言,“考古學(xué)”主要通過物質(zhì)遺存研究過去的文化;“民族學(xué)”則專門研究現(xiàn)在的文化,因而又被稱為“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在我看來,這個“現(xiàn)在的文化”是指“歷史傳承到現(xiàn)在的文化”,是至今仍存的活態(tài)的歷史,其中有許多就是我們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一個時期以來,不少舞蹈學(xué)者積極參與“文化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建設(shè),高揚起“舞蹈人類學(xué)”的旗幟;準(zhǔn)確地說,這個“舞蹈人類學(xué)”就其關(guān)注的對象而言,其實指的是舞蹈的“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也就是舞蹈的“民族學(xué)”。舞蹈的“民族學(xué)”作為學(xué)科建設(shè)可借鑒“音樂”相關(guān)學(xué)科建設(shè)的辦法,仿效“民族音樂學(xué)”而建構(gòu)“民族舞蹈學(xué)”。這其中的共同點在于,無論是“民族音樂學(xué)”還是“民族舞蹈學(xué)”的學(xué)者,都是相關(guān)學(xué)科的民族志學(xué)者,都是以“田野工作”作為最基本的工作。
三、薩克斯《世界舞蹈史》開“民族舞蹈學(xué)”之先河
“民族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建構(gòu)可以參照“民族音樂學(xué)”。伍國棟指出:“‘民族音樂學(xué)’(ethnomusicology)這一學(xué)科名稱是一個復(fù)合詞語,它由‘民族學(xué)’(ethnology)和‘音樂學(xué)’(musicology)兩個詞匯復(fù)合而成。雖然這一復(fù)合詞匯在中國音樂學(xué)界已通常被譯作‘民族音樂學(xué)’,但亦有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將它譯為‘音樂民族學(xué)’更為妥當(dāng)……但無論如何,這種從‘民族音樂學(xué)’到‘音樂民族學(xué)’的詞序組合變化選擇,其主旨都是想要突出本學(xué)科‘民族學(xué)’與‘音樂學(xué)’相結(jié)合關(guān)系中的‘民族學(xué)’內(nèi)容,同時從字面上又可與當(dāng)今已普遍采用的‘音樂史學(xué)’‘音樂美學(xué)’‘音樂社會學(xué)’‘音樂形態(tài)學(xué)’等音樂學(xué)分支學(xué)科稱謂相并列、相對等而處于同一學(xué)科層次……由于‘民族音樂學(xué)’突出了‘民族學(xué)’內(nèi)容,而‘民族學(xué)’在社會科學(xué)中又是文化人類學(xué)的一個子學(xué)科或本身也可被視為是‘人類學(xué)’,因而與近親的文化學(xué)、民俗學(xué)等學(xué)科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在某些國外的音樂學(xué)著述中,此學(xué)科和與此學(xué)科研究領(lǐng)域相同的課題,同時還有‘音樂人類學(xué)’‘音樂文化學(xué)’‘音樂民俗學(xué)’等稱呼不同而學(xué)科性質(zhì)基本相同的表述。”*伍國棟:《民族音樂學(xué)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通過研究,《民族音樂學(xué)概論》對學(xué)科做出了以下定義:“民族音樂學(xué),是音樂學(xué)下屬的一門研究世界諸民族傳統(tǒng)音樂及其發(fā)展類型的理論學(xué)科,田野考察是其獲得研究材料來源的基本方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將所考察和研究的音樂對象,視為是一種音樂事象,倡導(dǎo)將某一民族現(xiàn)存的傳統(tǒng)音樂及其發(fā)展類型,置入該民族特定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環(huán)境之中,通過對該民族成員(個體或群體)如何根據(jù)自身文化傳統(tǒng),去建構(gòu)、使用、傳播和發(fā)展這些音樂類型的考察和研究,闡述其有關(guān)音樂類型的基本形態(tài)特征、生存變異規(guī)律和民族文化特質(zhì)。”*伍國棟:《民族音樂學(xué)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頁。可以看到,這個定義基本上是用“民族學(xué)”(也即“文化人類學(xué)”下位的“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的方法來進行“音樂學(xué)”的考察和研究。作為“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門類下同一級學(xué)科的“音樂與舞蹈”,如果將上述定義中的“音樂”換成“舞蹈”,基本上可定義“民族舞蹈學(xué)”。
伍國棟在回顧“民族音樂學(xué)”的簡史之時,指出其前身的學(xué)科被稱為“比較音樂學(xué)”。這個萌芽于18世紀(jì)中葉的“比較音樂學(xué)”,主要是“運用比較思維的方法,并以某種音樂傳統(tǒng)的音樂作為參照系去看待和觀察另一種音樂傳統(tǒng)的音樂的。”*伍國棟:《民族音樂學(xué)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20世紀(jì)初在德國出現(xiàn)的、后來被稱為“柏林學(xué)派”的比較音樂學(xué)家,有一位庫爾特·薩克斯(Curt Sachs 1881—1959)其實也可視為我們“民族舞蹈學(xué)”的先驅(qū)者。由他所著《世界舞蹈史》在《序言》中所說:“‘藝術(shù)’一詞不能闡明舞蹈的全部概念……舞蹈打破了肉體和精神的界限,打破了耽溺于情欲和約束舉止的界限,打破了社會生活和發(fā)泄個人特性的界限,打破了游戲、宗教、戰(zhàn)爭和戲劇的區(qū)別,打破了一切由更為高級文化形成的各種界限……人類需要舞蹈,因為對生活的熱愛也迫使四肢不再懶散;人們渴望跳舞,因為跳舞的人能獲得魔力,為自己帶來勝利、健康和生活樂趣;當(dāng)同一部落的人攙著手一起跳舞時,便有一條神秘的系帶把整個部落與個人聯(lián)結(jié)起來,使之盡情歡跳——沒有任何一種‘藝術(shù)’能包含如此豐富的內(nèi)容……”*[德]庫爾特·薩克斯:《世界舞蹈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很顯然,這種不能被“藝術(shù)”一詞闡明的“舞蹈”,只能用“民族學(xué)”——“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來闡明。
庫爾特·薩克斯繼續(xù)指明:“從我們未開化的祖先傳下來的舞蹈,是一種有層次表現(xiàn)精神極為興奮時的活動情況,后來擴展到祈求神明,擴展到自覺地力求成為控制人類命運的超人力量的一部分。舞蹈變成了供奉犧牲品的祭儀,變成了表現(xiàn)念符咒、做祈禱以及先知預(yù)言的活動;舞蹈成為能召喚和驅(qū)散自然界的力量,醫(yī)治疾病,能使死者和他們的子孫取得聯(lián)系;能保證提供營養(yǎng)物,在追逐中交好運,在戰(zhàn)斗中獲勝利;可以賜福于田地和部落,是創(chuàng)造者、保管者、侍者和保護人……在原始社會的人類生活與古代文明社會生活中,幾乎沒有任何比舞蹈更具重要性的事物……舞蹈不是一種僅為人們所能容忍的消遣,而是全部落的一種很嚴(yán)肅的活動;在原始社會人類生活里,沒有任何場合離得開舞蹈:生育、割包皮、少女獻(xiàn)身祭神、婚喪、播種、收割、慶祝酋長就職、狩獵、戰(zhàn)爭、宴會、月亮盈與蝕、病患——在所有這些場合,都需要舞蹈……舞蹈是拔高了的簡樸生活——這種說法道出了舞蹈固有的全部特征和最完整的含義。但是它還可擴大到從科學(xué)這個領(lǐng)域來思考,只是不能根據(jù)這種思考給它‘下定義’罷了。這種定義是不容易確定的;事實上分析到最后,也許會得到‘下定義’是不可能的結(jié)論。人類所有的活動都應(yīng)該拋開刻板的倉促的分類法——工作和娛樂、法律和自由可融為一體,而這種覺察不到的融合可能就是舞蹈的主要特點。因此從確定的意義來講,給舞蹈下的定義不可能比‘有節(jié)奏的活動’更嚴(yán)謹(jǐn)……”*[德]庫爾特·薩克斯:《世界舞蹈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頁。很顯然,庫爾特·薩克斯從“‘藝術(shù)’一詞不能闡明舞蹈的全部概念”出發(fā),最后得出“給舞蹈下的定義不可能比‘有節(jié)奏的活動’更嚴(yán)謹(jǐn)”的認(rèn)識,其實也就是今日“民族舞蹈學(xué)”對其更為廣袤的視野而形成的更為深邃的認(rèn)知。
四、民間舞蹈的“動態(tài)切入法”與“文化類型劃分”
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tǒng)的以“民族舞蹈學(xué)”目光從事研究工作的專著應(yīng)該是羅雄巖的《中國民間舞蹈文化》。該書前言中寫道:“半個世紀(jì)以來,在民間文化與各民族淳樸民風(fēng)的陶冶下,筆者由一個民間舞蹈的學(xué)習(xí)者,轉(zhuǎn)變?yōu)槊耖g文化的研究者;同時深深感到,我們這代人既然有幸學(xué)習(xí)了各民族的民間舞蹈,就該系統(tǒng)地研究它們所體現(xiàn)的中國文化精神與民族審美情趣,建立與之相應(yīng)的‘中國民間舞蹈文化’新學(xué)科……1986年,筆者在北京舞蹈學(xué)院開始講授《中國民間舞蹈文化》課程;此后,在教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上,逐漸形成學(xué)科的理論結(jié)構(gòu)與研究方法……以舞蹈文化的特殊性、民間舞蹈文化特征、中國原始舞蹈遺存、中國民間舞蹈的文化類型、‘動態(tài)切入法’為基礎(chǔ)理論;以可操作的‘動態(tài)切入法’作為核心理論,研究中國民間舞蹈的形式特征與文化傳承規(guī)律……”*羅雄巖:《中國民間舞蹈文化》,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羅雄巖《中國民間舞蹈文化》的第三章便是《“動態(tài)切入法”的理論與操作》。如羅雄巖所說:“動態(tài)形象是舞蹈文化理論研究的根本,是‘動態(tài)切入法’的核心理論……動態(tài)形象是‘音’‘象’‘動態(tài)’互動的文化符號。舞者是在一定時間與空間通過動態(tài)形象展示文化信息的;舞者的動態(tài)形象中,對于民族的原始文化符號與今日的文化信息都會有所體現(xiàn),它們是有待研究者辨析的充滿生命力的形象。因此,‘動態(tài)切入法’的核心理論,是詮釋動態(tài)符號所展示的深邃的文化內(nèi)涵,辨析原始舞蹈文化遺存、時代文化信息,運用新的藝術(shù)實踐與理論的升華……”*羅雄巖:《中國民間舞蹈文化》,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頁。為便于操作,羅雄巖提出了“動態(tài)切入法”的32字口訣,即“特定層次、多種因素、縱橫探索、深入研究、貴在升華”和“動態(tài)切入、意境描繪、個性升華”。在他看來:“前20字是從五個方面探索舞蹈文化的步驟;后12字是操作的核心,又是完成研究目的三個遞升的層次。”*羅雄巖:《中國民間舞蹈文化》,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頁。從該書所列“操作示意圖”來看,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民族學(xué)“田野調(diào)查”(或?qū)嵉卣{(diào)查)方法的平移和改造,也可以說羅雄巖的《中國民間舞蹈文化》就學(xué)科而言就是中國的“民族舞蹈學(xué)”。
羅雄巖《中國民間舞蹈文化》第六章為《中國民間舞蹈的文化類型》,其中有“中國民間舞蹈文化類型劃分方法比較”一節(jié),分別介紹了李雪梅的“地域生態(tài)劃分法”和筆者的“語言族系屬劃分法”。其中李雪梅的觀點首見于其論文《論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新文化區(qū)》,她將中國民間舞蹈分為“六大文化區(qū)”:一、秧歌舞蹈文化區(qū)——北方漢族,以北方旱作文化為代表,屬于黃河流域文化中心的農(nóng)耕文化;二、花鼓舞蹈文化區(qū)——南方漢族,以南方稻作文化為代表,屬于長江流域文化中心的農(nóng)耕文化;三、藏族舞蹈文化區(qū)——青藏高原地區(qū)以藏族為主體,典型的少數(shù)民族民間舞蹈,以農(nóng)牧文化為代表,屬于游牧和農(nóng)耕混合型文化;四、蒙古族舞蹈文化區(qū)——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以蒙古族為主體,以溫帶草原游牧文化為代表,屬游牧和定居輪牧型文化;五、西域樂舞舞蹈文化區(qū)——西北地域以維吾爾族為主體,以典型的綠洲文化和游牧文化為代表,屬于灌溉農(nóng)業(yè)和游牧混合型文化;六、銅鼓舞蹈文化區(qū)——西南地區(qū)多民族,以農(nóng)耕文化為代表,并根據(jù)具體情況可劃出亞文化區(qū)或文化圈,如朝鮮族舞蹈文化圈。在上述“文化類型劃分”的基點上,李雪梅撰寫了《地域民間舞蹈文化的演變》的專著,其中特別強調(diào)“環(huán)境與舞蹈文化的關(guān)系”——不僅闡明了環(huán)境的自然要素對民間舞蹈形成的影響,也闡明了環(huán)境制約的勞作方式對民間舞蹈的影響;在此基礎(chǔ)上,李雪梅詳細(xì)論述了《舞蹈文化區(qū)中的舞蹈類型》(第四章)、《民族民間舞蹈的區(qū)域變化與發(fā)展》(第五章)、《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的空間傳播》(第六章)和《民間舞蹈文化現(xiàn)象的環(huán)境反映》(第八章)。可以說,這是一部十分有水準(zhǔn)的“民族舞蹈學(xué)”的專著。
羅雄巖在書中所提及的“語言族系屬劃分法”,所列材料來源是筆者的《風(fēng)姿流韻:舞蹈文化與審美》。其實,這一觀點首先發(fā)表于《四夷樂與邊疆民族舞蹈的生態(tài)格局》一文。后來在與彭松先生共同主編的《中國古代舞蹈史綱》中,列入第十一章《四夷樂與邊疆民族舞蹈》。邊疆民族樂舞,在古時稱“四夷樂”(周代也稱“四裔樂”)。這是古人從以“中原”為“中”的空間方位上來區(qū)分邊疆民族樂舞,今天對其加以討論與“種族中心主義”無涉。該文認(rèn)為,在中國文化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原文化與四夷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始終在進行的,盡管方位的側(cè)重會有變化,交流的主客也會易位。對邊疆民族舞蹈生態(tài)格局的考察,是該文最早提出以語言格局為參照,并以歷史文獻(xiàn)作為數(shù)據(jù)進行了描述。除漢民族舞蹈外,該文認(rèn)為中國民俗舞蹈可以分為三大生態(tài)格局:這就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生態(tài)格局、漢藏語系·苗瑤和壯侗語族生態(tài)格局、阿爾泰語系生態(tài)格局。在后來出版的《風(fēng)姿流韻:舞蹈文化與審美》一書中,修訂為“中國民俗舞蹈‘四大色塊’的人文格局”,增加了“漢族色塊”,并將“漢藏語系·苗瑤和壯侗語族生態(tài)格局”調(diào)整為“澳泰色塊”(因為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兩個“語族”可能應(yīng)屬于“澳泰語系”而非“藏緬語系”)。這種“舞蹈文化類型劃分”的理念也是“民族舞蹈學(xué)”的重要學(xué)科構(gòu)成,只不過那時還缺乏學(xué)科建構(gòu)的自覺。
五、逐步建立起對民族舞蹈文化特異性的體系化分析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民族舞蹈學(xué)”就其研究對象而言,與“民族民間舞蹈”關(guān)系最為緊密;換言之,本源意義上的“民族民間舞蹈研究”就是“民族舞蹈學(xué)”的研究,就要采用遵循“田野工作”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巫允明所著《中國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和在此基礎(chǔ)上撰就的《中國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教程》,其實就是比較典型的中國“民族舞蹈學(xué)”研究成果。在后一部著作中,作者附錄了一篇《論“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的研究方法與途徑》,其中寫道:“對于‘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的研究方法和途徑,我在1994年曾提出和發(fā)表過:借助于語言學(xué)所使用的‘民族語言系屬’理論,對同語言系統(tǒng)民族的族源、民族習(xí)俗與原生態(tài)舞蹈間的關(guān)系進行舞蹈文化研究的可行性論述。以后的十余年中,在此基礎(chǔ)上我進一步吸納了文化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試圖將二者的研究方法與結(jié)論引入對‘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的研究。經(jīng)前后近20年的實踐,證明這種研究方法是可行的……”*巫允明:《中國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頁。具體而言,巫允明強調(diào)“‘研究’必須立足于‘考察’。”*巫允明:《中國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頁。她說:“考察,即文化人類學(xué)中最為強調(diào)的‘田野考察’……希望通過‘田野考察’獲取對既定研究目標(biāo)所需的翔實材料,首先需要進行全面、細(xì)致和大量的案頭工作……考察過程中,除將調(diào)查事實與案頭材料進行核實、比對外,要對不同年齡層的長者進行有準(zhǔn)備的訪談,從他們的回顧中取得對過往歷史的見證資料……一個調(diào)查者的記憶再好,到后期整理調(diào)查資料時的回憶難以毫無遺漏,因此考察者每日書寫工作日志就顯得尤為重要……舞蹈屬于一瞬即逝的動態(tài)藝術(shù),對于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的考察,以錄音、錄像和攝影進行記錄,缺一不可……”*巫允明:《中國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頁。以上所謂“吸納了文化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其實就是以“民族學(xué)方法”所進行的“民族舞蹈學(xué)”研究。
如果說,“民族舞蹈學(xué)”主要是用“民族學(xué)”方法來研究“舞蹈”,特別是如庫爾特·薩克斯所言“‘藝術(shù)’一詞不能闡明舞蹈的全部概念”的“舞蹈”;那么在舞蹈學(xué)科中最接近“民族舞蹈學(xué)”的當(dāng)屬“舞蹈生態(tài)學(xué)”。資華筠、王寧著《舞蹈生態(tài)學(xué)》“前言”中寫道:“‘舞蹈生態(tài)學(xué)’1988年由中國藝術(shù)研究所立項,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了《舞蹈生態(tài)學(xué)導(dǎo)論》,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礎(chǔ)理論體系……20多年來,這門學(xué)科所建立的基礎(chǔ)理論,全面應(yīng)用于舞蹈研究、教學(xué)、評論、實地考察等,經(jīng)受了實踐的驗證,也在實踐中有所豐富、提高。2000年聯(lián)合國提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民族民間舞蹈成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門類,這些舞蹈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成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核心問題。‘舞蹈生態(tài)學(xué)’涉及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中自然舞蹈的評價、擇定、保護方法科學(xué)化諸多問題,更加顯示了它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資華筠:《舞蹈生態(tài)學(xué)》,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
在《舞蹈生態(tài)學(xué)》的“總論”中,資華筠、王寧討論了該學(xué)科的學(xué)科定位、研究目標(biāo)與特點以及研究方法。其中指出:“舞蹈生態(tài)學(xué)是對舞蹈藝術(shù)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進行宏觀與系統(tǒng)考察的科學(xué)。它以舞蹈為核心,以舞蹈與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之間相互關(guān)系、相互作用為研究對象,目的是探索不同舞蹈的產(chǎn)生、存在、發(fā)展的規(guī)律,研究其特點的形成,討論它如何受到環(huán)境的影響,又如何反轉(zhuǎn)過來影響了環(huán)境。”*資華筠:《舞蹈生態(tài)學(xué)》,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這個關(guān)于“學(xué)科定位”的表述與“民族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內(nèi)涵在本質(zhì)上是相似的。如其所言:“舞蹈生態(tài)學(xué)……突破有些舞蹈研究僅就舞蹈現(xiàn)象的局部分析就事論事的局限性,從‘舞蹈與人類’這個大主題中,用多元綜合的方法分析舞蹈的自然形態(tài),揭示舞蹈的內(nèi)在本質(zhì)。從‘藝術(shù)與人類’的關(guān)系這個角度來探討藝術(shù)的本質(zhì)與規(guī)律,是近年來各門藝術(shù)研究的共同路線,也是藝術(shù)研究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不過,因為舞蹈的存在方式、表現(xiàn)方式有著如前所述以‘人’為媒質(zhì)的特性,研究‘舞蹈與人類’的關(guān)系更為直接,有更特殊的意義,也更為迫切。無論是生物人、社會人——個體或群體,均離不開與其所處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獲取到宏觀地研究舞蹈本質(zhì)的一把鑰匙,以舞蹈與環(huán)境關(guān)系為出發(fā)點,開啟舞蹈生態(tài)學(xué)的原理。”*資華筠:《舞蹈生態(tài)學(xué)》,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頁。
在論及該學(xué)科的研究目標(biāo)與特點時,作者在提出“舞蹈生態(tài)學(xué)以舞蹈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為研究目標(biāo)”后,指出“舞蹈生態(tài)學(xué)的研究目標(biāo)決定了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自然舞蹈(Natual Dance)。因為只有這種舞蹈是原始舞蹈的延續(xù),是始終與民族、社會、自然環(huán)境融合在一起的。它是民族文化的要素,也是表演舞蹈(Performance Dance)依據(jù)的素材。研究自然舞蹈,才能抓住作為文化事象和人類創(chuàng)造的舞蹈藝術(shù)的根本……舞蹈生態(tài)學(xué)提出的對自然舞蹈形態(tài)分析(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nce)的可操作性概念,對民族舞蹈風(fēng)格特色的觀察、分析將更加清晰有據(jù)。繼而結(jié)合其表意審美內(nèi)涵,提煉各舞種具有典型意義的‘語匯系統(tǒng)’,歸納‘同形舞目類群’,并在此基礎(chǔ)上確立了層次分明、脈絡(luò)清晰,涵蓋了舞蹈形態(tài)、功能、源流譜系和播布區(qū)等的多維舞種(Multidimensional Choreospecies)概念,這無疑對探尋由于各民族的環(huán)境差異以及在不同步的發(fā)展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各種人文因素制約著舞蹈發(fā)展的表征性現(xiàn)象與深層次緣由的認(rèn)識,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遵循這一路徑層層深入——由表及里、由局部向全面拓展,必然對其民族文化特異性的社會人文緣由及生成發(fā)展規(guī)律有更加科學(xué)的認(rèn)知。此外,借助考古、文獻(xiàn)等來追溯舞種傳衍、播布路線和在此過程中的功能演變,并分析這種變化反轉(zhuǎn)過來對舞蹈的外部形態(tài)又產(chǎn)生何種影響……將有助于梳理舞種進化源流譜系,豐富并深化對其歷時性的研究。正是在‘形、功、源、域’綜合性研究的基礎(chǔ)上,逐步建立起對民族舞蹈文化特異性的體系化分析,并有望實現(xiàn)舞蹈科學(xué)研究‘質(zhì)’的飛躍。需要說明的是,‘民族文化特異性’研究,不只是為了‘別異’,更期望在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中相互汲取、促進,探究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共通性。”*資華筠:《舞蹈生態(tài)學(xué)》,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2年版,第9-11頁。細(xì)讀“舞蹈生態(tài)學(xué)”的學(xué)科定位、研究目標(biāo)與特點,我倒傾向于視其為較多借鑒了“生態(tài)學(xué)”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民族舞蹈學(xué)”。
六、“民族舞蹈學(xué)”研究的中國先賢及其主張
實際上,中國自現(xiàn)代以來,就不乏以“文化人類學(xué)”目光來審視“舞蹈”者,聞一多《說舞》就是其中最為重要者。在《說舞》一文中,聞一多指出:“舞是生命情調(diào)最直接、最實質(zhì)、最強烈、最尖銳、最單純而又最充足的表現(xiàn)。生命的機能是動,而舞便是節(jié)奏的動;或更準(zhǔn)確點,是有節(jié)奏的移易地點的動。所以它只是生命機能的表演。但只有在原始舞里才看得出舞的真面目,因為它是真正全體生命機能的總動員,它是一切藝術(shù)中最具綜合性的藝術(shù)……現(xiàn)在我們更可以明白,所謂表演與非表演,期間也只有程度的差別而已。生命情緒的過度緊張、過度興奮,以至成為一種壓迫,也是一種愉快;所以我們也需要在更強烈、更集中的動中來享受它……一方面在高度的律動中,舞者自身得到一種生命的真實感(一種覺得自己是活著的感覺),那是一種滿足;另一方面,觀者從感染作用也得到同樣的生命的真實感,那也是一種滿足。舞的實用意義便在這里。或由本身的直接經(jīng)驗(舞者),或由感染式的間接經(jīng)驗(觀者),因而得到一種覺得自己是活著的感覺,這雖是一種滿足,但還不算滿足的極致、最高的滿足;是感到自己和大家一同活著,各人以彼此的‘活’互相印證、互相支持,使各人自己的‘活’更加真實、更加穩(wěn)固,這樣滿足才是完整的、絕對的。這群體生活大和諧的意義,便是舞的社會功能的最高意義;由和諧的意識而發(fā)生一種團結(jié)和秩序的作用,便是舞的社會功能的次一等的意義……”*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2頁。在聞一多所處的時代,“表演舞蹈”并不發(fā)達(dá),且矯揉造作;而“文化人類學(xué)”所主張的“文化相對主義”,使他通過《說舞》來申說一種主張,申說“群體生活大和諧”的意義,申說“團結(jié)和秩序”的作用,從而喚醒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20世紀(jì)80年代初,中國舞蹈界有一場關(guān)于“舞蹈美學(xué)”的大討論,起因一是整個社會興起的“美學(xué)熱”,一是針對王元麟《論舞蹈與生活的美學(xué)反映關(guān)系》的批判。因為王元麟認(rèn)為:“要把舞蹈本身的美學(xué)特點弄清,就要先拋開其他的特別是文學(xué)的審美作用因素,從舞蹈的純?nèi)恍问阶饔脕磉M行分析和認(rèn)識……它的純?nèi)恍问匠3>褪俏覀兾璧附绶Q為‘風(fēng)格素材’的舞蹈動作本身的舞蹈表現(xiàn)……我們對舞蹈審美的自身認(rèn)識,不能不首先從舞蹈動作開始。通常有一種看法,以為舞蹈動作只是舞蹈的形式,其實動作本身正是它美學(xué)的內(nèi)容之所在。”*王元麟:《論舞蹈與生活的美學(xué)反映關(guān)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編:《美學(xu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頁。正是這句“動作本身正是它美學(xué)的內(nèi)容之所在”挑戰(zhàn)了舞蹈界的“常識”,因而遭到“群起而攻之”。實際上,批判者在用“表演舞蹈”美學(xué)觀照來批判王元麟“非表演舞蹈”(也即資華筠所謂“自然舞蹈”)的美學(xué)特質(zhì)。因為在王元麟看來:“我們講舞蹈的美學(xué)內(nèi)容,就是指某一特定社會生活內(nèi)容在某一舞蹈動作上的特定風(fēng)格的反映……事實上,任何民族的任何具有風(fēng)格特點的舞蹈動作,當(dāng)初都和該民族地區(qū)特定生活動作相關(guān)聯(lián),只不過今天不一定能找到其生活動作的藍(lán)本。作為特定概念的‘舞蹈動作’,無論今天有無現(xiàn)實藍(lán)本,它總是要以一定社會群眾的審美傳統(tǒng)和習(xí)慣為存在基礎(chǔ),它本身就是個特定的美學(xué)概念。”*王元麟:《論舞蹈與生活的美學(xué)反映關(guān)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編:《美學(xu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頁。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王元麟所說的“舞蹈的美學(xué)內(nèi)容”,本質(zhì)上就是“民族舞蹈學(xué)”的“美學(xué)”。
王元麟認(rèn)為:“事實上,我們所有舞蹈的風(fēng)格及其美都是它特定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它們所表現(xiàn)的風(fēng)格和美都是由一定的社會實踐決定的,它們這些表現(xiàn)為人體律動和造型的特定風(fēng)格與美開始都是聯(lián)系于一定社會生活現(xiàn)實的具有功用意義的人體動作姿態(tài)的……舞蹈動作作為一種特定的風(fēng)格和美的形成,是由該特定民族的社會實踐決定的。這里有各種歷史的、地域的因素交錯作用,但基本生產(chǎn)勞動方式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但是要說明的一點是,這種勞動方式對舞蹈美的作用大都是在勞動方式具有該社會普遍性意義的時候才能發(fā)生。因為最初舞蹈者進行舞蹈活動時,并不是如我們的‘生活動作典型化’論者所說的那樣是為了反映勞動動作;而是因為這種普遍的勞動動作已成為大多數(shù)社會成員的肌肉活動習(xí)慣。當(dāng)他們需要把自己的過剩精力以舞蹈的集體形式表現(xiàn)出來時,這力量就必然沿著他們的肌肉活動習(xí)慣的通路發(fā)揮出來。事實上,他們正是在這種自己習(xí)慣的肌肉活動中才更體驗到一種生命的自我歡愉……但這種不自覺或下意識發(fā)生的動作卻必然是他們生活和勞動習(xí)慣動作的再現(xiàn)。作為這種感情的外部形式,各民族地區(qū)千差萬別,但又都是由該民族長期的社會實踐所形成的體態(tài)運動習(xí)慣決定的;而作為長期形成的體態(tài)運動習(xí)慣,在個體的肌肉活動組合定性可以交付給下意識的時候才具有意義。”*王元麟:《論舞蹈與生活的美學(xué)反映關(guān)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編:《美學(xu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頁。這段表述其實已暗示了我們“民族舞蹈學(xué)”學(xué)科建構(gòu)的聚焦點與方法論。
其實,就我國當(dāng)代“民族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建構(gòu)而言,值得特別關(guān)注具有世界視野的于海燕。她的《世界舞蹈文化圈縱橫談》在劃分并概述“世界八大舞蹈文化圈”(中國、印度、印度—馬來、波利尼西亞、阿拉伯、拉丁美洲混合、黑非洲、歐洲)后,對東西方舞蹈文化的異同加以了比較,論及了八個方面:“一、東方舞上身、上肢動作多于下身、下肢動作;東方舞面部表情豐富多樣,西方芭蕾身體及四肢表情多些……二、東方舞的戲劇性語言多于技術(shù)性語言……三、東方傳統(tǒng)舞蹈中程式化語言多于示意性語言,西方舞蹈則反之……四、東方舞蹈多以收勢為主,或稱‘主靜’;西方芭蕾多以放勢為主,或曰‘主動’……五、東方舞蹈‘親近大地’,或曰‘立地’;西方芭蕾喜歡趨向天空,或曰‘向天’……六、東方舞蹈講究曲線美、對稱美,西方舞蹈講究直線美和不對稱美……七、宗教信仰的力量使東方傳統(tǒng)舞蹈得以滋生綿延千百年,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穩(wěn)定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使西方芭蕾在400年歷史長河中得以長足進步。就是說,東方舞蹈的發(fā)展生息借助了宗教力量,西方芭蕾的發(fā)展傳播借助了較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八、傀儡戲的發(fā)展,曾經(jīng)為東方傳統(tǒng)舞蹈輸送了有益的養(yǎng)料,進而使傳統(tǒng)舞蹈不斷進步完善;西方生產(chǎn)力的進步,勞動、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促成了一系列社會新舞種的誕生,如迪斯科、霹靂舞、靈魂舞等等。”*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3頁。這正是“民族舞蹈學(xué)”之前驗明正身的“比較舞蹈學(xué)”的研究。
結(jié) 語
關(guān)于“民族舞蹈學(xué)”學(xué)科建構(gòu)的若干思考,是由“非遺名錄”舞蹈“進校園”所引發(fā)的。這個“進校園”不同于我們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的中國民族民間舞“進課堂”,也不同于“高雅藝術(shù)進校園”的展演活動。那時“進校園”主要是作為“表演舞蹈”素材的教材建設(shè),作為與之相關(guān)的職業(yè)舞者的能力培養(yǎng)。因此,深入民間的采風(fēng)或多或少會帶有教材建設(shè)的代表性、訓(xùn)練性、系統(tǒng)性的考慮;與中國民族民間舞教材建設(shè)最具關(guān)聯(lián)性、也最具提升性的是“教學(xué)法”的課程建設(shè)。現(xiàn)在我們關(guān)注的是“進校園”的“非遺名錄”舞蹈的本真性、原生態(tài)和綜合化,這一工作將需要“民族舞蹈學(xué)”的指導(dǎo),也必然促進這一學(xué)科的積極建構(gòu)。歸納以上思考,我們想說的意思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民族舞蹈學(xué)”是一門以“文化人類學(xué)”,特別是以這一學(xué)科下位學(xué)科“民族學(xué)”(也即“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學(xué)理來觀照研究舞蹈的學(xué)科。雖然以“民族學(xué)”的學(xué)理為主,其實也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文化人類學(xué)”的另兩個下位學(xué)科——“考古學(xué)”和“語言人類學(xué)”。二、“民族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建構(gòu)無須“重打鑼鼓另開張”,可以積極借鑒“民族音樂學(xué)”學(xué)科建構(gòu)的已然成果。事實上,“民族學(xué)”視野中的舞蹈研究,幾乎就難以脫離音樂來進行。庫爾特·薩克斯認(rèn)為“‘藝術(shù)’一詞不能闡明舞蹈的全部內(nèi)涵”,他其實還有一段更精彩的表述:“在原始社會里,一般的舞蹈經(jīng)常用歌聲伴奏,一切歌曲都是為舞蹈編造的;事實上,除了舞蹈歌曲之外就沒有別的歌曲了……”三、“民族音樂學(xué)”在學(xué)科定形的建構(gòu)中,梳理了從早期“比較音樂學(xué)”發(fā)展而來的進程,也梳理了“音樂人類學(xué)”“音樂文化學(xué)”“音樂民俗學(xué)”乃至“音樂民族學(xué)”等稱謂的整合。這也給我們當(dāng)下“民族舞蹈學(xué)”學(xué)科建構(gòu)過程中的積極整合提供了鏡鑒。四、在“民族舞蹈學(xué)”的相關(guān)學(xué)科建構(gòu)中,舞蹈學(xué)界與音樂學(xué)界有較大差異。舞蹈學(xué)界似乎尚未見成熟的“舞蹈人類學(xué)”“舞蹈文化學(xué)”“舞蹈民俗學(xué)”等等,但有相對完備的“中國民間舞蹈文化”“中國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舞蹈生態(tài)學(xué)”,是在音樂學(xué)界未曾謀面(未見“音樂生態(tài)學(xué)”)、但卻深度關(guān)聯(lián)于“民族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建構(gòu)。五、“舞蹈生態(tài)學(xué)”的成功建構(gòu),給我們最重要的啟迪是必須用“生態(tài)學(xué)”的學(xué)理來彌補“民族學(xué)”乃至“人類學(xué)”的欠缺與不足;同時,也使這一方法相近、對象同一的學(xué)科建設(shè)在認(rèn)識上具有更大“公約數(shù)”,在實踐中具有更大“普適性”。六、比較正式地提出“民族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建構(gòu)并非說我們既往缺乏這方面的研究,而是指我們既往缺乏這方面研究的自覺——特別是指缺乏學(xué)科建構(gòu)“科學(xué)性”的自覺。我們希望“民族舞蹈學(xué)”學(xué)科建構(gòu)有個“名正言順”的開端,以便今后能以“民族舞蹈學(xué)”的名義開展學(xué)科研討、豐富學(xué)科內(nèi)涵、充實學(xué)科肌理、完善學(xué)科構(gòu)成。讓我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讓我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