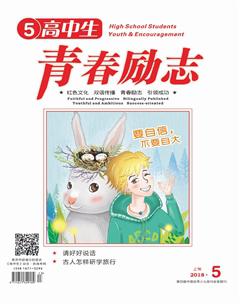在黑暗中唱起歌兒
李小刀

16歲時,在學(xué)校參加一場足球比賽,我?guī)蜓剡吘€向?qū)Ψ角蜷T狂奔,一不小心,球踢偏了,但也沒出界。就在我低頭趕到球前時,場外的一個學(xué)生突然起腳。我甚至沒來得及閉上眼睛,就直接被那個足球砸到了眼球。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眼前一片發(fā)黑”。于是,左眼失明,成為我青春歲月的紀(jì)念。
我靠著一只右眼完成了學(xué)業(yè),找到了工作。每次見到視障者,我都油然而生一種親切感。也許在我的心底,尚存留著一絲揮之不去的恐懼吧。恐懼這只獨眼,還能支撐我多少年?
巧的是,在我的讀書和采訪經(jīng)歷中,還真的有三位視障者給我以啟示。
第一位叫郭紅仙,五年前我采訪過她。這個農(nóng)家女子生下來就雙目失明,卻在11歲時母親去世后,就挑起生活的擔(dān)子。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苦情故事,那你就錯了。這個幾乎沒有正經(jīng)上過學(xué)的女子有著這塵世間難得一見的一顆詩心。
從童話到散文,再到詩歌,一段段優(yōu)美的文字如溪水一樣從她筆尖流淌出來。接受我采訪的時候,她已經(jīng)發(fā)表了幾十篇作品。第一篇作品發(fā)表在《廣播電視報》上,對方給她寄未了20元錢稿費。郭紅仙一說到這就笑:“當(dāng)時我‘暈暈乎乎,北都找不著了。”我問她稿費用來干什么了,她又笑:“當(dāng)然是買菜了。難道我還找個相框裝起來不成?”
我仍舊記得那天我在她居住的村莊繞來繞去的情景,記得郭紅仙干凈的家,記得她寫的一首詩的題目——“給我一天光明”。
第二位叫張娜,她在一個學(xué)校有著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那天,我見到她熟練地上樓梯,根本不像視力不好的人。她笑著說:“我只能看見人的輪廓,這樓梯,我走得太熟了。”和郭紅仙一樣,張娜也有一顆詩心。在長久的屬于自己的世界里,讀書和寫作占據(jù)了她大部分時間,也給了她無與倫比的快樂與滿足。她的一篇文章獲得了某個寫作大賽的全國一等獎。她喜歡朗誦,并把自己朗誦的作品上傳到博客……
第三位叫周云蓬,“九歲失明,學(xué)會了彈琴,寫詩,云游四方”。他這樣看待命運:蛇只能看見運動著的東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個太陽。深海里的很多魚,眼睛退化成了兩個白點。能看見什么?不能看見什么。這也是他的命運。他熱愛自己的命運,它跟他最親。它是專為他開、專為他關(guān)的獨一無二的門。
于是,周云蓬背一把吉他坐上了綠皮火車。他寫下“春天/責(zé)備沒有靈魂的人/責(zé)備我不開花/不繁茂/即將速朽/沒有靈魂”。他唱著海子的《九月》,也唱著自己寫的《中國孩子》。他發(fā)動眾多歌手,制作了童謠專輯《紅色推土機》,收入全部用于幫助貧困盲童,為他們購買讀書機、樂器、MP3。他寫道:這個計劃只是一聲遙遠的召喚,就像你不能送一個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凈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邊的樹、垃圾箱、風(fēng)吹的方向、狗叫聲、晚炊的香氣,會引導(dǎo)他一路找到家門。
感謝生活,讓我在16歲時,那個眼前一片漆黑的時刻,回到陽光底下。我依然感恩,感恩我能夠用右眼看到這些人。世界于他們而言,是一片黑暗,但他們坐在黑暗里唱起了歌兒。我想,那歌聲就如同干凈光滑的盲杖,教給看不見和看得見的人們,如何在這世界上尋找道路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