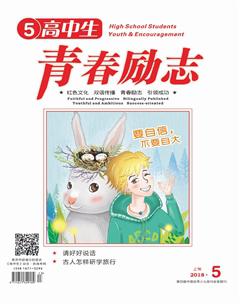不屬于我的家,開啟了我的夢想
李瓊


我還記得6歲那年,光線填滿寬敞的房間,母親手中吸塵器的嗡嗡聲從一個房間傳到另一個房間。
我還記得9歲那年,我常常懶洋洋地躺在長沙發上,看迪士尼卡通片,電視機放在墻上的一個內嵌空間里。
我還記得12歲那年,每個房間都掛著在西班牙鄉間拍攝的家人照片。
我還記得14歲那年,我在偌大的房子里一點點地給地毯除塵,折疊剛剛烘干的色彩柔和的襯衫。
我喜歡那棟房子。我喜歡陽光透過窗戶傾灑進來的樣子,仿佛可以掃清所有愁云。我喜歡自己總是可以在任何一個平坦的物體表面找到一本書或雜志。
但母親使用的吸塵器不屬于我們。我們從未付過有線電視費。照片上的人物也不是我的家人。
我一周只能見到一次自己清理的地毯,我從未穿過自己折疊的那些色彩柔和的襯衫。那棟房子不是我的。母親只是清潔工,我是她的幫手。
大約20年前,我的父母以難民的身份從摩爾多瓦來到美國。母親打過許多種零工,但我一出生,她就認定自己要做點不一樣的事情。她在報紙上登了一則提供房屋保潔服務的廣告,一對教授夫婦聯系了她。這成了她的第一單業務,他們的房子成了我們維持生計的基石。經濟衰退未了又去,但母親每逢周一和周五都要去那里,有時周日也過去。
她整日戴著藍綠色的乳膠手套,手持藍色的胡佛吸塵器,給仿佛有幾米長的地毯除塵。她擦過的鏡子沒準可以堆疊成小型的菲利普·約翰遜摩天大樓。這對她來說并不新鮮。吸塵器和手套或許有些新鮮,但這份工作并非如此。
在摩爾多瓦,她曾在家里種黃瓜和西紅柿。她曾花無數個小時跪在泥土里,像教授指導學生那樣用心,以善良和積極主動的態度侍弄她的蔬菜。現在,她耕耘的蔬果被吸塵器取而代之。
那兩位教授的家讓我得以一窺(更富裕的)另一半人的生活。他們很少待在家,于是我便觀察他們留下的痕跡:攤在廚房桌子上稍稍發皺的《紐約時報》,滿滿當當的私人圖書館中翻到一半就倒扣著的書,總是停留在國家地理頻道的電視。我把這些痕跡當成名人效應下的成功之路。我開始從學校的圖書館往外借書,并經常看新聞。
他們的家為我的夢想提供了庇護之處。在那里,我這個戴著眼鏡的電腦迷從《彭博商業周刊》上知道了一個名叫硅谷的神秘地方。在那里,我這個移民的兒子讀到了一個名叫巴拉克·奧巴馬的年輕參議員立志要做美國總統的故事——他也是移民之子。
我從教授家看到過的生活告訴我,在美國,移民也可以成功。工作可以用雙手和頭腦來完成。兩位教授讓我看到了他們獲得成功的要素,我也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的路。
最終,吸塵器的吸力養活了我們一家。吸塵器的嗡嗡聲提醒著我,我為什么有機會開著叮當亂響的小汽車去上學。我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我,是因為我的媽媽往美國夢的公式中傾注了大量勞動。她用藍色胡佛吸塵器為我的生活撐起了一片天。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畢業證書為她撐起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