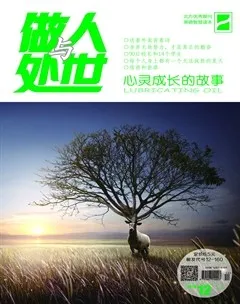金銀花姐姐
曾旭鵬
金銀花姐姐并不姓金,但確實名字中有銀花二字。她教語文,在一次課上講述草本植物時,調皮的我們現學現用地給她冠了名。之所以綴上“姐姐”而不是老師,除了她年輕以外,是因為她脾氣很好,就像鄰家大姐姐。但我那時喜歡下課的金銀花姐姐,不喜歡上課的她,因為我的語文成績實在太差。
就像藥材中很尋常的金銀花一樣,金銀花姐姐長得并不出眾。但是她是從城里來的,讀的書多,生活條件也好,氣質就顯得和鄉鎮老師不一樣。她個子不高,卻一頭長發。她臉上有點點雀斑,但膚色很白,所以襯得斑點有些突兀。來我們學校時,她剛大學畢業,少女心性尚未完全褪去,沉思或者生氣時,她的嘴巴會緊緊地閉起來,微微噘起,顯出一副能說會道的樣子。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我經常會在考試后見到這容貌。
又是一次考試失利,金銀花姐姐把我叫到教室外,她嘴巴微噘,雙手少見地背在身后。很少生氣的人嚴肅起來是很可怕的。我低頭,眼睛盯著她的長靴鞋尖,等待狂風暴雨的到來。“你就真的這么不喜歡語文?”金銀花姐姐淡淡地問。我詫異地抬頭,金銀花姐姐的平靜很反常,然后我看到了她的眼睛。
很難說小學四年級時的我,能不能體會什么是失望和沉重。那雙平日里明亮和藹看著我們的眼睛,布滿著對一個不成器學生的失望,還有只是屬于一個教師的挫敗。
“沒有啊。”我嘶啞著說。金銀花姐姐在我身上傾注了心力,無論是課上還是課后,無論是她忙或者不忙,只要我去問,她總是極開心的。她也和我約定,我稍有進步,就送我那時很少見的小瓷人。她從來不用請家長來威脅我,哪怕我學習很差。改我的作業用紅筆寫的話是最多的,不是批評,是讓同學們看了都嫉妒的溫婉的鼓勵。上課除了講臺,我的周圍就是她最經常來的地方,她來了,我莫名地能靜下心來。她會在我讀完一段課文后摸摸我的頭,時間久了,我就敢抬起頭看她,只看到如花如虹的笑……接下來的對話我忘記了,只記得我堅定有力地說:“老師!我一定要得A!”
之后,我將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在了語文學習上,大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態勢。一段時間后,金銀花姐姐把我叫了出去:“你不能這樣學,這樣你會很累,反而更討厭語文。”金銀花姐姐一臉正色道。那時的我搞不懂她在說什么,畢竟我只是為了贏得金銀花姐姐的小瓷人而學習語文。金銀花姐姐很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并及時把我拉回了正軌。她為我制訂了一份詳盡的計劃,什么時候學數學,什么時候學語文,什么時候做摘抄,什么時候讀課外書,什么時候寫作文……。她還將家中的藏書帶幾本給我,助我拓展課外閱讀量。那時在農村,一本文學著作在當時的父母看來,是花家畜一周的飼料費,買回來一個并不好看的裝飾品,是“富家仔”才會做的事情。
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書的世界讓我陷入了語文天地不能自拔,吃飯看,下課看,放假看。許多原本被她仔仔細細保護著,珍重地交到我手上的書,還回去的時候總是伴著污漬和卷曲,還有小男孩因為玷污了貴重的東西而局促不安的眼神。金銀花姐姐每次都只是彎下腰,笑瞇瞇地說,這才證明我有認真努力在看書,她的努力沒有白費。于是我的眼睛再度亮了起來。
一個10來歲的孩子,為了回應他人的期望而爆發出巨大的能量,本來會把自己也一并燒疼。幸而有金銀花姐姐,像一味平和、清熱解毒的良藥,挽救了這個過度熱情不講方法的孩子,并且潤物細無聲地影響了他以后的日子。
期末考試,所有的付出終將得到回報,以前不及格的我順利得到了A。作文尤其寫得出色,被當成范文在班上讀。這對金銀花姐姐和我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勝利,滿臉笑容的她眼中完全沒有了陰霾,只有喜悅。放假之前開閉校式的時候,金銀花姐姐送了我那個小瓷人,蠟筆小新樣式的,手托著腮,噘著嘴,像極了金銀花姐姐生氣的樣子。
我升學后,曾回母校看過金銀花姐姐。學校變得嶄新,金銀花姐姐的臉上卻有了歲月的痕跡。她一如多年前那樣叫著我的名字,踮起腳尖,伸長手臂,夸張地贊揚著我的身高;像母親那樣細致地問著我的生活、學業上的瑣事,笑瞇瞇地和我一起發牢騷。一個人,她和我毫無血緣關系,但是就是這個人,縱使你離她千里之外,你依舊會回憶她,感激她,祝福她;你也會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她,親近她,把自己的心事掏給她。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