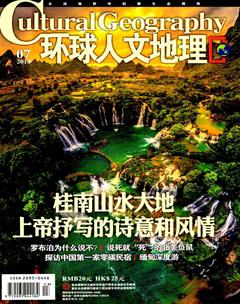博藏/遺產/建筑/方言
孝端皇后寶鳳冠
鯤艮
“紅妝十里,鳳冠霞帔。”大概是今人頗為向往的場景,可人們大都不知,明朝皇后所佩戴的鳳冠到底何其華美,更不知鳳冠所代表的尊卑等級制度。
古時男子成年要行冠禮,以此告別童年。孔子的弟子子路在被逼入絕境時說道:“君子死,冠不免。”由此可見頭冠之意義非凡。《易·系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古時君主為了統領天下,需得明尊卑、肅綱紀,統冠制而別等差。因此,頭冠不僅是一種服飾,更是體現尊卑等級的法度。
漢代,男性禮冠制度就已完備。因古時女子地位不如男子,女冠之始也遠遠遲于男冠,直到宋朝,才明確女冠的禮服冠制。禮服冠為人們參加重大慶典時所戴,最高品級的禮冠是皇后在受冊、謁廟、朝會時佩戴的鳳冠。到了明朝,鳳冠的制作日趨成熟,達到了工藝的巔峰。
1956年,北京定陵出土的明朝鳳冠,其精致華美令人驚嘆。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鈞及其妻妾——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后的合葬墓。定陵出土了四頂鳳冠:六龍三鳳冠、九龍九鳳冠隸屬于孝端皇后,十二龍九鳳冠和三龍二鳳冠隸屬于孝靖皇后。其中,最為精致華美的是孝端皇后的六龍三鳳冠。
此鳳冠以漆竹絲作胎,質輕而極具韌性。通體飾翠鳥羽毛點翠的如意云片,冠口外緣一周嵌紅藍寶石,其間飾有珠花,里為金口圈。鳳冠上共飾金龍六,翠鳳三:正面頂部正中—金龍,口銜珠寶滴傲然屹立,看來端莊而高貴。兩側在如意形云頭上各飾一飛龍,亦是口銜珠寶流蘇串飾。背面再立三金龍,作欲騰飛之勢。六尾金龍是由皇家精湛的花絲工藝制成,最后再經過“咬酸”(酸洗過程)給金龍提亮。鳳冠中層裝飾有三只翠藍色飛鳳,鳳首朝內,口銜珠滴。在金龍翠鳳間,有大小朱華樹穿插其中,珍珠寶石作梅花狀環繞其間。冠后部飾六扇由珍珠、寶石制成的“博鬢”,呈扇形左右分開,落落大方,儀態萬千。鳳冠上通過爪鑲工藝(用金片制成寶石“托兒”,其兩側焊出兩爪,緊緊抓住寶石)共嵌寶石128塊,珍珠5449顆,雍容華美,極盡奢華。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古代女性禮冠中罕有龍鳳。唐代后妃禮冠的基本制度是采用花樹和博鬢,宋承唐制,但有一個重大變化——在冠上先后添加了鳳與龍的形象。明初基本承宋制,《明史·輿服志》記載,皇后禮服為九龍四鳳冠。定陵出土的四頂鳳冠上的龍鳳數目與明初規定不同,可見明朝晚期對原定制度已不再嚴格執行。
明朝中后期以來,鳳冠的裝飾日趨精美繁復,帝后生活極盡奢華。嘉靖年間,明世宗下詔廣搜珠寶異石,僅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采辦的寶石,就花去銀兩4萬多。后來神宗親政,亦效法其父祖,每年都下詔采辦,僅一次就要采珠五千余兩。在常年無節制的采買中,百姓民不聊生,國庫貯銀也揮霍一空,明晚期宮廷如此豪奢則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酒泉夜光杯
天欲雪
皎潔月色下,盛滿美酒的夜光杯蒼翠欲滴,通體晶瑩。對著茫茫風沙與邊關雪月,戍邊將士們若能用此杯飲酒,也算是孤苦軍旅生活中難得的慰藉吧。
提起夜光杯,令人不禁聯想到這樣一幅畫面:羌笛悠悠,關山斜陽無際。霜營吹角,對夜難眠。唯飲一杯雪月直漫天明。月是“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的關山月,杯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的夜光杯。
古人用夜光杯飲酒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
《海內十洲記》記載:“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因為玉石比熱容小,可凝氣成水,故空杯一夜,天明水滿,即為“常滿”,又因杯壁透薄如蟬翼,月下斟酒,將呈現出晶瑩剔透的光彩,故名為“夜光常滿杯”。由此可見,夜光杯最早來自西域。
今天我們所說的夜光杯,大多指酒泉夜光杯。酒泉是漢代河西四郡之一,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絲綢之路的重鎮。如此一來,便和古書中的記載合上了。酒泉夜光杯是采用祁連山上的墨玉雕琢而成,祁連玉內含有多種礦物質,呈現出淺綠、翠綠、墨綠等多種顏色。用其制出的杯盞紋飾天然,色彩斑斕,有的蒼翠晶瑩,有的清澈疏淡。夜光杯質地獨特,即使在炎夏握住杯身,也令人頓覺清涼冰爽,酒杯盛燙酒不炸,斟冷酒不裂,碰擊不碎,用其斟酒。甘味香甜,日久不變。
夜光杯的制作。前后一共要經過28道復雜工序。首先,師傅們選擇祁連山老山窩子里的上乘玉料,根據不同的形制將玉料切成不同大小的圓柱體,再按一定尺寸切割。經5道工序制成毛胚,之后再切削、精磨出夜光杯的初型,掏膛后夜光杯終于定形。最后還要經過細磨、沖、碾、拓、拋光、燙蠟等14道工序,再用馬尾網打磨,才能制成一盞夜光杯。夜光杯傳承人黃越肅師傅說:“以前只能用腳踏、手拉,使機器轉動磨制夜光杯,現在設備更新了,可大半功夫還得靠手工,就算是爐火純青的老師傅制作一盞夜光杯也要花幾天的時間。制作夜光杯是個細活,靠的是經年累月做出來的手感,輕了重了都不行。用來研磨玉石的是金剛砂,容易傷到手指,一不小心就會把已成型的杯子磨壞,制作了好幾天的杯子就前功盡棄了。”祁連山終年白雪皚皚,在海拔四千米的雪山上采玉極為困難,加上運輸不便,供應的玉料十分有限。而制作夜光杯,工藝復雜,玉料的利用率也只有60%左右,其珍貴自不必說。
因為祁連玉質地細密,加上工藝獨特,酒泉夜光杯的表面張力極好,若將杯中盛滿酒,酒可過杯口而不溢。夏夜用此杯飲酒,杯壁透薄瑩翠,內里似有奇異光彩,杯面則浮著一輪明月,晃晃悠悠,清涼入口。尤為月下對飲,令人心曠神怡,詩興大發。
新天鵝堡
天天天睛吃葡萄
新天鵝堡的南北兩面坐落著清澈的阿爾卑斯湖和天鵝湖,在黛綠的云杉與雪松之間,美麗的城堡遺世獨立。這是孤獨的國王留給世人的一個未完的夢境。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德國那樣擁有如此眾多的城堡,據說全德國有近2萬多座古城堡。城堡最初的功能是用于防御,后來逐漸成為標志皇族權力與地位的建筑。而19世紀建造的新天鵝堡,如今已成為整個德國的象征。
新天鵝堡的建造者是德國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他對政事毫無興趣,反而熱衷于歌劇和建筑。國王15歲時,就被瓦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里中世紀的天鵝騎士所打動,并于1869年,在巴伐利亞西南部阿爾卑斯山麓的天鵝堡遺址上。開始建造自己夢想中的新天鵝堡。國王邀請了劇院畫家波契(Pocci)和舞臺設計師克里斯蒂安·揚克(Christian Jank)共同設計,他們根據國王夢想中的騎士故事設計出了一座比中世紀騎士之夢更為夢幻的城堡。城堡的建造耗費了大量物資。單在1872年,就用了450噸的水泥、1845立方米的石灰。這座城堡共設計有360個房間,歷時17年的建造卻只有14個房間依設計完工,因國王在1886年就逝世了,他只在新天鵝堡內居住了172天。
從瑪麗安橋望去,綿延的阿爾卑斯山脈令人心境豁然而寧靜,通體雪白的新天鵝堡優雅地佇立其間,黛藍色的塔尖高聳入云,尖峭而空靈。城堡整體沿著中軸門塔呈南北基本對稱,由火紅的門樓塔、南北面的7個棱堡、下沉小廣場、前院和主堡構成。由于受到古典復興與浪漫主義思潮影響。城堡外形呈現出哥特復興風格,又在國王與設計師天馬行空的幻想下,更添了許多創意和浪漫。
城堡的建制雖浪漫但又等級森嚴。堡內廳堂多為嚴謹對稱的巴西利卡形制空間,但堡內又隨處可見天鵝元素的夢幻裝飾。主堡共設計了5層,每層的功能布局都不同,主人、貴賓與傭人的生活空間、甚至使用的樓梯都嚴格分開,體現出嚴密的等級制度。國王雖一心向往中世紀生活,卻并不排斥工業革命帶來的新科技,城堡內有當時最為先進的設施:電氣化烤箱、高壓蓄水池、運送燃料的卷吊裝置……
與其他城堡不同,新天鵝堡內的壁畫并沒有大幅描繪古希臘羅馬神話,堡內隨處可見的則是瓦格納歌劇中的愛情。無論是起居室的《羅恩格林》,還是書房的《唐懷瑟》,都表現出國王向往個性、自由、浪漫的愛戀。與之相反,御座廳的壁畫卻具有嚴格的體系規范:國王和耶穌被同時描繪在上方的穹頂,四天使守于四方。傳道士立于兩旁,整個畫面展現出堅定的宗教秩序。但實質上卻在強調君權神授的思想。
規制和自由,復古與創新,宗教和愛情。這些矛盾在新天鵝堡內糅合成一種兼具理性與浪漫之美,就像當時在風雨飄搖中不斷更迭的德國社會,又像那位一生充滿爭議與傳奇的國王。
撲街
魚香肉絲
圖為香港的街頭鬧市,無論怎樣發展、蛻變為國際化大都市,那曾獨屬于香港的市井江湖氣息,卻生生地根植在每一代香港人的骨髓中,已成為他們的文化印記之一。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粵語作為影響力較大的漢語方言,在音調方面與普通話的四聲聲調不同,有9個聲調和2個變調。音域寬廣的同時,還保留有大量北方話已經丟失的古漢語的特點,比如中古漢語韻母的塞音韻尾和純音韻尾,以及一些古漢語用語,如“食(吃)”“行(走)”“企(站)”“走(跑)”等這些在我們現代普通話中基本上不再常用的詞語,現代社會已經很少有人用“你食了沒?”或者“你要不要行?”這些話了。
粵語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特殊詞匯的來源比較復雜多樣,有的是根據英語發音而來,比如“波(球Ball)”“的士(計程車Taxi)”“菲林(膠卷Film)”;如果不是本地人,根本無法理曉其中所蘊含的喻意,特別是一些罵人的話,熟悉香港電影的人一定不會對這個詞語陌生:撲街。
“撲街不是粗口,撲街面家鏟才是粗口。”電影《出埃及記》中的張家輝曾這樣說到。的確,相比“頂你個肺”這樣的粗口,“撲街”不涉及敏感詞匯,短短兩字既能表達憤怒,也帶有調笑之意,用法多樣,適合多種語境,就連根正苗紅的香港無線電視臺(TVB)播出的電視劇中。也經常可以見到這個詞從演員嘴里說出來。它除了常見的罵人用途外,還能用作熟人之間的彼此稱呼——“撲街仔。就屬你精!”這里的“撲街仔”你就不能說它是侮辱人的意思;有時還能是一種語氣詞,比如你覺得自己今天運氣非常不好,掉了錢包、錯過了公交。心里的火無處發泄,只能說一句:“唉,撲街!”既不罵別人,也不怪自己。就好像國語中的“唉。倒霉!”一樣。更多是一種怨氣的發泄。
那么,“撲街”一詞到底是怎么來的呢?
“撲街”,粵語讀作“pok gai”,“撲”即摔倒、撲倒,“街”就指街上。“撲街”連起來,就是摔倒或撲倒在街上之意。其來源有兩種常見說法,一說是清朝末年。廣州出現大量的反清志士,這些反清志士被捕后,往往會被押赴至“法場路”處刑。被處死的志士數不勝數,他們的尸首往往無人收回,就這么撲倒在街口,久而久之,人們就用“撲街”來形容橫死街頭的人,后來更被當做詛咒別人的話語,但語氣不如“冚家鏟”(意指別人全家死光光)來得激烈。另外一種說法則更為有趣,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涌入大量英國移民,而其中身處上流社會的公子哥都普遍愛好打網球,但他們大多都是花花公子,喜好結交漂亮姑娘的同時又不負責任,所以老百姓們十分討厭這些以體育為幌子出來勾搭少女的有錢人,但當時外國人在香港還是可以橫著走的,所以大家都不敢直接叫他們壞蛋,就用英文“Sport Guy”來稱呼他們,慢慢便演化為粵語諧音“死撲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