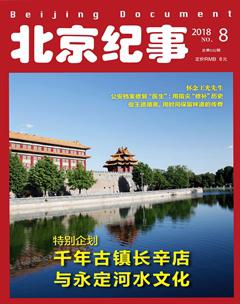公安檔案修復“醫生”:用指尖“修補”歷史
張巖 胡愛華
噴水、刷漿、拼接、托裱、上墻 ,經過十余道純手工的修補過程,一件件原本破舊不堪的老舊檔案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在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檔案處的檔案修復師范三成看來,這就像醫生妙手回春,讓危重的“病人”重獲新生一樣,“拯救”檔案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檔案是對歷史的承載和訴說,是最原始、最權威的證明材料。時光流逝,紙質檔案會經歷腐蝕、破損甚至滅失。為了讓珍貴的檔案永久保存,“修裱”就成了檔案館要做的事情。近日,記者走進全國公安系統唯一的檔案保護修復技術中心——北京市公安局檔案館檔案修復室,在這里看到,60多平方米的修裱室里格外安靜,修復師們忙碌地工作著。
打開一卷殘破的案卷,揭粘、除塵、去污、濕托、展平、刷漿、干托、雙面字跡加固……經修復師們的妙手,一頁頁布滿塵土、殘缺污損的老舊檔案重獲“新生”。
檔案修復師劉雪立告訴記者,修裱工作室有件“重器”,那就是朱紅色的裱糊大案,是修裱工作的操作臺。它的制作工藝來自故宮博物院,檔案修裱工作大部分操作都需要在這個工作臺上完成。而后她用鑷子認認真真地拼接大案上一張破損的檔案,小心地撥調,耐心地比對。
“只要這頁紙上還有一個字我們都會進行‘搶救,有時上面缺了一角,即便能猜出是什么字我們也不能填上,要保持內容的原狀,涂改后就失去法律效力了。”范三成是從事檔案修復工作近30年的老民警,目前在修復室負責指導修裱檔案。他告訴記者,修復室目前接收的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城區派出所保管的、損毀比較嚴重的居民檔案。“我們的修復工作主要是為群眾服務,很多群眾在處理涉及房產等問題時往往需要檔案證明,他們就會到派出所進行網上登記查詢,檔案館收到申請信息后會在卷宗中進行查詢,有破損的及時修補。”范三成說,純手工修復一頁檔案一般會經歷近20道工序,修復師們每天的工作量是33頁,具體時間還要看檔案受損的程度,有時只是補一張檔案的洞就要一天。
說話間,只見一名修復師用鑷子小心夾起殘留在下一頁檔案上的紙渣,放在正在修補頁的合適位置,并用補紙把附近的洞補好,一點點把補紙的邊緣摘掉。這個過程中,她每隔幾秒鐘就用噴壺在檔案上噴些水,以保持濕度,并讓字跡逐漸清晰顯現。
“所有的修補工作都完成后,檔案就可以上墻晾著。經過幾天時間,潮濕的檔案就會干透,變得非常平整,然后我們再裝訂成冊。”隨著范三成手指的方向,記者看到了一個別有洞天的小屋子。在一排排鏤空木質的墻板上,貼著一頁頁已經修復完畢上墻晾干的檔案。據介紹,這個墻板也是根據故宮博物院的特殊工藝制成,木板鏤空的部分糊上了20多層宣紙,組成平整的墻面,墻板更透氣,便于風干。
范三成介紹,目前修裱室重點對1949年之前日偽、敵偽時期破損的戶籍底簿進行搶救修復。對紙張纖維斷裂或板結的檔案等,需要人工一點一點剝離出來,經過十幾道修補工序,才能修復。為給記者直觀的感覺,他拿起一張破損的戶籍底簿,開始拼接,覆背,這一張A4紙大小的檔案紙,修復了整整兩個小時。
范三成坦言,破損的檔案修復完畢后,看到它完整無缺的時候,會有一種成就感:因為病入膏肓的病人看病,總是希望醫生能挽救他們的生命。實際上不管是古籍修復者也好,還是檔案修復者也好,我們修復者就是破損古籍、檔案的醫生。可以這么說,我們重新給它以生命。因為如果檔案破損特別厲害,我們不進行修復的話,這份檔案或者這份歷史就消失了。在歷史的長河中,見證歷史者會慢慢老去,記錄歷史的紙張也會慢慢殘破,他們無法阻止前者的發生,只能在時間的“手”中“搶救”后者。
據悉,經過北京市公安局檔案館檔案修復室辛勤努力,經過他們“醫治”而“復活”的公安檔案資料共3800余卷,近40萬頁,這些檔案成為民生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至今,北京市公安局戶籍派出所利用戶籍底簿、人口卡片等檔案資料,接待人民群眾70萬戶次,在查證親屬關系、查找親人,辦理落戶、退休、低保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切實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編輯·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