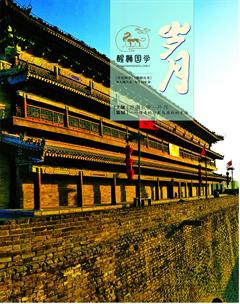漢唐長安樂舞與百戲
王吳軍

遠古,音樂和舞蹈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稱為“樂舞”。這些樂舞與先民們的日常生活、戰爭等多方面有關。在樂舞的藝術長河中,漢朝的樂舞以清新、蒼勁、壯美的藝術風格而獨樹一幟。在歷經春秋戰國的紛爭之后,漢朝的樂舞以熱烈的姿態,展示了泱泱風采。
漢:清新蒼勁,泱泱風采
和先秦樂舞的雍容典雅不同,漢朝長安的樂舞之風洋溢著豪放、質樸的藝術魅力,煥發出泱泱中華實現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之后的勃勃生機。漢朝時,中國傳統文化正處于對內各民族之間往來密切、對外交流空前活躍的時期。此時,長安作為都城,其樂舞的風格不僅豐富多彩,而且頗為包容。來自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樂舞就深得漢高祖劉邦的青睞,登堂入室,成為當時長安的宮廷雅樂。
而此時,廣泛盛行于民間和宮廷的“百戲”中,自然也不乏來自中亞各國藝人的舞蹈雜技表演。《漢書·武帝紀》中記載:“(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元封)六年(前105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所謂“角抵”,就是“百戲”。百戲是中國古代漢族民間表演藝術的泛稱,產生于秦漢時期。《漢文帝篡要》中記載:“百戲起于秦漢曼衍之戲,技后乃有高短、吞刀、履火、尋檀等也。”可見百戲是對漢族民間諸種表演形式的稱呼,尤以雜技為主。漢朝時,樂舞和雜技常常混雜在一起。在長安城里,皇宮常常組織歌舞雜技演出,規模空前,吸引了京城內外甚至數百里遠的民眾前來觀賞,足見漢朝的舞的泱泱壯美的藝術風格和藝術魅力。這種表演不僅以樂舞、百戲活動顯示朝廷與百姓同樂、天下升平之氣象,同時,也多以場景壯美的大型樂舞、百戲以宴請四海賓客。如漢宣帝元康二年,朝廷將楚王之女解優公主嫁給烏孫王時,就在長安城的平樂觀演出大角抵的百戲,奏音樂送解憂公主遠嫁,招待匈奴使者及其他外國賓客。漢文帝、漢景帝時,曾設酒池肉林以饗四方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曼延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到漢武帝時,以百戲招待外國政要和使者,顯示大漢王朝的強盛與繁榮。可見,不僅來自民間的諸多歌舞雜技節目登上了王公貴族的大雅之堂,而且西域那些豐富多彩的文藝表演也成為招待國賓、展現大漢風光的宮廷雅樂。漢朝是繼先秦樂舞百戲之后,又樹立起了一座樂舞百戲發展的豐碑,它以大度、包容的藝術風格載入了中華史冊。
漢朝的長安城里,樂舞和百戲充滿了現實主義和個性張揚的藝術感染力,直抒心志、緣情而表演,一掃先秦宣教政化、懷舊復古之遺風,令人耳目一新。這種感懷而動,即興表演的風格,在漢朝蔚然成風,史不乏書。如漢朝長安城里的宴會中,廣為流行以舞相屬的禮節性交誼舞蹈,也就是在宴會過程中,賓客之間往往會相邀起舞。這種以舞相屬的社交舞蹈,就帶有明顯的即興特色,既是禮節,又有著自娛自樂的色彩。
《漢書》中記載說,西漢的長沙定王劉發,是漢景帝之子,由于其母不受寵,故其封地小而貧。有一次,諸王到京城長安朝拜皇帝,劉發遵旨以歌舞祝福皇帝。起舞時,劉發故作縮手縮腳之態,觀者都嘲笑他動作笨拙,皇帝也感到奇怪,就問他為何展示此種舞姿,定王劉發回答說:“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可見這種即興而舞的樂舞風格,不僅具有應酬娛情的功能,而且還可以宣泄情感胸襟的憂樂。
漢朝長安的樂舞和百戲的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浸潤有關,也與朝廷自身的藝術審美取向有關。漢朝初年,意識形態以黃老思想為宗,摒棄奢華而倡導樸素,這就為源于生活的樂舞和百戲的創作風格提供了良好而寬松的生存發展空間,而親近百姓、娛樂民眾的風格又無疑與統治者的與民休養生息的執政理念相輔相益,因此,當時長安城里的王公貴族們自然也積極推動并樂于參與其中。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本是一介平民,自稱是“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來自社會底層而且以好楚歌、楚舞而聞名于世,其言行中不乏楚地之風的豪邁粗獷。而且,楚文化的浪漫、清爽與黃老道家的率性而為、返樸歸真的宗旨本來就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劉邦在楚漢戰爭中,便以四面楚歌之勢而動搖、震撼過項羽士卒的軍心。因此,漢朝長安城里樂舞和百戲弘揚出來的豪邁、矯捷、浪漫,其實是有根源的。
漢朝的長安城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城垣面積達三十六平方公里。人口約達五十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大、昌盛的城市。西漢王朝在長安城設立有大鴻臚,專門管理外交事務。在長安未央宮北的桌街,設立了居處各國使節的使館區。對一些友好國家的國王、君長慕名而到長安的,往往被安置在長安南郊上林苑內的葡萄宮、平樂觀等國賓館。不少國家還送年青的王子到長安學習先進的漢文化。有的回國繼位后,更促進了雙方的友好交往。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到長安拜見漢宣帝。后來,他又親到長安迎娶昭君出塞。以及烏孫迎其在長安的王子回國繼位,鄯善國迎其酋長自長安歸國等,都舉行了盛大的迎送儀式,這使長安城充滿歡樂喜慶,友好祥和的氛圍。外域文化也使長安的人們耳目一新。由西域傳來了箜篌、琵琶、胡茄、胡笛等樂器,胡樂風糜長安。西域的樂舞也在長安流行起來。以歐洲羅馬的魔術師為代表的百戲在長安演出,更使朝野傾動。這些都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
唐:氣勢磅薄,開放自信
唐代,長安城里的樂舞和百戲又有進一步的發展,而且更加專業化。《新唐書·禮樂志》中記載說:“玄宗為平王,有散樂一部……及即位,命寧王主藩邸樂,以亢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宣宗每宴群臣,備百戲。”“咸通間,諸王多習音聲、倡優、雜戲,天子幸其院,則迎駕奏樂。”因此,無論在盛唐還是晚唐的長安城里,百戲始終是王公貴族喜愛的藝術表演形式。
百戲形式多樣,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當時,長安城里的百戲有傀儡戲、參軍戲、排闥戲、渾脫舞、旋盤、擲槍、蹴瓶、飛彈、拗腰、踏球、吞刀、吐火、藏狹、山車、旱船、尋檀、走索、丸劍、跳丸、角抵、戲馬、斗雞、舞劍、擊鞠、戴竿、蹋鞠、相撲、拔河……可以說,人間百藝,應有盡有,百戲的發展推上了一個新高峰。
其中,舞馬是一個精彩非凡的表演節目。《舊唐書·音樂志》中記載說,表演時引舞馬三十匹或百匹,分左右兩部。馬身上披著華麗的錦繡,絡以金銀飾物,打扮得金碧輝煌。奏的樂曲是《傾杯曲》,馬開始舞蹈時,“連騫勢出魚龍變……翩翩來伴慶云翔……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這些馬隨著音樂的節奏而搖頭擺尾,有時像魚躍龍門一樣矯健壯觀,有時像飛鳥一樣輕捷,有時跪倒前膝緩緩徐行,有時隨著急劇的鼓聲而奮力跳躍。舞馬的高潮是馬匹登上三層床榻,旋轉如飛,最后由大力士舉著床榻,馬靜立在榻上一動不動,銜杯曲膝,“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真是難得觀賞到的藝術表演。
唐長安城規模浩大,氣勢恢弘,布局整齊,城垣面積達八十四平方公里,人口達百萬。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和繁盛,長安成為交通發達、商業繁榮的國際性大都會。來自各國的使節、學者、高僧、藝術家、留學生和商人云集于此。大批外國人僑居于此。
貞觀初年,僅突厥降部移居長安的就有近萬家之多。西域的樂舞自漢朝傳人長安后,至唐朝初年已達高峰,貞觀十一年(637年)整理出的十部樂舞,即《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和《高昌樂》這些樂舞,大多是西域諸國的。以鐘罄等打擊樂器為主的傳統的雅樂,缺乏創造,遠離生活,被社會冷遇。以管弦樂器為主的西域樂舞則風糜長安。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善于擊打羯鼓的高手。唐長安城的樂府伶工也多出于西域的音樂世家。如以善弄婆羅門見稱的米國人米嘉榮家族,以琵琶聞名的曹國人曹保家族,其家族子弟在長安樂府,幾乎與李唐一代共始終。當時,風靡長安的樂舞有軟舞、健舞之分。健舞尤以胡騰、胡旋、拓枝最為盛行。開元之際,西域諸國到長安城,為唐朝朝廷多獻胡旋女。唐玄宗深好此舞,楊貴妃、安祿山都能跳胡旋舞。白居易在《胡旋女》詩中說:“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描寫了精妙絕倫、出神入化的樂舞表演。自波斯傳入的打馬球,更是在長安皇室貴族、御林禁軍中大為盛行。
大唐對外域文化兼容并蓄,可見其博大容納、開放自信的精神。唐朝的樂舞氣勢磅薄,場面壯觀,集詩、詞、歌,賦予吹奏彈唱,融合了鐘、鼓、琴、瑟于輕歌曼舞中。樂曲高亢,動作舒暢,服飾華麗,是盛唐時期的歌舞升平、國泰民安的真實寫照。
在長安專門設置了各種樂舞機構,如教坊、梨園、宜春院、太常寺等,其中的樂工、歌舞藝人達數萬人之多。士大夫和豪富之家還有很多能歌善舞的官伎、舞伎。這些人中集聚著大批的優秀藝術人才,他們以自己的聰慧和辛勞獻身于藝術創造,將樂舞藝術推向高峰。唐朝有《破陣樂》,是歌頌唐太宗李世民的武功的。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命呂才等人創作,由一百二十人披甲執戟表演。這是表現戰陣的樂舞,音樂粗獷雄壯。伴奏的樂器以大鼓為主。表演時聲勢浩大,《舊唐書》中稱其“發揚蹈厲,聲韻慷慨”。
唐朝的樂舞經過漢朝百戲在舞蹈技巧上的飛躍和推動下,達到一個更趨成熟的新境界,此時,是樂舞藝術發展的最高峰。唐朝人把樂舞看成抒情和展示才華、表示禮節的手段,是能文能武、能歌善舞的文化素養的展示。
從漢唐時期長安樂舞百戲的發展來看,不僅是民間樂舞百戲繁榮發展的成果,而且也是社會開放、經濟繁榮的結果。漢唐時期長安城里的廣大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增長的,而當時樂舞和百戲的繁榮則正好滿足了人民群眾的這種精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