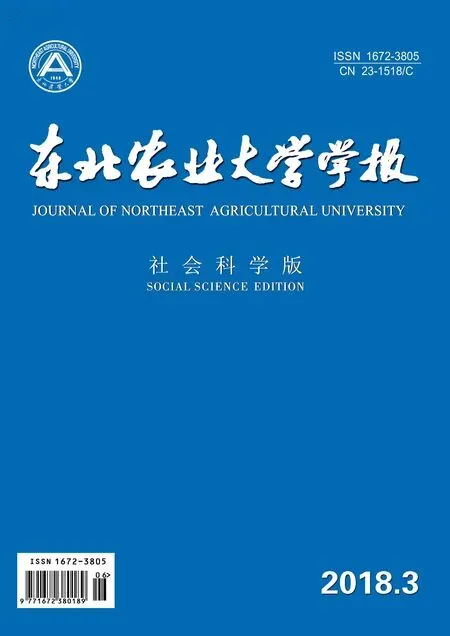唐五代馬匹價格考
丁君濤
(湖北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唐五代馬匹貿易特別是唐與回鶻絹馬貿易,學界研究較多,但唐五代馬匹價格研究成果較少。李德龍《敦煌遺書S.8444號研究——兼論唐末回鶻與唐的朝貢貿易》一文從出土敦煌遺書分析馬匹價格,認為就文書而言,一匹馬可易絹約23.75匹[1]。以往每馬40絹是朝庭為報回鶻助戰之功特許的“贈予”性價格,此定價給回鶻帶來巨大經濟利益,也給朝庭造成沉重財政負擔。劉正江《回鶻與唐的馬絹貿易及其實質》認為,唐與回鶻間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回鶻成為主要馬匹供應方,但馬匹價格明顯高于市場價,嚴重背離商品價值規律,唐王朝與回鶻馬匹貿易主要出于政治考量[2]。馬俊民《唐與回紇的絹馬貿易——唐代馬價絹新探》認為,唐與回鶻絹馬貿易是帶有政治色彩的公平貿易,就價格而言,一方面回鶻馬匹價格相比突厥差別不大,并未特意提價;另一方面,回鶻遠居烏特勤山北,因路途遙遠,運輸成本增加,馬匹價格自然較高。此外,中唐前后,北方游牧民族馬匹售價并無較大起伏,回鶻亦未乘勢抬價[3]。學者主要探討唐與回鶻官方馬匹貿易價格,但對民間市場馬匹貿易研究有限。孟憲實所著《唐西州馬價考》從出土文獻入手,分析西州市場馬匹價格情況,認為該地馬匹價格在唐代多次上漲。
唐五代時,官方馬匹貿易價格一般高于民間,民間貿易價格多由市場定價,官方貿易還受政治、軍事、慣例等因素影響,民間馬匹價格波動性遠大于官方。不同地域、品種的馬匹,價格差距明顯,西北地區馬匹價格遠低于內地。因此,唐出使回鶻使臣常利用其特殊身份私下販馬。“貞元中,詔以咸安公主降回鶻,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副。前后使回紇者,多私賚繒絮,蕃中市馬回以規利,獨憬一無所市,人嘆美。”可見,即便政府未曾特意提高馬匹價格,西北馬匹的低廉價格也足以吸引使臣參與販賣。至少在貞元年間,中原地區馬匹價格遠高于西北養馬之地,西北地區大量販馬活動可以為證。
一、唐代民間馬匹價格
唐代貞觀年間,監牧擁有大量馬匹,馬匹價格為“一馬一絹”,是秦漢以來少見的低價。當官府擁有大量馬匹,且限制百姓用馬時,民間需求減少,直接拉低馬匹市場價格,同期西北地區馬匹價格亦屬低廉,據唐貞觀年間馬匹買賣契約顯示,馬價不過5匹練。此后隨著唐代監牧不斷衰弱,絲織品大量輸出,馬匹價格有所上漲。
從出土文獻可見,6~8世紀初的一百多年中,吐魯番地區馬匹價格波動不大,普通馬匹一般每匹價值銀錢32~37文,優良馱馬約每匹50文銀錢。隨著中原與西北地區商貿往來日漸密切,馬匹價格逐漸上漲。神龍二年,《唐譯語人何德力代書突騎施首領多亥達干收領馬價抄》中記載馬匹價為“錢貳拾貫肆伯文”,到神龍三年時,“馬一疋騮敦七歲,大練壹拾叁。”[4]即一匹七歲騮敦馬價值十三匹大練[4]。開元二十一年,同樣的騮敦,馬六歲,則值18匹大練,“馬壹疋騮敦六歲,開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練拾捌疋。”[5]《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記載天寶二年馬匹價格則與開元二十一年間差距不大,其文錄如下:
突厥敦(馬壹匹)(次上直大練貳拾匹),次拾捌匹,下拾陸匹次
上直(小練貳拾貳匹),次貳拾匹,下拾捌匹
(草)馬壹匹 次上直大練玖匹 次捌匹 下柒匹[6]
晚唐時期,吐蕃占領敦煌以后,馬匹買賣曾以白銀計價,P.T.1297(3)《購馬契約》中記載馬價為5兩純銀,而BD16099《龍年購馬契》中記載馬價為8兩純銀[7],此為西北出土文獻所載市價。內地也常有馬匹買賣,價格與西北地區關聯密切。
唐代內地馬匹價格從《唐律疏議》中可窺一斑。《唐律疏議》卷六《名例》載:“假將私馬直絹五匹,博取官馬直絹十匹。”《廄庫》:“假有殺馬,直十五疋絹。”[8]可見在《唐律疏議》編撰時期,即高宗永徽二年,馬匹價格約在5到15疋絹之間。同時期西北地區馬匹價格與此相近。可見因唐前期民間馬匹等牲畜充足,對西北地區馬匹需求并不強烈,中原地區與游牧地區馬匹差價不大。唐后期馬匹供應不足,內地馬價遠高于西北地區。
據《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載馬價錄文,不同種類、性別、年齡馬匹價格有別[6]。評判馬匹價格重要標準是質量,良馬價格遠高于駑馬。
就資料分析,西北地區民間馬匹價格在整個唐代呈上漲態勢,從每馬5匹練逐漸增至十余匹練,支付手段多以絹、練等絲織品為主。吐蕃族占領敦煌時期,曾以金銀等貴金屬支付,與該族較多使用金銀有關。“吐蕃時期最主要的貨幣應是黃金,應屬黃金貨幣區域,白銀則是輔助性貨幣”[9]。也有學者認為白銀作用更大,“吐蕃貿易交換中最為重要的媒介物是銀子,銀子行使貨幣的職能”[10]。因此,以白銀買馬在吐蕃占領敦煌期間屬正常貿易行為。從貞觀年間到晚唐時期馬匹價格,出土文獻均有一定記載。以吐蕃占領敦煌時期馬匹交易價格為例,分別為5兩純銀、8兩純銀,平均約為6.5兩,晚唐時期白銀價格很難考證,若以一兩白銀一貫錢計,則過低,與晚唐時期馬匹短缺狀況不符。敦煌文書中略有記載,如P.2049號《后唐同光三年正月沙州凈土寺直歲保護手下諸色入破歷算會牒》載,“麥叁碩,張兵馬使買銀壹量,打碗用”“粟肆碩,張兵馬使買銀壹量,打碗用”[11],銀1兩約需麥3到4碩。
初定兩稅時,粟價較以往昂貴,每斗賣錢100文。《李文公集》卷三《進士策問》第一道言: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①參見商兆奎《唐代農產品價格問題研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8(24)。。學者張超林估算貞元年間粟價為每斗200文②參見張超林.唐代糧價研究,西南師范大學(2003)。。推斷德宗年間折算后粟價格約每斗150錢③學者全漢昇在《唐代的物價變動》中論證兩稅法實行之初,粟價每斗一百文,到貞元年間,粟價升至每斗二百文。結合德宗年間糧食價格發展趨勢折算,此處選取中間值以便計數,不代表實際價格。。據此推算,6.5兩白銀可換粟約19.5到26碩,合錢29.3貫到39貫之間,可換絹十余匹。可見唐代民間馬匹貿易價格逐漸上漲。隨著民間馬匹數量減少,加之與北方少數民族間貿易日益繁榮,馬匹價格漸趨穩定:可易絹10~20匹。
二、五代時期馬匹價格
五代時期,民間市場每匹馬價格不過數匹絹。官方馬匹貿易價格較高,但民間價格遠低于唐代。此時以絹帛計價的馬匹價格低于唐代,很大程度上是因商路受阻,內地絹帛難以運往西北邊疆地區,導致絹帛價值高于以往。西北地區以絹帛為貨幣的情況也發生改變,“唐朝中期,多數地區仍是錢帛兼行,絹帛既是商品,也是貨幣。吐蕃占領敦煌后情況有所改變,在商品交換中,絹帛已不起一般等價物作用,而以糧食和布匹作為價值尺度。”[12]晚唐五代時,敦煌等地買賣馬匹多以糧食計價,與當地農牧業不受商貿影響有關。吐蕃占領敦煌后,遵約不遷徙當地居民,又實行計口授田,故其農牧業可保持不衰[12]。“雖然現在尚難找到一種可以相信為等價物的商品,但這種等價物在當時當地可能為小麥。”[13]可見,以糧食計算晚唐五代時期敦煌區域馬匹價格較為合適。
五代時期絹價和糧價對馬匹價格有重要影響,不同等價物的對應價格有所不同。五代時期民間馬匹貿易文書相對較少,從敦煌藏經洞文書可見,價格較唐代有所上漲。P.3257《后晉開運二年(945)十二月河西歸義軍左馬步押衙王文通牒及有關文書》記索佛奴“其叔進君賊中偷馬兩匹,忽遇至府,官中納馬壹匹,當時恩賜馬價,得麥粟壹拾碩,立機緤伍匹,官布伍匹。”[14]其中立機緤和官布統一折算成糧食,立機緤是晚唐五代敦煌普遍使用的一種棉布,每匹緤長度在24到25尺之間,敦煌文書中并無立機緤具體價格,只能以其他文書中價格換算。P.3051《丙辰年(956)僧法寶貸絹契》、P.3627《壬寅年(942)龍缽略貸絹契》、P.2453《辛丑年(941)十月二十五日賈彥昌貸生絹契》等記載借貸1匹生絹利息為1匹立機緤,P.2504《辛亥年(951)康幸全貸生絹契》載:“貸白絲生絹壹疋,長叁丈玖尺,幅寬壹尺玖寸。其絹利利頭鎶鑑壹個”[14],至于鎶鑑價格,據S.2899號文書記載為“粟肆碩伍斗”,P.3501《戊午年(958)康員進貸生絹契》載“其絹斷償利頭,見還麥肆碩”,即借貸生絹1匹利息是麥4碩[14]。因此若借貸周期一致,立機緤價值可能約麥4碩。至于官布價值則很難判斷。據敦煌文書P.2912《丑年正月已后入破歷稿》記載:“教授送路布十五匹,準麥六十七石五斗。都頭分付慈燈布十匹,準麥四十五石。與宋國寧布兩匹,[準]麥九石,都計一百廿一石五斗。□齋亻親布一匹四石五斗,□□藏□齋亻親布一匹四石二斗。□眾亻親布……石九斗。布一匹四石二斗。”[11]賬中除兩匹以4.2石出售外,其余皆以4.5石出售,可知官布價值在麥4.5石左右,因此后晉開運二年的馬匹價格約為52.5石麥。P.2504《年代未詳(十世紀)龍勒鄉百姓曹富盈牒》所載馬匹價格為2匹生絹,其文書中記載“內一疋斷麥粟廿七石”,因此2匹生絹為54石,馬匹價格為麥粟54石。
五代時期馬匹價格在54石麥左右,唐代馬匹價格若以絹計則高于五代時期,若以糧食計則低于五代時期。唐代糧食價格波動較大,天寶五載(746),“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十三錢,絹一匹錢二百。”[15]以此價格計算,一匹突厥馬在24.6~30石米之間,而米價要高于麥價,據陸贄《請減京東水運收腳于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記載:“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16]高啟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中,認為“一斗麥約等于1.44斗粟”[17]。因此,唐代馬匹價格折合成麥約為28.4~34.7石,若以糧食計算,唐代馬匹價格低于五代時期。
馬匹價格昂貴或與五代時期軍事形勢有關,此時戰爭頻繁,官府多次在民間征用馬匹,直接妨害養馬業發展。僖宗時期,因鎮壓農民起義,官吏積極補充馬匹數量,增強軍事力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15]。晚唐時期,隨意掠奪民間馬匹現象時有發生。到五代時,北方戰爭頻發,又多在適宜養馬之地,官府飼養馬匹數量不足,就經常下令掠奪民間馬匹,本已衰落的養馬業再受摧殘。《五代會要》載:“梁開平四年(910)十月,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晉天福九年(944)正月,發使于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馬。”[18]官方奪馬括馬行為直接傷害民間養馬熱情,導致民間市場馬匹數量嚴重不足。同時西北作為重要馬匹來源地,因軍事沖突較頻繁,畜牧業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此外,五代官府為增強軍事力量,有意提高官方購買價格,以吸引少數民族販馬,同時直接推高馬匹市場價格。同時期,絲綢商路受損,北方馬匹更難輸入,回鶻馬匹價格遠低于黨項等地,但甘州回鶻等在運馬途中常被其他少數民族劫掠,廉價馬匹供應受阻,自然導致五代時期馬匹價格上漲。
唐五代西北地區馬匹價格經歷較大起伏,與中原馬政管理、游牧地區軍事安全、商路通暢程度等有密切關系,前期馬匹價格穩定且低廉,很大程度因內地馬匹充足且商路暢通,西北地區馬匹市場供應能夠滿足需求,此后價格則不斷上漲,據孟憲實所著《唐西州馬價考》,認為西州馬價以銅錢計,從高宗至天寶時期初處于上漲階段[20]。至晚唐五代時期,馬匹需求量越來越大,而供應卻越來越少,自然不斷上漲。見表1。

表1 唐五代民間馬匹價格
三、唐五代官方馬匹價格
唐五代時期,官方和民間馬匹價格存在一定差別,中原在與周邊少數民族,特別是北方實力強大少數民族互市貿易時,馬匹價格一般高于市場價格,但會有所變化。當回鶻漸趨衰弱,政治、軍事影響力下降,且唐朝廷馬匹緊缺程度有所緩解時,每匹馬價格低于40絹。李德龍《敦煌遺書S8444號研究——兼論唐末回鶻與唐的朝貢貿易》一文通過出土文獻中價格對比,認為回鶻在894年至904年間向唐朝進貢馬匹,朝廷給予每匹馬約23.75匹絹回賜,遠低于40匹絹。894年至904年間,唐與回鶻均處衰弱時期,唐無力亦無心羈縻回鶻,回鶻對吐蕃牽制力大減,馬匹貿易在唐與回鶻關系中作用下降,因此價格下浮。可見唐代官方貿易中,馬匹價格并非一成不變,受馬匹需求程度、少數民族政權對朝廷重要性、馬匹質量等因素影響。同時邊境地區軍隊、驛站在民間市場購馬仍采用市場價,當與少數民族馬匹互市價格遠高于市場價時,朝廷會意識到其中問題(意識到問題后或調整價格,如未調整,即不受民間制約),因此受政治限定的官方馬匹價格仍受民間馬匹市場制約。
唐五代中原與回鶻、突厥等民族馬匹貿易持續時間很長,朝廷以各種形式購買大量馬匹。學界普遍認為,唐代官方互市馬匹價格約為40絹,特別是與回鶻互市馬匹價格較固定。實際馬匹價格與貿易形式、時間、民族均有密切關系,不同情況下,馬匹價格亦有調整。當中原馬匹極緊缺時,價格自然上漲,面對實力弱小的少數民族,交易價格則有所下降。此外,出土文獻記載西北軍府、驛站等機構在當地所購馬匹價格低于40絹,可見西北當地價格更接近市場價,少數民族從中獲利不多。本文討論官方馬匹價格是指中央朝廷與少數民族大規模朝貢貿易、互市貿易時的價格。
隋朝與少數民族也有密切的馬匹貿易,對少數民族給予貿易優待,造成財政壓力。楊勝敏認為,“在隋代,公元610年,一匹馬交換價值為十萬幣,這樣算,一匹馬等于一百匹絹。”[21]以此高價買馬非常少見。當時河北地區適宜養馬,“冀州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22]李淵起事前,竇建德等“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即以重金求取突厥馬匹[23];遠在洛陽的王世充為補充馬匹,把宗女嫁給突厥可汗,與突厥互市溝通購馬渠道[24]。李淵及謀士裴寂、劉文靜等也知欲起事成功,須獲足夠馬匹,“今士眾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需”[23],但當始畢可汗派康鞘利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時,李淵意識到高價向突厥購馬會后患無窮,“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貰之,不足為汝費”[24],于是“擇其善者,止市其半”。唐王朝與少數民族之間官方馬匹貿易并不依賴市場,少數民族多利用交易機會,在中原急需馬匹時抬高馬價。
唐朝與強大少數民族的官方互市中,馬匹價格變化并不明顯。開元年間與突厥互市,曾涉及支付絹帛問題。開元二十三年,唐在與突厥互市時,發現突厥違背舊例,“一年再市”“納馬多倍”,總數達14 000匹,玄宗為維護與突厥關系,特意多留,“十退其二”,付物50萬匹。十退其二,購馬數量約為11 200匹,以50萬匹總價計算,每匹馬約為44.6匹。唐與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時,每年支付絹數10萬匹,“仍許于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每年赍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開元二十三年兩次互市,共購馬11 200匹,可見互市馬匹數量可達5 600匹左右,以每馬44.6匹絹計算,為24萬余匹絹,與“每年赍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吻合。可見唐代與突厥互市貿易,每匹馬價格約40余匹絹。
唐與回鶻絹馬貿易交易量遠超突厥。《舊唐書·回紇傳》載:“自乾元之后,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40匹,動至數萬馬。”可知唐與回鶻絹馬貿易,每馬約40匹絹。《全唐文》中《與回鶻可汗書》明文記載唐與回鶻絹馬貿易情況:
達覽將軍等至,省表,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匹,都計馬價絹五十萬匹。緣近歲以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不免闕供,今數內且方園支二十五萬匹,分付達覽將軍,便令歸國,仍遣中使送至界首。雖都數未得盡足,然來使且免稽留,貴副所須,當悉此意。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納馬多,則此力致歉,馬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約,彼此為便,理甚昭然[25]。
唐在此次絹馬貿易中計需支付50萬匹絹,實際僅支付絹帛25萬匹。至于此次買馬數量,學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6 500匹,也有認為2萬匹,還有學者認為是1萬匹。以50萬匹絹總價計算,6 500匹馬,則單價為76.9匹絹,2萬匹馬,則單價為25匹絹,與40絹官價差距過大,可信度不高。馬俊民在《唐與回紇的絹馬貿易——唐代馬價絹新探》中認為,“二萬匹”或為“一萬匹”之訛,如為1萬匹,則每馬價格為50匹絹,與元和四年白居易所做《陰山道》一詩中所舉實例“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吻合[3]。元和三年絹馬貿易原本約定買馬數量為6 500匹,“頃者所約馬數”可為印證,但回鶻并未遵守約定,后文才有“宜有定約,彼此為便,理甚昭然”,要求其信守約定。回鶻前往互市馬匹數量遠多于此,唐最終印納1萬匹。“印納”即接收,唐與少數民族馬匹貿易時,一般在馬匹上打上官印表明購入,對不同民族馬匹用不同印。胡三省說:“所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國互市,中國以印印之也。”[24]
總之,唐代在與少數民族官方馬匹貿易價格一般不低于市場價,反映唐代羈縻思想及其少數民族政策。許多邊境將軍因此在邊境高價購馬,以壯大軍隊實力,“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至于唐以高價獲得多少馬匹,史料并無統計,僅與回鶻互市馬匹貿易數量就已十分驚人。據推測,回鶻賣馬數量或在140萬匹以上,用絹5 800余萬匹以上,如加之朝貢貿易及其他少數民族馬匹貿易,數目更加龐大。購馬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使唐與回鶻之間馬匹貿易廣受爭議。
五代時期,因中原地區長期戰亂,養馬戶常被政府無償征馬或低價購馬,民間馬匹市場嚴重萎縮,官方養馬機構又無力滿足中原王朝馬匹需求。后梁明宗時期,宰相奏報:“黨項之眾競赴都下賣馬,常賜食禁廷,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凡將到馬無駑良,并云上進國家,雖約價以給之,而計其館給賜賚,不啻倍價,耗蠹國用,請止之。”而明宗認為“國家常苦馬不足,今番官自來中國,錫賜乃朝廷常事,不足言費”[26]。可見此時朝庭是因缺馬而欲購馬。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遠不及唐代軍隊養馬規模。五代時期政府控制馬匹數量最多不過十幾萬匹,后唐長興四年為馬匹數量最多階段,朝廷馬匹約有5萬[19],如計全國總數,或為十幾萬匹,較唐代監牧動輒數十萬匹相去甚遠。唐代官方監牧馬匹數量達到兩次高峰,一是自唐太宗至高宗時期,“用太仆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二是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即便晚唐時,各地藩鎮馬匹總數亦遠超五代時期,據《舊唐書·地理志》統計,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九個節度使擁有戰馬數量高達135 550匹。因此,五代馬匹緊缺程度遠超唐代,使得此時期馬匹價格亦遠高于唐代。“(長興)三年正月,三司奏,從去年正月至年終,收到諸番所賣馬,計六千馀匹,所支價錢及給賜供費約數四十萬貫。”[27]以40萬貫總價計算,每匹馬約為66.6貫,遠高于唐代40匹絹價值。五代時期馬匹貿易耗資巨大,明宗天成年間,每年買馬耗費需50~60萬貫,直到財力難以承受,而降至40萬貫。
分析可見,中唐以前,唐政府馬匹儲備充足,監牧可為軍隊、驛站提供大量馬匹,“方其時,天下以一絹易一馬。”但此時期,唐在與周邊實力強大少數民族馬匹貿易中予其一定優惠,馬匹價格高于市場價格,但購買數量被嚴格控制,財政支出尚可承受,目的在于安撫少數民族,并非獲得馬匹。到晚唐五代時期,監牧受到沖擊,加之戰爭頻發,馬匹嚴重緊缺,購馬價格上升。同時,與少數民族馬匹貿易時,羈縻色彩明顯淡化,市場作用日漸顯現,“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28],貿易基本接近市場價格,已無中唐以前明顯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