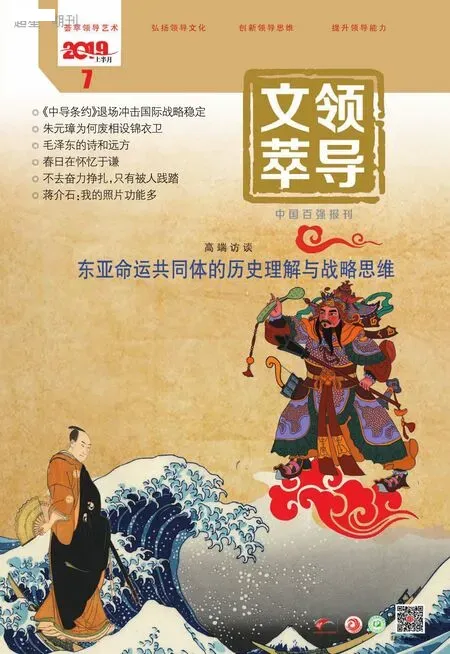周恩來和他喜愛的6種花
游綜編
梅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在我國古代,文人雅士們將傲雪斗霜的梅、松、竹并稱為“歲寒三友”。
周恩來從小就喜歡梅。1904年,才6歲的周恩來和他的兩個弟弟要隨父母從淮安城遷去清江浦外婆家萬公館居住。那是一個冬天,剛好周家院內有一盆臘梅已蓄蕾待放。周恩來舍不得這盆美麗的臘梅,一心想把它帶走。他當時幼小,搬不動這個盆栽,于是便將花從盆中取出,敲掉花根上的泥土,然后將這株臘梅帶上小木船,捧到萬公館,親手栽到萬家塾館一側的院子里。一個多世紀以來,這株臘梅長得枝繁葉茂,年年噴香吐艷。為此,當地一家煙廠特意以這株梅的照片作為商標生產出“一品梅”系列香煙,寓意周恩來官至一品,高風亮節也是一品。
吊蘭
忍犯冰霜欺竹柏,肯同雪月吊蘭蓀
周恩來在上海領導秘密斗爭時,曾提出凡是中共機關或是主要領導人的住地都要在窗口放上或吊上一盆吊蘭,遇有緊急情況時,首先要將花盆推落窗前,以便向不知情的同志報警,避免更大損失。
1942年6月底,周恩來因操勞過度致使疝氣發作,不得不住進重慶歌樂山龍洞灣中央醫院動手術。他的管床護士特意從家中帶來一盆長得很旺盛的吊蘭,然后用醫用膠布貼吊在周恩來的病房窗前,為病房平添了幾分生機,也令周恩來賞心悅目。
周恩來的手術很順利,手術4天后他即能下床走動,到7月12日,再有三天就可以出院了。這時,由于歷時十幾天后用來貼吊吊蘭的醫用膠布失去黏性,那盆吊蘭突然墜地摔碎。周恩來見狀心中暗暗吃驚。但他畢竟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會平白無故地往壞事上想,而是高興地寫下兩句詩:“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但是,就在那天下午,送《新華日報》的報童在給他送報時,順口說:“倉庫老太爺因打擺子死了,現在正忙后事。”周恩來的父親周劭綱先生當時在重慶為《新華日報》設在下土灣的倉庫做管理員,小報童既不知道老人與周恩來的關系,更不明白當時南方局領導向生病住院的周恩來隱瞞了實情。一聽報童的話,周恩來頓時警覺起來,便估計到可能是自己父親出事,同志們正瞞著他。于是,他立即決定提前出院,回紅巖山上。吊蘭的摔碎和周恩來父親去世當然只是巧合,并無因果關系,但是,對于重孝道的周恩來來說,帶給他的仍然是極大的傷痛。此后,就很少見到他生活和工作的場所有吊蘭出現了。
蓮
蜻蜓點水紅菱醉,菡萏馨香白鷺陪
周恩來的故鄉淮安是個著名的“水城”。當時,城區內有月湖、勺湖、蕭湖、桃花垠等水系,城區約五分之三的面積都是水面,到處都長有菱角、蓮荷、蒲草等水生植物。周恩來喜歡蓮花緣于宋代大哲學家周敦頤寫下的《愛蓮說》。據《周氏宗室大典》載,周恩來系周敦頤的38代裔孫。周恩來5歲入家塾館讀書時,塾師不僅向他們講授孔孟之道,還把《愛蓮說》懸掛于書房中堂上,讓孩子們天天看,天天讀。《愛蓮說》中有一名句“出淤泥而不染”,這正是周恩來看重的人品道德。因此,他常以荷花的性格激勵自己和教育部下。
櫻
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枝便當游
1917年,周恩來從南開學校畢業后東渡日本。次年春,當他見到盛開的櫻花時,為櫻花的美麗燦爛而贊嘆。他在詩作《雨中嵐山》中寫道:“雨中二次游嵐山,兩岸蒼松,夾著幾株櫻。到盡處突見一山高,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瀟瀟雨,霧濛濃;一線陽光穿云出,愈見姣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借櫻花抒發自己的胸臆。
這首詩不僅表露了周恩來對櫻花的喜愛,更是抒發了對自己在日本尋找到救國真理的喜悅。后來在他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曾對日本來訪的朋友們說:“當年我離開日本回國時正是櫻花盛開的季節。我也想在櫻花盛開的時候再去訪問日本。”令人遺憾的是,周恩來的這一美好愿望一直未能實現。1972年,周恩來與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共同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兩國關系的正常化。當時,周恩來向日本贈送了一對大熊貓;田中角榮向中國贈送了1000株大山櫻。
1979年周恩來逝世三年后,田中角榮又向中國贈送了1000株櫻樹,分別栽植于江蘇淮安、浙江紹興、南京的梅園和天津的南開等留有周恩來足跡的地方,這一以櫻花傳遞中日友好的做法還延展到日本民間。
海棠
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空蒙月轉廊
周恩來非常喜歡海棠花。據周恩來的侄孫周國鎮介紹,周恩來在新生的人民政權建立時,為什么要選擇中南海西花廳做自己生活和辦公的寓所呢?就是因為他看到了西花廳院子里有那么多海棠花和那座“不染亭”。
1954年,為實現印度支那和朝鮮半島的和平,日內瓦會議召開,那是新中國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國際會議的舞臺,周恩來以外交部部長的身份親自率團參加。
由于美國當時采取完全敵視中國的政策,因此,壓根兒就不希望會議有任何成果。在美國的阻撓下,會議前后開了40多天。就在周恩來在日內瓦的會內會外廣交朋友、多方協調溝通努力工作時,國內中南海西花廳院子里的海棠開花了。在家的鄧穎超見花思人,就剪下碩大的一朵花,放進一本厚書里壓好,然后連同上年采自北京香山的一片紅葉一起裝進一只信封,只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上“紅葉一片,寄上想念”,然后托前往日內瓦的工作人員捎給周恩來。
1988年4月,當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的海棠花又一次盛開時,鄧穎超又一次見花思人,深情地寫下《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鄧穎超稱自己的這一篇文章既不是詩,也不是散文,而是“一篇紀念戰友、伴侶的偶作和隨想”。
“春天到了,百花競放,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走了12年了,離開了我們,他不再回來了。
你不是喜愛海棠花嗎?解放初年你偶然看到這個海棠花盛開的院落,就愛上了海棠花,也就愛上了這個院落,選定這個院落,到這個盛開著海棠花的院落來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還長,到現在已經是38年了……”
今天,我們再讀鄧穎超的作品,讀出的依然是滿滿的懷念。
水仙
不懼淤泥侵皓素,全憑風露發幽妍
西花廳的花匠很會養水仙,每到冬天,無論是周恩來開會或是會客,都會有盛開的水仙花到場伴隨。周恩來的辦公桌上也會放上一兩盆水仙,使他的辦公室內花香四溢,生機盎然。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14日,他的骨灰盒被放置于勞動人民文化宮接受各界人士吊唁,儀式結束后,骨灰盒轉至人民大會堂,并按周恩來生前愿望放置于臺灣廳內度過最后一夜。當時在臺灣廳內,伴隨周恩來靈骨的還有骨灰盒周圍的6盆水仙花。那翠綠的葉、潔白的花、黃色的蕊,正象征著周恩來人品的高潔。
“那印象太深刻了!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周恩來的衛士韓福裕曾這樣形容當時的情景。打那以后,他年年都早早地養水仙,并通過請教西花廳的花匠,學習養花技術,從而確保自己養的水仙在每年的1月8號周恩來祭日開花,然后陳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以示對一代偉人的悼念。
(摘自《時代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