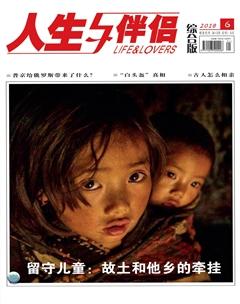海伯伯
木心
海伯伯在我家的地位頗為特殊,母親稱他“海哥”,傭人稱他“海爺”“海老爺”,姑丈舅父來時,叫他“阿海”。一日三餐,他坐在男仆們的桌上,是上方首席。
海伯伯似乎是我家的總管,卻不盡然,至少缺乏總管的威嚴架勢,精明指揮的才干。海伯伯是誰也不怕他的,廚娘忙不過來了,求他幫忙殺十只雞,他便一只一只地殺。袖手旁觀者還涼涼地插一句:
“海爺大材小用了。”
他似乎沒有聽見,殺完了,倒去問廚娘:
“那你來得及推毛嗎?”
推毛者就是先把雞浸在熱水里,透了,就可將雞毛拔凈。
海伯伯殺雞,無疑是大材小用。他一身好武藝,先天體質極佳,山里人,原是廟里的小沙彌,確鑿受過老和尚的指點,練過一番內外軟硬功夫。常道是“半路出家”,他卻是半路還俗,十八歲逃出山門,十九歲入贅成親。這段往事,最好少提,海伯伯除了教人拳腳時會拉扯到當年練擺式的經驗,平日里一貫武人文打扮,衣履雅潔,一卷在手。有時還考考我:
“井字當中加一點,什么字?”
我不識,他便道:
“那是咚,一塊石頭丟在井里,便是咚。”
此其一。還有許許多多怪字,不知從何搜來。黃昏的燈下,男仆們圍滿桌邊,看海爺寫一個,講一陣,從瞠目不解到悅然大悟是這樣的警捷,他們快樂非凡,認為海爺著實是滿肚皮的才學,不比舉人老先生差多少,舉人老先生有多少分量他們是不知道的,他們喜歡比,這一比,真痛快!
……
海伯伯,真姓真名是鄭阿海,一望而知是個俗人。在我誕生之前他是我家的成員。我們這種規范森嚴的舊家,除了鏡子、燈,是亮的,其他全是暗沉沉的。希臘的是青年文化,甚至是少年文化,歐洲是中年文化,惟有中國一貫千年是老年文化。家中的寬床、長桌、大椅,都特別高,適合于身材特別魁梧的人用的,似乎不是三代五代傳下來,而是開辟混沌之后,就各自黑黓黓地呆蹲到今天。除了鏡子、燈,第三便是海伯伯是亮的。不必恭維,他沒有學問,即使端午節喝了雄黃燒酒后,海伯伯詩興大發,白壁題詩,一首七絕,至少有三處不妥不通,母親聞人傳笑,便悠悠道:
“你的海伯伯又在賣弄他的薛蟠體了。”
我自然明白薛蟠體是什么等級,為海伯伯擔愧承羞,詩也實在要不得,那回廊的墻面白堊剝落,字又歪斜無書卷氣,真丟人,想個什么法子把那丑跡掩蓋掉。卻見海伯伯提了一桶石灰漿來,他說:
“本來該去舊換新了,這就統統粉刷一遍。”
翌日清早,他又把隔夜刷過的壁面,連陳年起殼的泥層統統敲落,噴濕墻磚,黃沙水泥低筋拌和了,括糙打底,二道是細沙石灰抹平,初夏薰風,干得也快,不出三天,回廊白壁煥然一新,映著搖曳的竹影,整座邸宅中,是這一帶最雅潔宜人了。母親走過,又加按語:
“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題壞了詩,將功贖罪呢。”
海伯伯決非無能之輩,他的真才實學是武功和手藝。
父親在世之日,他是隨從的鏢師,餐桌上的座位是在父親的左邊第一席,他小于父親三歲,父親當眾稱他“海弟”“我海弟”。平日兩人閑話則“小海”“海喔”“阿海”“海”,不一而足。他解過父親的危,救過父親的命,我兒時即使看慣父親和海伯伯的親密無間的情態,也常奇怪自己和表兄弟之間怎么不能也是如此這般呢,所以時時會發呆地看父親和海伯伯這種一個眼色一個動作便默契得出神入化的趣劇。父親要出門辦事,走到庭心,一頓,海伯伯奔上樓去向母親取了大衣。父親看細字更換一副眼鏡,失手跌碎了鏡片,海伯伯從左胸袋里掏出一副新的,父親隨即戴上,看完文件,逗趣道:
“再跌碎了呢?”
海伯伯從右胸袋里又掏出一副,那驗光的訂單也帶出了袋外。
“單子在你這里?”父親說。
“我有用,當然歸我。”
父親赴宴,必與海伯伯同行,入席亦習慣于二人并坐。老式款待法的“布菜”“敬菜”是主人家將每道肴品的精華部分用特備的筋匙取了送到客人酒盞前的一個中型碟子里,往往堆成一座小山,父親不動它,當海伯伯快要罷箸退席時,父親說:
“海弟,幫幫我,恭敬不如從命,主人家的美意,代我領了。”笑著把碟子移到海伯伯的面前—武人的食量大于文人何止一倍,此時此地,海伯伯當然只好以半飽為度,于是一個純粹精華之物的小山,聊作補充,良有以也—我們孩子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覺得父親和海伯伯其實也是孩子,比我們會想辦法會說話而已,我很羨慕,癡癡地想:大家都像他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