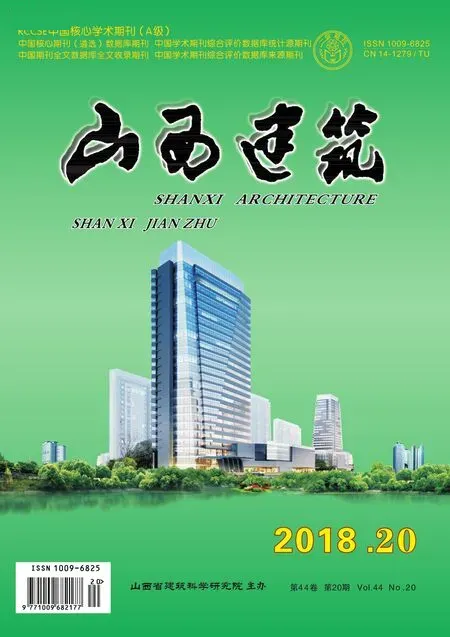實體書店空間的現代性重構
劉 練
(華南理工大學,廣東 廣州 510641)
0 引言
很多人質疑現代化其實就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模式的普遍化,近代科學也將現代化描述為通過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城市革命等變革生成現代社會的過程。“現代性”(modernity)作為這一發展過程中的衍生詞,比現代化更能深入解釋與描述瞬息萬變的當今社會,“被定義為在此過程中對當下的體驗及質疑”[1]。
在這一過程中,實體書店在與城市地租、網絡書店、生活模式等的博弈中不斷解體與重構。從舊式書店到書店+,從物質需求到精神享受,從單一空間到多元空間,書店空間的重構體現了現代性在人類精神文化與消費觀念中的影響,但這種改變卻是非連續性的、斷裂的。
1 何為現代性
現代性并不像字面意義上簡單地以時間線為基礎的社會歷史進程,而是多時空、多學科的雜糅并序,自提出之初就具有多重含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近代研究中“簡單”“線性”的現代性也逐漸被“多元”“全球”的現代性所取代,歐洲中心主義的現代性在多元社會的沖突下已經成為不同民族、階級、地域文化撞擊下的產物。現代性的成功之處在于以時間尺度為基點,通過不斷的打碎與重組實現對空間的再生產,從而超越了歷史階段的永恒性。
根據夏爾·海德萊爾的描述,現代性的特征為:當下的、新的、短暫的、轉瞬即逝的、偶然的,每個當下的相較之前的都是最新的,但也是轉瞬即逝的,不可預計的。一方面隨著都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精神信仰不斷消解,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固有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但另一方面信息化與科技的發展也不斷的形成新的枷鎖。現代性在前進的同時,也在不斷的回歸固有的歷史渦輪中,不斷重現原始與支離破碎,即螺旋上升。不同于現代主義,現代性并不注現象本身的描述,而是注重批判與自我批判與自我反思的過程,并且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現代主義之于現代性正如火車之于旅行,妓院之于愛情。
2 書店+中的現代性
實體書店空間是整個城市乃至社會的微觀影像,書店變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現代性之于社會的影響。盡管世界范圍內的圖書總銷售量呈上升趨勢,但在城市空間的擠壓與網上書店的沖擊下,傳統書店被邊緣化,生存面臨困境,越來越多的傳統書店瀕臨倒閉但卻不愿舍棄實體書店的固有優勢。面對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傳統書店不得不謀求新的發展機遇,倡導多種業態的跨界整合,由單純的賣書場變為多元模式共生的體驗空間——書店+。
書店+空間模式的形成是現代社會空間之于現代性最為典型的表現之一。工業化、信息化所建構的文化與生活空間使消費理念與生活品味逐漸提升,傳統的實體書店功能空間單一,購物體驗差,不符合技術文明與信息革命的當下要求,只能被“煙消云散”。當整個世界逐漸被資本主義與享樂主義侵蝕,人們更加注重精神層面的需求,要想成為現代性,必須不斷創新,尋求突變。實體書店只有不斷的打碎與重組原有的消費空間、文化空間、交往空間,才能夠維持“新”,在困境中謀求發展。因此,實體書店中不斷注入咖啡、閱讀、展覽、沙龍等新鮮血液,以符合現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商品經濟和理性主義使整個社會結構都產生了重大的變革,在生理需求已經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加注重精神享樂,城市公園、展覽館、博物館、電影院等生機勃勃。城市空間不斷重構,城市地租也日益提高,信息技術革命使網上購物迅猛發展,為應對此危機,原有的商場空間除了提供單純的購物需求外,也提供家庭娛樂、餐飲、休憩等空間,更加注重人性化服務。同樣,亞馬遜、當當、京東等網上書店的興起使單純的以賣書為單一營銷模式的書店受到沖擊是不可避免的,杭州“光合作用”關門停業、北京人文學術書店倒閉等似乎向我們宣示不求變只能滅亡。在這種囧境中,實體書店必須適應現代性中的世俗運動,以現代的社會空間和精神需求去尋求新的發展模式,因此書店+應時而生。書店+經營模式多樣,注重客戶體驗,為實體書店生存提供契機,廣州方所(如圖1所示)、臺灣的誠品書店(如圖2所示)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證。

現代性在被普遍化的同時也逐漸的被“模塊化”。現代性已經滲透到每一種現象、每一個行為之中,所有人都在現代性的浪潮中掙扎,從建筑設計中的工業化生產到我們按部就班、日復一日的生活方式,每個人在被現代性的同時也被“模塊化”。同樣,書店+模式的成功,使其被認為是最符合人們情感需求與城市形象的產物,被無限的復制,并且被視之為放在四海之內皆宜生存的經營模式。
3 現代性中的矛盾性
盡管空間的重構為實體書店提供新的發展契機,受到廣大消費者的喜愛,但這究竟是“詩意的棲居”還是“技術的棲居”,面對商品經濟與信息革命的沖擊實體書店的確需要謀求新的發展機遇,但通過簡單的科學技術手段打造的精品書店微空間究竟是閱讀空間還是休息享樂的場所,書究竟是店面的主題要素還是咖啡的襯托。
現代性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對于社會現象的及時應對,同時它又是純粹的、獨立的,在尋求自我的發展,因而現代性本身就具有斷裂的、矛盾的。書店的設計應當在邏輯化的過程中去協調應對這兩種問題,而不是一味的妥協應對,為了生存而生存。
現代性雖然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是簡單的模數化生產過程,若想成為現代的,就要成為個性的、個人的,而不是現在的千城一貌。當然,個性并非意味著像福祿壽酒店、五糧液集團總部大樓一樣“奇奇怪怪”,而是在滿足現代化的基礎上突出自己的個性。自從誠品書店、方所的模式取得成功之后,很多傳統書店紛紛效仿,河北保定的新華書店設計甚至獲得了今年德國紅點獎的至尊獎,內部空間的性冷淡、枯山水、日式禪正式吸引廣大消費者的地方。但是當將新華書店與蔦屋、誠品放在一起時我們是否還能識別哪個才是我們童年經常光顧的場所。現代化、全球化的確需要我們在流變、嘈雜的環境中兼容并蓄,不斷創造,但多元、普遍是讓我們在能夠保持獨善其身、理性的前提下自由的重構自己。既然當初我們選擇了不要盲目的繼承傳統,現在也應該理性分析現代性所蘊含的矛盾與張力,不要被現代主義的既定教條框住。在實體書店的現代性重構中,不要的一味屈從于市場、屈從商品經濟下的那種趨炎附勢的操作,但也不能夠回避現代化社會所帶來的變革,固守傳統的空間模式,而是應該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在時代價值和永恒價值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4 結語
從單純的賣場空間到書店+空間的建構,體現了現代性在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文化中的巨大力量。書店+空間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建構出來,并在現代性的不斷反思與自我批判的過程中日趨完善。這種重構的過程,既是城市文化與城市空間的微觀影像,又在當下環境的影響下根據經驗與客觀現象的自我重組。所以實體書店的發展歷程是矛盾的、復雜的、斷裂的,社會階級、社會文化、社會精神的變革在書店空間重構過程中被不斷映射。在將來的發展中,書店中的消費者與消費者、消費者與書店空間、消費者與社會之間進一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不斷促進書店空間的消解與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