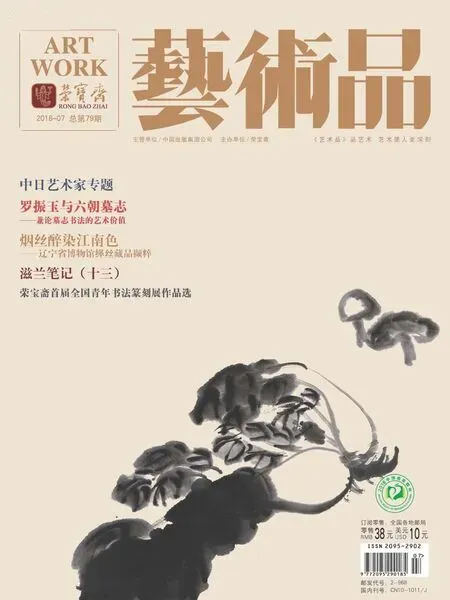藏雜雜說(七)
文/韓天衡


宋銀星眉紋歙平板方硯
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宋代歙硯較端硯為多,地理位置上,安徽較嶺南遠遠地近于北宋政治經濟中心的汴州,和南宋的杭州,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漢代硯多平板,純屬實用之需,而宋人之制平板硯,取上佳石品,多為觀賞,至少是觀賞兼及實用。這是跟宋代君臣乃至士人間推崇尚雅審美觀念,泛及到賞石、賞硯攸關。此硯有多道眉紋。因呼眉紋,故宜橫置,即是雕制施藝之硯,此也慣例。眉紋硯板上,有銀色的星星點點,稱銀星,尤其是當時初出,明潔如黑夜平湖間返照的繁星,有詩境。不過時過千年,倩容未免打折。
2004年,友持硯易字,置案頭多日,興起在硯四側,書隸刻十六字:“眉文道道,風情妖妖,千秋不老,曰黑里娋”。之所以有“黑里娋”之句,私意是文字里留些時代烙印也。
“文革”里買舊書畫、古玩可是千載不遇的好機會,而且機會有的是,看你喜不喜歡,覺悟不覺悟。當然,一不小心也會被扣上“封資修”余逆的帽子。所以得像地下工作者般靜悄悄地躲著玩,蠻緊要的。

唐云書畫、沈覺初刻紫砂壺
世界上有許多極平常的物事,因為文化,尤其是有大文化人的摻和,就產生出極不一般的文化效應。如南方滿山遍野的竹,因為王子猷的“何可一日無此君”,竹,成了文人高風亮節的象征;東坡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而這位先生還是念念于茲,也因此有了添加了文化原素而傳之千秋的“東坡肉”;陶壺原本是生產于宜興的茶具,平常物也,由于陳曼生的雅好,設計壺型,制辭書寫,遂有了文人都競相追逐的“曼生壺”……說到當代,唐云先生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先后收得八件,新取齋號“八壺精舍”。藥翁磊落人,八把壺換著用,這才叫不為藏物所奴,而真地做了它的主子。一日,女傭不慎,敲碎一柄,苦惱到他兩天滴米未進。心痛唄。他公子逸覽兄曾不無高興地對我說:還好,不是我敲的,否則,罵都被罵死了!
藥翁愛壺,也好畫壺,有天,將為他篆刻的“八壺精舍”大章送去,翁開心,問我:白相(玩)壺伐?我說勿白相。翁說:你勿白相?今朝就撥(給)一把你白相相。這小壺周身上下書畫詞塞得滿滿的,壺蓋的空隙處還署有“大石翁自用之壺”的小款。
此乃30年前事矣。我珍藏著,從未泡過茶,就怕有一天,也會苦惱懊悔到滴米不進,我可不想步大石翁的后塵。
許麟廬國畫
許麟廬先生為齊白石門弟,作畫豪放曠達,一如其人。1978年為唐云翁捎物去其府上。先生引我入戶,遞白酒一杯,稱進來者都得先喝一杯。我告因酒精過敏嚴重,滴酒不沾,故得破例過關。時見其畫室的吊繩上己掛著這張別致的新作,款也是預先書寫的,說:天衡,送你的。又側視我良久,蹦出一句話:“天衡不喝酒?沒勁!”


元代青花罐
20年前一次不可忘卻的薄游。那年春天,友人邀我假日里散散心,別老是粘在刀筆里,遂有江南古鎮同里一日之行。其實它離上海也不遠,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著名的退思園外,工藝、雜貨,以及大言不慚自稱古玩店的甚多。逛逛唄,友人陪我踩進間“古玩店”,打量四壁,自頂部而下的隔板上都擱滿瓷器,油光光、锃锃亮,多是新出窯的貨。定睛一窺,竟發現了一件舊器,叫店主取來一看。店主開腔:嘿,儂(上海方言,意為“你”)眼光蠻靈的,這是昨日剛從鄉下收來的。憑我對青花瓷的淺薄知識,認定此件是元代的青花罐,是藏瓷家們可求而不可得的寵物。問他多少錢?回答:所有的都是百元一件,這件二百。我心想這可是天公送我的禮物噢。未及開口,友搶先說:新開店啦,給一百沖沖喜啦。店主點頭,成交。
同里之行,喜出望外,漫步退思園,思在天外,怎么史料紹介、亭臺樓閣、奇花異木,似乎都未曾入我雙眸。出園,打道回府,一路上滿腦子塞的盡是“開心”兩字。

清咸豐官窯青花云鶴梅瓶
對于官窯瓷,我是屬于“掃盲班”級別的,比真懂的,我是不懂;比不懂的,似乎有些皮毛的認知。這是1988年友人要售我的一件清官窯瓶,造型、釉色、胎骨、圈底、署款文字,乃至未施釉的底圈沿的細膩感,都似真品。況且咸豐老官短命,龍椅一共才坐了10年,所以這一代官窯噐生產的總量,較之乾隆、嘉慶、道光都要稀少。彼時友人索價3000元,抵我當時15張書法的稿費,當慎重。但真?假?一個字,還真讓你心懸在了半空,上下不是,進退兩難,真切地感受到“學到用時方恨少”的古訓。

明代銅鎏金的正冠南極仙翁
國人千百年的傳統:祈福、祈壽、祈祿、祈吉祥。生孩子,送句“長命百歲”,讀書了,送句“狀元及第”,生日了祝你“壽比南山”……良辰美景,皆大歡喜。不僅是嘴上說說而已,且形成強大悠久的祈祝文化,書畫乃至各類藝術品里,這類題材也比比皆是。
這件明代銅鎏金的正冠南極仙翁,即是祝壽題材的精品,高約三十公分,背面署有“南豐縣鄧星造”,更是極具價值的史料。寫到這里,不由想起2004年8月4日,發生在北京潭柘古寺的故事。那天大雨,又非假日,知道香客無多,隨妻兒及學弟去禮佛,廟里極少人跡,確是無比清凈。進廟拾級至毗盧大佛殿,上香之際,萬籟俱寂,倏地聽到一聲巨響,不免一驚,學弟宋歌四處張望,才發現是大殿的頂上掉下了一塊約有六七斤重的大瓦當。從五六公尺空中墜在水泥地上,故有如此響聲,他提起一看,居然完好無損,上書有一“壽”字。宋歌說:老師,菩薩給您送壽啦,倘使不是我陪你來,這等事是說給別人聽都不信的呀。“壽”瓦當我攜歸上海,慎重地給壽字泥金,復在背面記其事。兩年后有一居士告我,廟里的法物還是奉還為宜,時我在病中,即由兒子和學弟冬緣及友人李君專程赴京“完璧奉還”給寺廟方。這已是十二年前的往事了。兼記之。

伊秉綬隸書“視已成事齋”
在明清的書法史上,八閩福建是涌現了一些杰出書法家的。代表性的明末大家,有張瑞圖、黃道周,對后世乃至如今都還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嘉慶時汀州伊秉綬的異軍突起,更堪稱譽,尤其是他那憨拙、古淵、博大、靜穆、詼諧的無古有我,自成一格的隸書,依拙見是上起八代之衰,扭轉了一千五百年頹勢的人物。以往有些論家,稱晉唐之下,書藝日衰,此說偏激,若以正草隸蒃四體書鑒之,說它是“一葉遮目,泰山不見”也不為過。試想漢魏六朝以降,有過高妙雄遒如伊秉綬的隸書不?可見九斤老太以偏概全的思維是不符合史實的。此橫披書“視己成事齋”,饒有外因通過內心始能成功的哲理。書長約六尺對開,伊氏隸書多粗勁者,此則為相對地細峻,較為少見,曾見上海博物館有一聯,也同類意趣。此齋額有葉恭綽先生藏印,尤是珍貴。25年前以四百元購入。去年某大拍賣行有伊氏隸書“遂性草堂”齋額,較現在我館展廳陳列的尺幅小近半,竟以2300萬成交。一字約值600萬。證明伊秉綬的威武。
(本文作者為中國篆刻藝術院名譽院長、上海書法家協會首席顧問、吳昌碩藝術研究會會長)